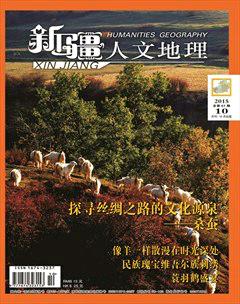探尋絲綢之路的文化源泉
孤島

博大精深的蠶桑文化
中國是世界上養蠶、種桑、織絲最早的國家。
絲綢的發明,是中國人對世界科學技術史的又一大貢獻。古時候,世界許多國家稱中國為“賽里斯”(seres),即“絲綢之國”。
我國很早就形成了完整的蠶桑文化體系。
據傳說,是黃帝的妻子嫘祖發明了養蠶和絲織的技術,實際上并非如此,比這要早得多。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掘,古老遙遠的新石器時代,我國就已經有了蠶業,有了絲織品。
從漢朝張騫“鑿”通西域以后,絲綢等中原的蠶絲織品就源源不斷地,被絲路上的商人從長安收購,運到西域、中亞西亞、地中海沿岸和歐洲各地兜售,成為展示古老中國的一面無聲的旗幟,亮出華夏的奇彩篇章。這些商人又在絲路的西端采購珠寶等奇珍異寶,通過絲綢之路賣給中原的王公貴族。可以說,蠶桑文化是絲綢之路文化的源泉和堅實的根基。元代的維吾爾族詩人馬祖常有詩云:“波斯老賈度流沙,夜聽駝鈴識路賒。采玉河邊青石子,收來東國易桑麻。”
絲路西頭的歐洲人,對絲綢十分癡迷。最早的古希臘人稱中國人為“賽里斯”,意思是產絲之國。在他們的腦海里,絲綢是長在神樹上的特殊“羊毛”。接著,羅馬人也集體傾心于絲綢,花高價買綾羅綢緞——在羅馬市場上,絲綢的價格猶如黃金,一兩黃金才買一兩重的絲綢。到了屋大維執政時期,羅馬享樂主義現象愈演愈烈,哲學家賽內加竟然著文《善行》,如此呼吁道:“人們花費巨資,從不知名的國家進口絲綢,而損害了貿易,卻只是為了讓我們的貴婦人在公共場所,能像在她們的房間里一樣,裸體(太薄?)接待情人。”羅馬元老院也曾三番五次下令,不讓在一些場合穿絲綢衣服。然而,“太陽照常升起”(海明威語),生活照舊如此前行……
絲綢,在西方如此流行,絲綢之路因此不斷地紅火著。殊不知,這皆來自于隨意、閑適的桑樹和小小的蠶繭。怪不得,我國一代代都不斷涌現出詩詞文章吟蠶桑、寫蠶桑、譽蠶桑、思蠶桑,如漢樂府詩《孔雀東南飛》和《陌上桑》等等,匯聚成一條條汪洋大河,一瀉千里……
蠶桑傳入西域
西域原來沒有蠶桑,西域的栽桑養蠶法,是隨著古代絲綢之路的開辟而從祖國內地傳入的,尤以傳入南疆為先。
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曾有過這樣的記載:很古的時候,“于闐”國(今和田)以毛毯、麻布和皮獸制作被服,不知種桑養蠶之事。聽說“東”國(中原)人有蠶桑,就派使者去求蠶種。東國皇帝“秘而不賜”。于闐王便以禮向東國求婚,允。于闐王命令前去迎親的專使告訴公主,帶蠶種至西域。為了傳播文明和幫助西域的角度考慮,公主竟將蠶種偷偷地藏在帽絮里,然后戴在濃黑柔軟的發髻上,躲避邊卡的檢查而移至塔克拉瑪干南緣。“《大唐西域記》繼續說:“陽春告始,乃植其桑。蠶月既臨,復事采養。自此厥后,桑樹連蔭。蠶蛾飛盡,乃得治繭。”《新唐書·西域傳》中也有類似的記載。
于是,大漠邊上興起了蠶桑之事。
從和田出土的唐代木版畫中,就繪有這位“傳絲公主”傳播蠶桑生產技術的圖景。無論歷史上有無這位傳絲公主,但蠶桑從內地傳入卻是真的,根據各種史料推斷,其年代應該在漢代絲綢之路開通以后。
“絲綢之路”是一條西漢時張騫和東漢時班超出使西域開辟的以長安(今西安)、洛陽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最終到鹿特丹,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大商道,有南道、中道、北道三條路線。這一命名是世界著名的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于1877年在他的《中國——我的旅行成果》書中確立的。在這條逾7 000公里的長路上,絲綢與同樣原產中國的瓷器一樣,成為當時一個東亞強盛文明的象征。各國元首及貴族曾一度以穿著中國絲綢,家中使用瓷器為富有榮耀的象征……而絲綢的原材料則主要得益于蠶桑。
聽說,阿勒泰草原上有古老的桑株巖畫。
我在克孜爾千佛洞還目睹過畫上的采桑圖。
大地浮沉,滄海桑田。塔克拉瑪干在億萬年前,是一片汪洋大海,金魚翻躍,浪花簇簇,海獸在船夫的吆喝中露出脊背,沉穩而超然。忽如莊周一夢,悄然而去,面對的又是一番蒼涼景象。
生命之水流逝了,土地開始癱瘓。
人類誕生以后,這里的人將太陽融化雪山而流下的冷冷淚滴,喂著馬、牛、羊、毛驢和自己的生命。有了蠶種后,又從沙漠里開墾出綠意點點的桑田。他們把自己所有的夢想和愛都交付給沙漠邊上的小屋,這古老而素樸的家園。
他們孕育了桑田,而桑田又支起諾亞方舟,反將他們從窮山極惡的風沙里奪回,引渡向幸福,有晚清楊至灼的詞為證:“蠶事正忙忙,匝地桑桑。家家供奉馬頭娘。阡陌紛紛紅日上,士女提筐。零露尚灢灢,嫩芽初長,曉風搖飏漾晴光。果樹森森同一望,點綴新裝。”
在和田,在南疆,在塔克拉瑪干周圍,種桑養蠶織綢,從生存土壤里過濾出來,成為一種美與生存合一的蠶桑文化。
新疆桑葚
桑樹,一種落葉喬木,高約3至7米,也有更高的。桑樹樹皮呈灰褐色,桑樹葉子多卵圓形,四周如粗鈍鋸齒;花朵單性,顏色為黃綠色。新疆南疆,有許多百年桑樹,濃郁蒼翠。
新疆植桑歷史悠久,由內地傳入至少已有1 700多年。
桑樹的葉子不僅可以養蠶供以織絲,在新疆最為獨特的卻是其果實的食用。
桑葚,桑樹的果穗,始見于《唐本草》:長圓形,有柄,長1厘米至2.5厘米,紫紅色或黑色,也有白色的。
全國已收集、保存有近3 000份桑樹樹種資源,它們相對集中于新疆、河北、云南、四川等省、自治區。桑葚口感好的,是雅安3號、綠葚子、江米果桑等;產量高的,是紫城2號、瓊46、長青皮等;藥用價值高的,是新疆藥桑;抗病性強的,是打洛1號、瓊46等;還有的綜合性功用優秀,如白格魯等。
新疆桑樹樹種資源十分豐富,有本土地方品種資源、疑似野生種資源、引進的外地桑種資源等。有雞桑、長穗桑、華桑、白桑、黑桑、廣東桑、長果桑、鬼桑、魯桑、瑞穗桑、滇桑、蒙桑、唐鬼桑、細齒桑等 14 個桑種的種質資源。endprint
桑葚是第一種來到南北疆大地的水果,在新疆被譽為“瓜果中的報春花”。
新疆桑葚個大,汁多,味甜,性寒。鮮食時,其味酸甜可口,生津止渴。桑葚還可被制成桑葚罐頭、桑葚酒、桑葚膏、桑葚果凍、桑葚果汁飲料、桑葚酸乳、桑葚果醬、提取桑葚紅色素等等。
兩千多年前,桑葚已是中國皇帝御用的補品。《隨息居飲食譜》載,“桑葚聰耳、明目、安魂、鎮魄。”
在新疆,桑樹還有另一種獨一無二的妙處:那就是制造桑皮紙。和田的古人制造桑皮紙,是一種古老手工藝。
桑皮紙曾經一度是造紙行業的主角,被稱為人類紙業的“活化石”,它記錄著我國傳統的造紙工藝,是人們了解紙文化的另一個窗口。
和田、吐魯番等地區,從古至今桑樹遍野,綠影叢叢,為桑皮紙的制作提供了可靠的原料。以桑樹皮為原料制作古老的桑皮紙,用來印制書籍、印錢、制扇等,對于古老的西域民族來說,也許是一種物競天擇,而對中國文化來說,又增添了一種神奇的色彩!
新疆蠶桑的興起
據史料記載,新疆自漢朝末年,開始學習內地的養蠶治絲技術,蠶絲業開始處于自發狀態。公元2世紀以前,西域還不能生產絲綢,所有經西域運往中亞甚至歐洲、北非的絲綢都來自內地。
新疆絲綢生產大約開始于公元3世紀到4世紀,到魏晉南北朝時,新疆的養蠶絲織業已具相當規模,它的技術技藝自然也是從內地引入的。
考古人員曾在尼雅遺址里發現一只蛾口蠶,時間不晚于4世紀;吐魯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的文書中的 “建初十四年(公元418年)嚴福愿賃蠶桑券”,記載了“賃叁薄蠶桑”的情況;文書中的“北涼玄始十二年(公元423年)兵曹牒為補代差佃守代事”記載了當地官府已使用佃農看桑,兵曹雇用闞相平等20人看護桑田的史實。文書中,還有“用兵先囤糧,養蠶先栽桑”的記載。這些出土文書,透露出公元3世紀至5世紀,新疆地區的蠶桑業已比較興盛,有相當的規模了。
新疆在學會栽桑養蠶之同時,還向內地學習了繅織技術,嘗試著絲綢用品的生產。
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的一張“某家失火燒損財物表”上,標示著“蠶種十薄、綿十兩、綿經緯二斤、絹姬(機)一具”等物品的字樣;在“高昌永康十年(公元475年)用綿作錦絳線文書”中,也記載了“須綿三斤半,作錦絳”一事。另外,還有許多有關龜茲錦、疏勒錦、高昌所作龜茲錦等的記載,可見那時的尼雅(今民豐)、龜茲(今庫車)、疏勒(今喀什)、高昌(今吐魯番)等地已經有絲綢生產,織綢機的聲音在蒼涼的大漠響起。
唐朝是一個非常開放和歷史上最為興盛的年代。精湛的養蠶織綢技術也自然被來往于長安與新疆間的絲綢商人獲得。因而,從唐朝后期直到宋、元時期,新疆本土制造的錦、緞,已出現了質的飛躍,與內地的同類產品相比獨樹一幟,特別是圖案設計上有一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被列為貢品,聲譽傳至宮廷內外。
1966年和1972年,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出土了有聯珠對孔雀的貴字錦、對鳥對羊樹紋錦、胡王牽駝錦、聯珠貴字綺和聯珠對鳥紋綺等品種,其中“聯珠”是第一次發現的特殊紋錦。在新疆吐魯番和民豐的墓葬里,曾發現過大批的唐代絲織品,大多是聯珠對禽對獸變形紋錦,如對孔雀、對鳥、對獅、對羊、對鴨、對雞、鹿紋、龍紋、熊頭、豬頭等象征吉祥如意的圖案。墓葬里還出現了團花、寶相花、暈花、騎士、貴、王、吉字等新的紋飾。
據傳在元代之前,新疆還曾織出過更加高級的絲綢,如“胡錦”、“番緞”等。
歷史翻到明代,鄭成功下西洋大獲成功,打通了海上絲綢之路,東方和西方的貿易交往大多通過海上完成,陸地上的絲綢之路反而遭受冷落,刺激新疆蠶絲生產和蠶業技術交流的源泉流逝,新疆的蠶桑業因此一步步走向衰微和沒落……
振興邊疆桑蠶業
公元1883年(清光緒九年),新疆建省以后,一些有識之士如左宗棠等人,大力倡導“陸防”觀念,與新疆強化了管理與聯系,新疆的蠶絲業由此重新復興,走上了一條曲折回旋的上升之路。
時任欽差大臣并督辦新疆軍務的左宗棠,他把新疆蠶桑業的復興,作為籌劃新疆經濟藍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翻開左宗棠的《左文襄公奏稿》,可以看到他的一些發展新疆絲綢業的思想。首先,他認為,新疆人民不需要以高價“度隴趨蜀,以買新絲”,即遠赴甘肅、四川去買絲,而應該自己生產,使其“耕織相資,民可致富”;其次,俄國、印度、阿富汗等鄰國的商人常來新疆購買蠶絲,部分還遠赴四川返購,如果新疆當地的絲綢能供其所求,新疆“近水樓臺先得月”,有大利可圖;第三,民得利而富,則“厘稅有增,可稍紓軍儲之急”,由此增加國家利稅,填補軍需之用。
具體如何振興新疆的蠶桑業?左宗棠認為,先從南疆開始,因為南疆環塔克拉瑪干四周的綠洲遺留桑樹多,容易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南疆發展起來后再發展北疆。
為了實施這一計劃,左宗棠在南疆各地區籌劃建立推廣蠶桑的官方組織機構——蠶桑局(于1883年在疏勒設立);引進他故鄉湖南的桑樹“湖桑”,改良新疆原有桑樹品種;并先后從浙江一帶招募40多名養蠶工和紡織工,到和田傳授技藝,以圖復興邊陲的養蠶事業,并幫助更新設備,選用良種,在困難中籌措興辦蠶桑業經費等等,致使邊疆的蠶事初興。由于南疆氣候干燥、晝夜溫差大,土壤含鹽堿較重,有的地方煮繭用水混濁等原因,短期內絲繭的產量和質量并沒有得到顯著的提高,加之一部分官吏以倡辦蠶桑為名,行沽名釣譽之實,甚至還想方設法盤剝桑農,致使左宗棠一走,新疆蠶桑業又陷入低谷,舉步維艱。
后來又怎樣了呢?
公元1907年(清光緒三十三年),近代著名學者王樹枬任新疆布政司,為了重振南疆蠶桑業,征召了一個熟諳蠶桑的浙江紹興人氏趙貴華,全面負責蠶桑事物。endprint
我的這位前輩老鄉趙貴華,走訪了南疆八大城鎮,邊了解情況,邊搞種桑養蠶的技術表演,宣傳蠶桑的妙處。同時,他通過四處尋訪賢能,找到領工匠韓庭秀、老養蠶工徐永高、提花匠毛金芳和織綾羅綢緞的大工匠蔣光賢等四位來自江南的老藝人,以及和這四位齊名的維吾爾兄弟夏木西、司奈木、阿合毛拉、巴海等,開始了漫漫征途……
再后來,新疆蠶事得到了空前規模的發展,具有民族特色的“艾德萊斯綢”也由此興起,和田出現艾德萊斯的絲綢生產場地。古代和田是絲綢之路南路的交通樞紐,是重要的絲綢集散地,是西域三大絲都之一。
“艾德萊斯”一詞,泛存于印歐語系和突厥語系詞匯中,通常讀音“阿特拉斯”,維吾爾語變音為“艾德萊斯”。艾德萊斯綢,最早產于和田洛浦縣西北部的吉亞鄉,玉龍喀什河中下游的東岸。它的生產工藝流程是:先將蠶繭煮沸抽絲—并絲—卷線,然后經過扎染—圖案設計—捆扎,最后分線—上機—織綢,形成成品。
艾德萊斯綢是新疆喀什、和田特色傳統手工藝織品,其扎染技術獨特,質地柔軟,輕盈飄逸,圖案層次分明,布局對稱,組合嚴謹,色彩艷麗,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把新疆歌舞之鄉、瓜果之鄉極富藝術風韻的特點集中于尺幅之中,深受新疆維吾爾族和烏孜別克族婦女的喜愛。隨著不斷地對外開放,新疆生產的艾德萊斯綢已遠銷巴基斯坦、吉爾吉斯斯坦、沙特、土耳其、德國、美國、日本及沿海等地,深受中外客商及用戶青睞……
絲綢之路的源泉
據近代的歷史統計,僅和田境內,當時蠶桑樹就栽種了200余萬株,大批大批的蠶繭、蠶絲銷往美國、俄羅斯,每年收回的白銀就有8萬兩之多……
民國時期的謝冰,在他的《新疆游記》中,這樣描寫新疆蠶桑的盛況:“自莎車至和田,桑株幾遍原野。機聲時聞比戶,蠶業發達,稱極盛焉。”1915年,和田共有養蠶戶32 440戶,年產蠶繭550噸、生絲307噸。
這一切,似乎很遙遠,想想21世紀初,在南疆和田一帶為了以新的政策、新的經濟林果,快速拉動所謂的當地經濟,人們有計劃地成片成片地砍伐桑樹,一步步遠離蠶事……世事如煙,不由得讓人生出滄海桑田、人生無常的感慨來。
2002年,不知為什么掀起了一場砍伐桑樹、發展新的經濟林果業的浪潮。有人認為,古老的桑樹雖好,但沒有經濟效益(有的地方少有人養蠶、制絲,做衣服和被褥),耽誤了脫貧致富的大好時機,所以要拿出上世紀90年代初大種桑樹的精神勇氣,來大規模地砍掉那些“無用”的桑樹,騰出空間來種植核桃、杏子、紅棗、葡萄等,發展現實經濟。
此今一發出,各縣、鄉鎮、村莊就紛紛開始砍伐桑樹。例如,在洛浦縣,要求一個月砍掉農毛渠邊500公里的桑樹。于是乎,桑樹像是遭遇了一場突如其來的巨大變故,抑或犯了什么大罪,紛紛成了“刀下鬼”。“桑樹”之“傷”,這次卻受之于它們自己。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南緣歷經滄桑的桑樹,一株株倒下,一排排倒下,一片片倒下……無論是百年老樹,還是剛剛長出的小桑樹,幾天之內就從地球上徹底消失了……一些農民的房前屋后,砍下的桑樹壘積成山,當柴火燒也燒不完。
然而,有兩個沙漠邊沿的鄉鎮卻依靠鄉領導和桑農的庇護,桑樹才得以幸存下來。這兩個鄉就是洛浦縣的杭桂鄉和墨玉縣的喀爾賽鄉。
鄉領導以真情、真實、常理,勸說那些上面來指導、檢查砍伐桑樹的干部,而農民則找上門來說:要砍桑樹,還不如拆了我們的家,毀了我們的地!
曾畢業于蘇州蠶桑專科學校的買買提明·阿布都拉,現在是墨玉縣喀爾賽鄉的鄉長,他說“我們鄉沒有砍掉一棵桑樹。”該鄉,現在生存著90萬株桑樹,年產蠶繭150噸左右。
桑樹是不是沒用了呢?在今日的浙江,蠶繭用來做蠶絲,而蠶絲做的“蠶絲被”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被子,既暖和又非常輕薄,許多生活條件好的家庭和三星級以上的酒店里,有許多用的都是蠶絲被。所以,經濟走在全國前列的浙江,都沒有集體砍伐桑樹改種其他果樹。在一些農村,一些不能出遠門打工的家庭,還是靠種桑養蠶而獲得過年所需的資金。而在有著悠久蠶桑、絲綢傳統的浙江湖州等地,仍然靠著蠶桑養家糊口或發財致富。
而在未砍桑樹的喀爾賽鄉,養蠶也是有明顯的經濟效益。這個鄉,每年可以從蠶繭上獲得300萬的經濟收益,蠶農不需要遠行賣繭,到了季節,和田地區絲綢廠就派人到鄉蠶繭收購站現場收購,最好的蠶繭為特五級,收購價格不菲;接著是特四、特三、特二、特一,一級、二級、三級、四級、五級,最差的五級蠶繭收購價每公斤也在10元以上。
墨玉縣的喀爾賽鄉和洛浦縣的杭桂鄉,一株株桑樹撐著綠色冠蓋,站在路邊、渠邊、桑園、村邊、沙漠邊、維吾爾村民的房前屋后,裝扮著黃沙漫漫的家園,它們有的已抗拒了上百年的風沙,給人們染了上百年的綠色,結了上百年的桑葚果,或許還無意中,在哪一年的戰亂、饑荒中以自己的桑葚救了誰和誰的性命。
桑蠶文化的延伸
人各有命運,蠶桑業似乎與人一樣,也有命運,起起落落,盛盛衰衰。
不說遠的,自共和國成立以來,新疆和田地區的蠶繭產量就顯示了這種起伏:1950年44噸,1959年3 800噸,1978年700噸,1995年5 400噸,2001年3 370噸,2005年200噸……
與此相比,桑樹就自強不息得多,它一旦長成以后,無論在什么野地、田間地頭,還是沙邊溝岸,一代代地生生不息,甚至斧頭也不能讓他們低頭,以自己的綠給沙漠綠洲撐起一片生命的色彩。一到春末就第一個長出果實,無私地將桑葚供給經過的每一個需要的人,而且從不要求人們感恩。能抗拒風沙,卻最終抗拒不了人類的斧頭。2002年,和田地區無數的桑樹還是被莫名其妙地執行死刑的判決,五分之四的桑樹都被處了“腰斬之刑”。種大一棵樹,可能需要很多很多年,流很多很多汗水,然而砍掉它時,卻只在一瞬間……
有一件欣喜的事是:也就在2002年這一年年底,我從另一份資料上看到,在自治區科研院所改革與發展專項資金的資助下,建立起了“新疆桑、蠶生物工程育種重點開放實驗室”。
到2006 年,該研究所與農業部設在西南大學的蠶桑學重點開放實驗室,共同建立“新疆蠶桑基因資源研究中心”,進一步收集、整理、研究新疆乃至亞洲中部干旱地區的特有的桑樹種質資源,建立具有地域特色的中亞桑屬植物遺傳基因庫。
南疆的維吾爾族尤其喜歡種植桑樹,在他們心靈深處,桑葚是救命果。在大地上種下一棵桑樹的人,可以吃到天堂里的果子。在和田、在喀什、在庫爾勒等這些生態脆弱的環塔克拉瑪干沙漠綠洲,桑樹像平凡的英雄,默默地防風固沙,是農田和家園的保護神。一到春夏之交的青黃不接時節,滿樹的桑葚又是桑樹無私賜予饑餓人們的食糧。因此,沙漠邊沿的和田人對桑樹的厚愛包含著一些莫名的崇拜,所以,有一句諺語世世代代相傳:“桑大不可砍,砍桑如殺人。”
而在我國的漢文典籍中,桑樹被稱為“東方自然神木”。
可以這樣說,沒有桑樹,就沒有我國5 000年歷史的蠶桑業,就沒有絲綢,更沒有絲綢之路。從這個意義上看,絲綢之路不僅僅是一條路,而是中國桑樹生命的一次延伸,是桑樹在植物文化學上的由東向西的一次再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