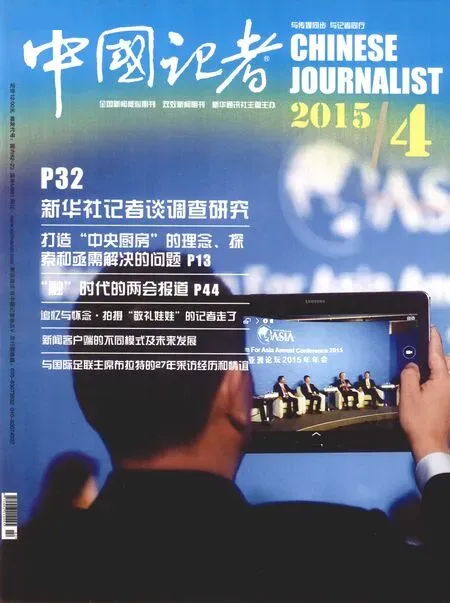法律視角下,氣候變化報道的重點與趨向
法律視角下,氣候變化報道的重點與趨向
□ 文/王云鵬
提要:隨著氣候變化問題成為新聞報道中的焦點議題,氣候變化報道也成為媒體熱點。當前,在氣候問題已經不僅是一個生態問題,而且向多個領域延伸的背景下,強化氣候變化的法治維度,增加對國際和國內氣候變化法律的關注,就顯得日益重要。作者以一位氣候變化法律研究者的視角,介紹了氣候變化報道在法律維度方面需要關注的若干問題。
關鍵詞:氣候報道 環保報道 法律 趨向
當前,隨著應對氣候變化問題被確認為國家戰略,①氣候變化報道正成為新聞報道熱點問題。以往氣候變化報道多強調氣候問題的科學性、政治性、社會性等問題,突出報道過程中的專業精神和對國家利益的考量。②而隨著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程的加快③,新聞媒體應當強化氣候變化的法治維度,增加對國際和國內氣候變化法律的關注度,從而在培育公眾相關法律意識,協助以法律調控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氣候變化的法律變遷要求媒體更新報道視角
無論從科學事實、經濟社會影響和圍繞氣候談判的國際政治博弈來看,氣候變化問題本質上均屬于一個全球性的社會問題。從法律調控角度出發,氣候變化法本身具有國際法屬性。作為《國際氣候變化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的締約國,我國有義務將氣候變化的國際協議“內化”為本國的法律、政策和行動。比如《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和每一年度的《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
關注國際氣候變化法律變遷在于兩點:第一、國際氣候變化新框架協議的形成和“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的發展;第二、各國應對氣候變化法律的最新進展。
1. 理性看待“各自能力”原則。我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一直視《公約》和議定書為應對氣候變化的主渠道,并始終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但是,自2011年“德班會議”以來,歐盟等開始在氣候談判中要求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放棄其一直所堅持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承擔與發達國家相同的量化強制性減排承諾。發達國家淡化其歷史責任和修改“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的立場,一直延續到之后的多哈會議(2012)和華沙會議(2013)。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談判中的利益博弈,使得“各自能力原則”出現在國際氣候變化法的視野中。典型例證就是中國對溫室氣體減排的承諾、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將“各自能力”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并列的表述,④以及“利馬氣候行動倡議”提及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公平原則和各自能力原則。
可以預見, 2015年達成的新議定書或者法律文件,必然依據“各自能力”原則要求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承擔一定的量化減排義務。對這一可能的國際氣候法律發展,將來的氣候變化報道應當理性看待:
首先,即使中國被課以強制性的減排承諾,在《公約》項下,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依然可以根據本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做出適當可行的具體承諾,平衡經濟發展與應對行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除非《公約》的基本原則被推翻。其次,即便不承擔具體的強制性的減排義務,我國基于深化經濟改革且通過“抑霾降碳”來倒逼產業結構升級的目的,也應在可持續發展和建設生態文明的背景下,采取適當的減緩行動。最后,我國在《哥本哈根協定》中已經做出了到2020年在2005年基礎上降低碳排放強度達40%-45%的承諾,且這一承諾已被寫入《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規劃(2014年~2020年)》。我國也已經通過淘汰落后產能、推動產業升級、擴大新能源利用、推廣低碳節能技術等切實的節能減排戰略行動,實現了碳排放強度實質性的降低,承擔了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應當承擔的減排責任,不應妄自菲薄。
2. 客觀介紹他國制度進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如,歐盟單一的碳交易市場的發展和形成,對中國碳交易制度試點和全國碳交易市場構建的借鑒意義。美國依據《清潔空氣法》對溫室氣體排放予以監管的“舊瓶裝新酒”式的法律變遷,也印證了通過大氣污染防治法律體系調控溫室氣體排放的制度化可能。正是基于這種可能,《大氣污染防治法》(征求意見稿)提出了協同控制溫室氣體與細顆粒物、可吸入顆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大氣污染物的基本原則。因此,在堅持我國利益,揭露發達國家忽視其歷史責任和其高人均碳排放量的同時,氣候變化報道也應當對歐盟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新制度發展予以客觀評價和報道。
氣候變化立法亟待媒體持續關注
如前述,到2020年在2005年基礎上降低碳排放強度達40%-45%的承諾,已被納入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由此,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開始面臨環境與碳排放雙重約束,氣候變化立法已實質啟動。中國網、新華網、
《法治日報》《經濟參考報》《中國氣象報》等媒體,在立法草案提交并征求意見的2012年初對草案的框架、內容、特點和基本措施等進行了集中報道。但根據筆者以“中國氣候變化法”為關鍵詞在百度和中國知網的檢索結果看,自此之后,氣候變化立法被淹沒在更多的立法熱點之中,比如《立法法》《環境保護法》《大氣污染防治法》等的修訂和修改,鮮見相關方面的追蹤報道。
考慮到氣候變化的長遠效應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戰略性,媒體應對氣候變化相關立法工作予以持續關注。
比如不定期地對“氣候變化法”立法建議稿、征求意見稿和立法草案的生成予以關注;定期訪談參與該項立法的相關部門負責人、專家和學者,披露立法進程,維持公眾對于該問題的關注度。
除應對氣候變化的基本法律制度構建予以關注外,媒體應對各項具體減排制度保持關注,比如《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規劃(2014年-2020年)》提到的碳交易制度、碳排放認證制度、財稅和價格政策、投融資政策,以及能源、節能、可再生能源、循環經濟、環保、林業、農業等相關領域的法律法規和電力、鋼鐵、有色、建材、石化、化工、交通、建筑等重點行業溫室氣體排放標準等。
客觀評價,全面報道各項減排機制
在對氣候變化相關立法予以持續關注時,媒體還應客觀評價不同制度的績效,不應毫無依據地夸大或貶低某一溫室氣體減排制度的效能。當前對大氣污染和氣候變化等環境問題的應對方式,大體有三種路徑:
第一、依靠政府強制手段的“命令與控制”方式,比如污染物排放標準、對污染源的新建或者改建實施強制性審批程序、履行標準或者排放限制、強制性信息披露、產品禁令或者使用限制等。立法表現為制定以水污染、大氣污染等為代表的環境保護基本法律制度。第二、以排污權交易為代表的“成本與效益”方式。這種方式基于新制度經濟學家的理論,試圖以經濟方式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排放權交易制度與應對氣候變化的結合,衍生出《京都議定書》下“清潔發展機制”“聯合履約機制”⑤和各國碳交易制度。第三、排污收稅(費)制度。當前實施于英國、荷蘭、波蘭、丹麥等國,以化石燃料燃燒的二氧化碳含量為計稅依據的碳稅(氣候變化稅),就是基于該方式的以溫室氣體排放為規制對象的制度安排。
我國目前應對氣候變化的制度構建,并未超出上述路徑范疇。政府在推進地方碳交易試點,完善全國碳交易制度的同時,也在探討改革資源稅和環境稅制以征收碳稅的可能性,并提出要加快制定重點行業的溫室氣體排放標準。然而,基于對政府行政監管效率的懷疑,研究更多的是在討論并倡導碳交易等“成本-效益”減排機制,對碳排放標準的關注和研究較少。
主流媒體對于氣候變化的報道也有類似趨勢。如從中國知網“中國重要報紙全文庫”(該庫主要收集《人民日報》《中國經濟導報》《中國環境報》《中國證券報》《文匯報》《科技日報》《中國能源報》等重要報紙刊物,基本能夠代表主流媒體報道趨勢)2005年以來主要報刊的相關內容來看,截至2015年3月16日,以“碳交易”為題名的目標文章有670篇;以“碳稅”為題名的目標文章有430篇;而以“碳排放標準”“二氧化碳排放標準”或者“溫室氣體排放標準”為題名或者關鍵詞的匹配目標文章極少。
因此,媒體和學術界在對行政主導下的環境污染治理模式的低效率進行反思和批判的前提下,不應毫無依據地假定碳交易等“成本-效益”方式的有效性,從而忽視了傳統的標準制度和行政監管手段對于溫室氣體減排的績效,應考慮國家政策宏觀走向,秉持客觀立場,理性評價不同減排制度。(作者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博士生,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我國在城鎮化進程中構建低碳城市的法律保障措施體系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號:13AFX024)


【注釋】
①國家發展改革委:《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2007,《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
②朱國平:《氣候報道的專業精神》,《中國記者》2012年2月,72頁-74頁;鄧瑜:《從發展傳播學視角看氣候變化報道—兼談“關注全球氣候變化”的電視策劃》,《中國記者》2010年2月,32頁-34頁;劉軍:《怎樣把握與拓展氣候變化報道》,《中國記者》2007年8月,14頁-15頁。
③《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④《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新華網2014年11月13日。
⑤Kyoto Protocol, Article 6 and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