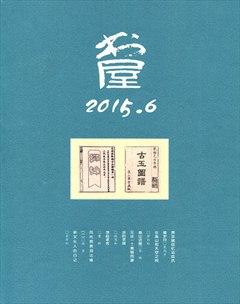賈亦斌回憶浴血抗倭歲月
裴高才
2003年盛夏時節,筆者為撰寫《胡秋原全傳》赴京專訪了胡氏老友、九秩高齡的賈亦斌將軍。賈老上穿白襯衣,下著藍條褲,足穿平底布鞋,親自走下樓,來到庭院門口笑臉相迎我,給人賓至如歸之感。當時,老將軍給我的印象是,他雖然滿頭花白銀發,但腰不勾、背不駝,步履穩健,連老人斑都沒有一塊,看不出他是一位年過九旬的老人。我在參觀賈老的書房時,老人一邊介紹他于戰時陪都重慶與胡秋原的相識相交,一邊提筆給我簽贈將軍的回憶錄《半生風雨錄》,還特地題寫了一副對聯:“醒獅怒吼,誰敢鯨吞蠶食;散沙凝結,哪怕豆剖瓜分。”當談到當年在抗日戰場上南征北戰、九死一生的經歷時,賈老動情地說:“日寇發動的那場戰爭太慘了!淞滬會戰時,我親眼目睹由湖北一起前去的數百位將士倒在日軍的炮火下!徐州會戰時,為了阻擋日軍進攻,黃河被炸決口,一下子死了成千上萬的老百姓;武漢會戰時,日本人放毒氣彈,我們第八十一師的兩個營只有三個人活下來;鄂西會戰時,我率兩個營到敵后打游擊,部隊被包圍,狂風暴雨,又沒有飯吃,八九十個官兵活活凍死了。戰場上的慘烈、倭寇的兇暴、人民的痛苦,我都永遠忘不了……”
百年前的1912年11月22日,賈亦斌出生于湖北省武昌府興國州(今陽新縣)青龍鄉賈家門前屋的一個農民家庭。湖北陽新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也是天災人禍頻發的地區。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全國工農運動、學生運動等革命風暴蓬勃興起,特別是湘、鄂、贛等省的農民運動更是洶涌澎湃,工會、農會、婦女會、兒童團等如雨后春筍紛紛建立起來。在工農大眾的支持下,北伐軍節節勝利,勢如破竹,繼攻克了湖南后,于1926年10月10日又光復了武昌,一時間,武昌成為大革命運動的“紅都”。正在湖北陽新縣城陽新中學讀書的賈亦斌看到北伐軍官兵人人佩戴著“愛國家、愛百姓、不怕死、不要錢”的字符,官兵同穿草鞋,部隊紀律嚴明,對老百姓秋毫無犯,所到之處都受到老百姓的熱烈歡迎。賈亦斌也與同學們一道走上街頭游行和登臺演講,熱烈歡迎北伐軍,縣城到處洋溢著一派革命氣氛。不久,學校停課,賈亦斌回到家鄉,投身到熱火朝天的農民運動之中。
由于陽新縣農民一直與貧苦抗爭、搏斗,他們積極擁護北伐軍和農民協會的主張。家鄉的農民協會、兒童團等革命組織也很快建立起來了。賈亦斌的二伯賈方南出任農會會長,十五歲的賈亦斌也被推舉為兒童團團長。
大革命失敗后,賈亦斌因家貧學費和生活費無著,當向親戚借錢受辱之時,正值徐源泉率國民革命軍四十八師駐防湖北,于是,他于1930年報名參加了第四十八師教導隊。舊軍隊是用士兵的血淚織成的,他在其中常遭鞭笞辱罵之苦,多次被打以后,他含著淚暗下決心:將來我當了軍官絕不打罵士兵。
1931年初,第四十八師教導隊更名為國軍第十軍干部學校,并將校址由荊州遷到武昌。同年夏,武漢遭受了特大洪災,災后霍亂流行,賈亦斌不幸感染了霍亂,整日上吐下瀉,高燒不止,瘦得皮包骨,學校認為他沒救了,就將他遣送到難民營,讓其自生自滅。賈亦斌也以為自己只有在難民營等死了。好在,自進了難民營后,他的病情竟奇跡般地好轉起來,后被送醫治愈,撿回了一條命。
賈亦斌大難不死歸隊不久,忽聞“九·一八事變”爆發,頓時失聲痛哭,他既痛恨倭寇侵占東北,又對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感到痛心疾首。
歲末年初,賈亦斌在軍校畢業后,回到第四十一師先后任文書、特務長和少尉排長。當他得知,1932年1月28日,日軍在上海挑起事端,遭到我國抗日鐵軍第十九路軍的奮勇還擊(即“一·二八”淞滬抗戰)。全國及上海廣大民眾踴躍支援十九路軍的義舉,粉碎了日軍速戰速決的陰謀。賈亦斌從內心感到高興。
可是,1932年5月,中日雙方簽訂了不平等的淞滬停戰協定。協定規定:日本政府可以在上海派駐一定數量的海軍艦只和一部分的海軍陸戰隊,而中國政府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區不得派駐軍隊,只能由中國的保安團隊和警察來此地維持地方秩序。
為了應對日軍再次挑起事端,國民政府于1934年至1936年間在上海到南京之間和上海到杭州之間構筑了大量的國防工事。同時,南京政府任命張治中將軍為京滬警備司令。張治中受命后即開始秘密組建司令部,并主持制定進攻上海日軍據點的新未來作戰計劃。該計劃規定:在戰爭剛開始時,就以優勢兵力突進到上海,一舉掃蕩和消滅日軍的據點,以防止日軍利用這個橋頭堡進行大規模的登陸。為此,張治中將中央軍的精銳部隊第三十六師宋希濂部、第八十七師王敬久部和第八十八師孫元良部以及炮兵笫八團和炮兵第十團秘密布防在蘇福線和錫澄線附近。
“七七事變”爆發后,正在荊州整訓的少校營長賈亦斌多次代表全營官兵向上級請愿,要求開赴前線殺敵報國。
盧溝橋戰起,京滬警備司令張治中將軍立即命令所屬部隊進入戰備狀態,同時,他請示蔣介石獲準:將第二師補充旅一團的官兵化裝為上海保安團隊,派駐到上海的虹橋和龍華飛機場加強警戒。
1937年8月9日,日軍海軍中尉大山勇夫騎摩托車欲闖進上海虹橋機場,被我保安隊士兵擊斃。次日,日方代表以此借口要求我軍化裝的部隊撤出上海并拆除上海市區的防御工事,遭到我軍斷然拒絕。8月11日,日軍海軍第三艦隊駛集黃浦江及長江下游各港口,日軍在上海的海軍陸戰隊四千人也進入了戒備狀態,上海的形勢驟然緊張。當天下午九時,張治中命令早已集結好的我軍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和炮兵第八團、第十團連夜推進到上海市區和黃浦江一線。
8月13日,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最大規模的淞滬會戰打響了!雙方投入的總兵力達百萬之眾。面對占盡海陸空優勢的野蠻入侵者,中國軍隊奮起抵抗,損失慘重,每天傷亡將士近萬人。
“淞滬會戰”的消息傳到湖北,二十五歲的賈亦斌渾身熱血沸騰,為表達他誓死上陣殺敵的決心,他毅然咬破手指寫好血書后迅速到師部請纓,他的申請被批準,并于9月初啟程,從湖北隨國軍第四十一師第二四五團開赴上海前線。他到上海以后,被編入國軍精銳第十七軍團第一軍第一師,就任第一師第二旅第四團第一營營長。
賈亦斌所在部隊的任務,是據守上海市郊的楊行和劉行一帶。這里是一片平地,無險可守,只能靠深挖戰壕與敵人打陣地戰。那時候,日軍上邊有飛機,黃浦江上有軍艦,陸地上有很精銳的武器。而我軍的武器比較差,在不可一世的日軍看來,我軍前線的將士就像日方海、陸、空軍的活靶子一樣。面對兇殘的倭寇,賈亦斌視死如歸,他率領戰友們在陣前宣誓:“我們前來保衛大上海,就是跟小鬼子拼命的!活下來就勝利了,死了也甘心!”
為了摸清敵軍的情況,賈亦斌帶領幾名隨員,進入一個叫趙家宅的小村莊的一片小竹林里偵察。當他剛剛拿起望遠鏡向敵人陣地望去,很快被敵人發覺了。霎時,一發迫擊炮彈飛過來落在他身后,他的帽子被氣浪掀掉,腦袋被彈片炸出了血,一下子就暈倒在陣地上,戰友以為他“光榮”了。醒來后,戰友就讓他下去療傷。他堅決地表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身為營長,怎能不去?!只要我有一口氣,就要堅守陣地,死也要死在戰場上!死了也不做亡國奴啊!”
與敵人打陣地戰,必須以深挖戰壕作掩體。可是,上海地下水位高,一挖戰壕水就往外冒。賈亦斌率領官兵們只能陷在滿是積水的泥濘中與敵人苦戰。上海的老百姓了解到這一情況后,他們紛紛拿來木板與鋼板作掩體,全力支持國軍抗敵,形成了軍民聯合抗日的激動人心場面。
在同仇敵愾的愛國熱情鼓舞下,賈亦斌率部英勇頑強,打退了敵人一次次瘋狂的進攻,幾乎每一寸陣地都經過反復的爭奪,甚至肉搏拼刺刀,雙方都傷亡慘重。經過浴血奮戰二十多天,賈亦斌率領的第一營四百多人只剩下不到一百人,而手下的連長三個陣亡、一個受傷;排以下軍官幾乎傷亡殆盡,但官兵們愛國殺敵的士氣依然高昂。
9月20日,賈亦斌率部移防劉行,敵軍出動二十架飛機、數十門大炮,千余發炮彈幾乎把陣地全覆蓋了,隨后日軍陸軍在數十輛坦克的掩護下,分三路對賈亦斌部進行合圍。旅長嚴明得知賈亦斌的第一營的嚴峻形勢后,就緊急在電話中問賈亦斌是否要增援。賈亦斌知道,當時戰場上的每個部隊里面大都傷亡過多,都需要增援。所以他斬釘截鐵地回答:“報告旅長!人在陣地在,我不僅不要增援!還應該去增援別人!”幸虧是廣西援軍及時趕到才給賈亦斌解了圍。
到了9月30日,日軍發動總攻擊,經過激烈戰斗,大場失守,賈亦斌所部腹背受敵,被迫撤退到蘇州河南岸,賈亦斌率第一營官兵防守北新涇大橋。面對敵強我弱,善于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的賈亦斌摸到了如何打退渡河的日軍路子。
原來,賈亦斌邊打仗邊觀察邊總結,他認為:我軍的戰術觀念陳舊、落后和官兵們不具備現代戰爭的常識,仍然沿用以往國內戰爭的老一套戰法和日軍作戰。在日軍的立體戰法之下,僅憑一腔的愛國的勇敢必然招致了許多無謂的傷亡,必須要學會隱蔽、用靈活機動的戰法與敵軍周旋。當他發現敵人在渡河前,往往是先用飛機轟炸,炸了以后用炮打,炮擊以后才是步兵渡河進攻。于是,賈亦斌根據敵人進攻的規律及時調整了戰法,他在陣前緊急布防說:“我們的陣地首先一定要做好隱蔽!把機關槍做得很低,敵人第一輪用炮擊的時候,我們不要動;敵軍用飛機轟炸的時候,我們也要隱蔽在戰壕不要動。一旦看到日軍炮炸了、飛機炸了以后,步兵差不多能來渡河了。當日軍步兵到了河中間的時候,我們的機關槍這才開打起來,讓敵軍進也不能、退也不能!只有這樣打,才能重創日軍!”
賈亦斌的戰術迅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僅堅守了陣地,而且造成日軍大量傷亡。很快,友鄰部隊也專程到賈亦斌這兒來現場觀摩,推廣他的殲敵經驗。有一天,他正在給友軍第三十六師介紹防御工整的時候,一發炮彈打來落在他附近,他的腿掛彩了。戰友們要送他離開陣地,他堅決不肯,只是稍作包扎繼續堅守陣地。
親歷抗倭現場,賈亦斌最強烈的感受就是戰斗太慘烈了!戰場上人數既多,又無險可守。敵海、陸、空三軍的火力可以盡量發揮,我軍等于陷入一座大熔鐵爐,任其焦煉。敵方炮火之猛,猛到我軍炮兵白日無法發炮,而夜間又無法尋找目標,只是盲目轟擊。所以,當時我軍將士完全是以血肉之軀來填入敵人的火海。將士們犧牲的壯烈,在中華民族抵抗外倭的歷史上,鮮有前例。
同時,賈亦斌與戰友們終日處于極度的疲勞和饑餓之中。日軍只要看到國軍生火燒飯,飛機就炸來了。這樣一來,他們白天就根本沒有辦法燒飯,只有到了夜晚以后才可以燒飯。所以他們經常是忍饑挨餓地戰斗。最慘烈的是戰場救護不及時,醫務人員少得可憐,擔架隊也較少。許多傷兵缺醫少藥躺在戰壕里,任其日軍炮火轟擊,運傷病都不能運,往往輕傷變重,重傷者自生自滅了。
賈亦斌回憶說,日軍為了盡快結束“淞滬會戰”,于1937年10月初就開始著手尋求一種另外的方式來解決上海日軍的困境──抽調三個師團,從杭州灣登陸打擊我軍的側背處。11月5日,上海后方失守,我軍被迫全線撤退。賈亦斌受命掩護大部隊撤退,撤退中,第十七軍團司令部被一隊輕裝的日軍打個措手不及,警衛部隊和參謀人員大部分被打死,軍團長胡宗南只和幾個參謀僥幸逃出而加入了潰散的大軍;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薛岳的汽車被日軍的機槍打翻,司機和衛士被打死,薛岳趴在一條下水溝中大氣不喘地足達幾個小時方才脫逃。
上海撤退的時候,難民和國軍幾十萬人都擠到那個馬路上。那天天剛亮,日軍飛機便對我軍俯沖掃射。賈亦斌發現前面不遠處的馬路那邊有一個孕婦,拖著四個孩子,非常吃力地奔逃著。這時,一架日機突然俯沖下來,賈亦斌急忙喊那個孕婦趴下!話音未落,一顆炸彈轟然爆炸!孕婦和四個孩子全被炸死,她腹部也被炸開,胎兒還在蠕動,遍地都是鮮血。這種慘景,幾十年后賈亦斌一想起來仍痛心不已:“我在戰場上,最慘烈的是這一次。真是慘不忍睹啊!”
當賈亦斌率隊撤到方家窯附近的一條河邊時,公路橋上已經布滿了地雷,以炸橋阻止日軍。我軍唯一的一個用德國15cm重炮裝備的炮團撤到這里,無法過橋。重炮團團長彭孟緝在岸邊失聲痛哭。他對賈營長說:“中國就只有這個像樣的炮團,怎么辦呀!”賈亦斌也愛莫能助,炮手們只好忍痛把嶄新的重炮全部推進河中。
“淞滬會戰”結束后,第十七軍團軍團長兼第一軍軍長胡宗南召開會議議決有功人員。第一旅旅長嚴明對胡宗南說:“我們第四團第一營營長賈亦斌是個怪人,他兩次受傷,不下火線;給他增援,他不要,還要增援別人;但他作戰勇猛且善于動腦子,在蘇州河重創日軍,后期又掩護部隊撤退。我保舉這個怪人晉升團副!”但因胡宗南說賈亦斌不是黃埔出身,結果改任賈為旅部中校參謀主任。
“淞滬會戰”歷時三個月,打破了日軍三天占領上海、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幻想,共殲滅日軍四萬多人,我軍也付出傷亡三十多萬將士的慘重代價。賈亦斌接下來又參加了“徐州會戰”、“武漢會戰”,屢立戰功。1941年升任第七十三軍第七十七師少將參謀長,參加了鄂西戰役和第三次“長沙會戰”。賈亦斌的德行深受蔣經國賞識,歷任預備干部局副局長、代理局長、陸軍預備干部訓練第一總隊總隊長。蔣曾稱贊道:“文將不愛財,武將不惜死,則天下太平矣。賈亦斌兼而有之!”1948年12月初,為反對內戰,賈亦斌與段伯宇等醞釀、籌劃,于1949年4月7日在浙江嘉興毅然率部起義,26日抵達南京,被批準為中共黨員。
新中國成立后,賈亦斌歷任上海公安局社會處干訓班副主任,上海食品出口分公司經理。1957年8月加入民革,歷任民革上海市委員會第三至六屆副主任委員,第四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979年10月調民革中央工作,先后任民革第五至七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第八至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名譽副主席,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至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常務委員。曾兼任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理事會副理事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常務理事、顧問,譚嗣同研究會名譽會長等職。
2005年9月3日上午,胡錦濤同志曾在人民大會堂湖南廳,向賈老一行十位抗戰老戰士頒發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紀念章。現值中國人民紀念抗戰七十周年之際,賈老的話語仿佛在耳邊回響:“抗戰時,正面是國民黨在打,敵后是共產黨在打,這就是全面抗戰,光講哪一面都和事實不符。而共產黨提出‘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這個方針是最重要的,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也非常重要,保證了抗戰最終取得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