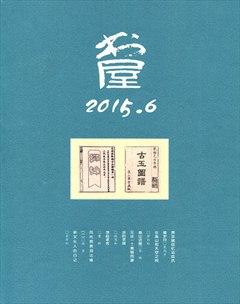從教材看時(shí)代變遷
付強(qiáng)
教材不僅承載著教學(xué)內(nèi)容,也承載著時(shí)代的歷史記錄。作為從事大學(xué)教材工作三十年的人來說,最近距離地目睹了教材所反映出來的時(shí)代色彩和歷史色調(diào)。
光從教材的外觀上來說,就深刻地反映了時(shí)代的發(fā)展。與上世紀(jì)八十年代的教材在裝幀、紙張、設(shè)計(jì)、印刷、開本等進(jìn)行比較,當(dāng)下的教材完全可以用美觀大方、制作精美、質(zhì)量上乘等字眼來概括。當(dāng)然這里有一個(gè)瑕疵就是,校對上的錯誤成為經(jīng)常性的了,這和工作人員的責(zé)任心有關(guān),也和計(jì)算機(jī)輸入法有關(guān),當(dāng)然,更和人們對速度和效益的過度追求有關(guān)。三十年前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教師手里的油墨講義,如今恐怕都是遙遠(yuǎn)的記憶了,在當(dāng)代大學(xué)生心中更是空白。可惜這里不能使用圖片對比,否則將八十年代的教材、講義的圖片跟如今的教材作個(gè)對比,恐怕更有說服力,也更鮮明。
與理科類教材內(nèi)容具有一定的穩(wěn)定性不同,文史類教材的更新變化要更快一些,教材和教學(xué)內(nèi)容變化大的,就是中文系的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了。中國的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不過百年多,但這方面的歷史書寫卻一直是變化多端的。記得八十年代采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是唐弢主編的,三卷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出版,1979年原版,1984年再版。整個(gè)印刷質(zhì)量上與當(dāng)下各版本相比明顯粗糙得多,當(dāng)然在書價(jià)上也是翻了幾番,從那時(shí)的幾角錢到今天的幾十元。
九十年代出現(xiàn)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教材,最具影響力的、并被廣泛采用的就是錢理群等三人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三十年》,經(jīng)過一再修訂、再版,出版社也歷經(jīng)上海文藝出版社到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列為“教育部重點(diǎn)教材”,2011年列為“國家級規(guī)劃教材”,并得到重新修正。這部教材是由當(dāng)時(shí)國內(nèi)頂尖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方面的專家編著的,學(xué)術(shù)性較強(qiáng)。特別是在編寫方面,明確了三個(gè)十年的歷史分期,并明確界定了現(xiàn)代文學(xué)的發(fā)展歷史是1917—1949年。
隨著重寫文學(xué)史問題的提出,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方面的教材就出現(xiàn)了各種版本,包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程光煒等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劉勇等編著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孔范今主編的《新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朱棟霖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精編》等,以及東方出版中心出版、王曉明主編的《二十世紀(jì)中國文學(xué)史論》,后兩種教材明顯采用大文學(xué)史觀,將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的時(shí)間跨度算為從1917年起到二十世紀(jì)末,將以往所說的當(dāng)代文學(xué)史涵蓋在其中。不同的教材編寫者自然有自己的在內(nèi)容編選上的考量,因本人非文學(xué)研究方面的專業(yè)人士,僅從歷年任課教師選用的教材版本的變化做個(gè)大概的描述。
隨著現(xiàn)代文學(xué)史教材的變化,當(dāng)代文學(xué)史的教材也不斷在更新。可想而知,八十年代的當(dāng)代文學(xué)史無論在觀念還是容量上都是陳舊的。最早采用的是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初稿》,上、下二冊。進(jìn)入九十年代后,就出現(xiàn)了各種版本,洪子誠版的《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陳思和版的《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教程》、孟繁華與程光煒版的《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發(fā)展史》是教師們選用最多的三個(gè)版本,可見其權(quán)威性很高。
相對于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史教材的可選擇的豐富性,中國文學(xué)史和外國文學(xué)史的教材版本相對來說就要少得多。較早的《中國文學(xué)史》是游國恩主編的,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出版,共計(jì)四冊,后來出現(xiàn)了也是四卷本的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xué)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外國文學(xué)史則一直采用朱維之主編的版本,因?yàn)椴粩嘣谛抻啠霭嫔缫彩遣粩嘧兓A硪粋€(gè)偶爾被教師們采用的就是鄭克魯主編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外國文學(xué)史》了。當(dāng)下的外國文學(xué)史教材與早先的相比,主要的變化就是增加了大量二十世紀(jì)的文學(xué)史分量,尤其是二戰(zhàn)后很多作家作品已經(jīng)進(jìn)入到文學(xué)史,也即歐美文學(xué)史的時(shí)間跨度是從古希臘到二十世紀(jì)末。相對來說,《中國文學(xué)史》則保留了相當(dāng)?shù)臅r(shí)間穩(wěn)定性,
相對于文學(xué)史教材的不斷變化,語言類的教材則保持了相對的穩(wěn)定性。《現(xiàn)代漢語》從八十年代以來就一直采用的是黃伯榮、廖序東主編的版本,當(dāng)然已經(jīng)經(jīng)過四次修訂。《古代漢語》也是歷經(jīng)幾十年仍在采用王力主編的版本,由此可見這兩種教材的權(quán)威性地位一直沒有被撼動。
閑來翻閱不同時(shí)期的教材,雖不能從專業(yè)的眼光和角度進(jìn)行研判比較,但從教材中所折射出的時(shí)代感還是相當(dāng)明顯的。尤其是文史類教材,只要是接受過一定教育的人,都能夠看得懂,雖不能從學(xué)術(shù)的高度對各個(gè)版本的優(yōu)劣進(jìn)行比較分析,但這類教材所表現(xiàn)出來的與時(shí)俱進(jìn)的歷史面貌,相信大多數(shù)讀者都能夠看得出來,但同時(shí)也有某種發(fā)人深思的東西蘊(yùn)藏其中。真正在教科書里站得住位置的,還是要經(jīng)歷過時(shí)間的淘汰的。
經(jīng)過三十年的發(fā)展,教材的面貌可謂煥然一新,但學(xué)生對教材的心理和態(tài)度也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八十年代還處在相對匱乏貧窮的歷史時(shí)期,學(xué)生對教材的熱情和敬畏之情溢于言表,即便是要節(jié)省伙食費(fèi),也要購買教材。今天的學(xué)生則不然,能主動淘弄二手教材已實(shí)屬不易,更有不少學(xué)生寧愿節(jié)省下教材費(fèi)購買電子娛樂產(chǎn)品。在學(xué)生的眼里,更是完全看不出對教材的敬畏之心了,這是更加令人倍感悲哀的。這一方面是由于電子閱讀對圖書閱讀的沖擊,但還有一個(gè)教材本身的原因不能不引起重視,那就是由于利益的驅(qū)動使得部分教材在編寫上很粗糙、出版上很泛濫,讓其失去了以往的權(quán)威性,導(dǎo)致師生們對教材失去了應(yīng)有的信任和敬畏,這一點(diǎn)是要引起足夠重視的。
隨著電子閱讀的普及和教學(xué)手段的現(xiàn)代化程度的提高,特別是最新的教學(xué)模式——“慕課”(MOOC)的方興未艾,教材——這種承載著教育使命的一種圖書形式,在未來的發(fā)展會是如何,以及能否退出歷史的舞臺,還是個(gè)未知數(shù)。但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它不僅凝聚了幾代編寫者的心血,更是記錄了一個(gè)時(shí)代的歷史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