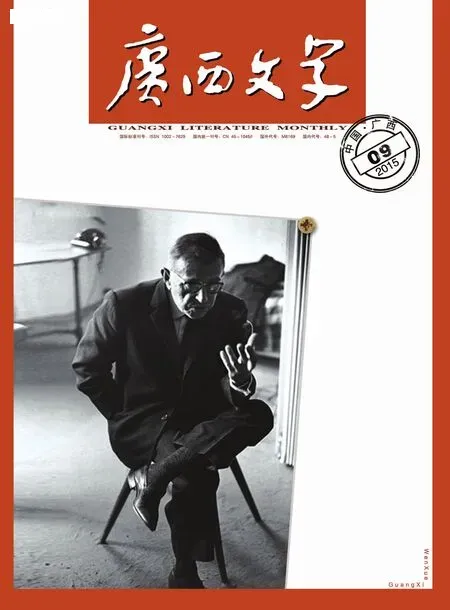《廣西文學》散文新銳專號述評
劉 軍/著
本期《廣西文學》所推出的散文專號若加以準確定位的話,則為廣西地方新銳散文專號。由人員構成可知,收錄的十六位作家,多集中于70后、80后兩個年齡段,極個別成員如廖蓮婷則為90后作者。兩個年齡段中,70后散文作家居多,有十二人之多。70后作家為何還要冠之以新銳之稱號,這要從這一代散文作家自身的尷尬地位說起。因此在評析文本之前,我想集中談談70后、80后兩個散文群落的寫作狀態問題。因視野所限,必有疏漏之處,懷抱“散文是大可以隨便的”的先賢之言,將其延伸為“散文觀點亦可以隨便言之”的談話原則,不周之處,懇請批評式的回饋。
首先需要申明的是,代際區分是一種疏懶的理論歸類方法,其學理性基礎并不穩固,一旦面臨真正的文學思潮和文學流派的發生,很容易坍塌下來。出于描述的方便,在本文中,姑且使用代際區分的方式來介入當下的散文寫作。70后散文群體地位上的尷尬源自其自身遭受擠壓的狀態。前有50后、60后的雙峰并峙,后有80后散文群落的崛起,基本態勢恰如凹陷于群山中的臺地,臺地上固然也有起伏之山丘,但自身旋起的旋風很難穿越周圍的山峰,抵達遼闊的遠方。50后、60后兩代作家大多成名于20世紀80年代,在那個文學的黃金時期以及啟蒙語境濃郁的氛圍里,一旦站穩腳跟,便很容易根深葉茂。因為這一時期不僅為文學寫作的黃金時期,也是文學傳播的黃金時期,文學話語其時作為政治話語的有力補充,它對社會話語的介入之深,其他話語皆難以比擬。不過,在這個黃金時期內,散文文體的冷寂及自我窄化卻貫穿始終,然而并不妨礙在其后的時段內,部分成名的小說家、詩人偶有涉足或側身散文寫作領域所掀起的狂風巨浪。實現文體寫作轉身的有小說家史鐵生、詩人劉亮程、戲劇史家余秋雨、詩人北島、小說家張承志、詩人蔣藍、學者周國平、詩人周濤等人,偶有涉足卻大放異彩者則為數甚多,如賈平凹、張煒、王安憶、于堅、李皖、費振鐘、楊永康等。上述諸位基本歸屬于50后、60后兩代,他們分別在散文大概念下的某個領域內取得極大的成就,如劉亮程的詩性散文、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賈平凹的性靈散文、費振鐘的文史隨筆、楊永康的新散文、史鐵生的哲理散文。近二十年來,始終恪守散文場域未有越界者,僅有林賢治、周曉楓、張銳峰、筱敏、鮑而吉·原野、艾云、祝勇、耿立、王開嶺等人。人員構成上也基本上是50后或60后作家。這兩代人所擁有的學識、閱歷、資源這三大因素,如陡崖般樹立在70后一代面前。不單有前面陡崖的聳立,70后散文群落還遭遇了后有追兵的局面,這個追兵就是正在崛起的80后新銳散文群體。他們中的一些人,比如草白、吳佳駿、阿微木依蘿、喬洪濤、王威廉、朱強、胡竹峰等人,在各自的寫作實踐中,皆取得不俗的成績。其中草白獲得了臺灣《聯合報》新人獎,朱強和胡竹峰兩位則是《人民文學》新人獎獲得者。80后集體崛起的后面是相對自由和寬松的社會語境,在才、氣兩個因素的表現上,與60后、70后相比較,更加透亮和逼真,無論經驗的傳達還是個性呈現,或許是受到思維認知以及藝術清規戒律的束縛較少,他們更勇于直面自我與現實間的關聯。這種返諸自身的觀照方式,彰顯出后現代語境里中心崩塌之后重建主體的努力。此外,就成長歷程而言,他們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人生的啟蒙,在新世紀之后奠定各種認知的維度,市場化、媒介影響、娛樂等元素不自覺地滲透到他們的精神血管里,順從、妥協、對抗的對象相應也發生了巨變。因此,他們的書寫,拋卻了鄉土和抒情兩種常見之路徑,烙下的恰是流動性社會進程的種種印痕。
當然,70后散文群體一直嘗試著以文體探索的形式改變自我前后夾擊、散兵游勇的生存狀態。新世紀之初,新散文論壇的發起人馬明博利用論壇的影響力,提倡散文的無邊界性寫作,并組織出版了《新散文十五家》《新散文百人百篇》兩本圖書,與祝勇、張銳峰等人提倡的“新散文運動”相呼應。同屬于70后的塞壬、傅菲、閆文盛、范曉波等人,則是其中的積極實踐者。楊獻平、黃海等人,則利用原散文論壇、大散文論壇、散文中國論壇,提出“原散文”的概念,倡導散文寫作的紀錄片風格。四川的兩位70后,張生全和沈榮均則致力于“在場主義”的推介,他們分別是《在場》刊物的編委之一和“在場主義”散文獎的評委之一。要言之,新世紀以來各種新的散文理念的后面,皆可發現70后群體活躍的身影。盡管部分散文新實驗在理論建設上未取得充分的擴展,在創作實踐層面也存在脫節和錯位的情況,不過,70一代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散文的基本格局,進一步推動了去中心化局面的形成,同時也為散文文體的邊界拓寬積累了充分的經驗。換一種說法,70后散文群體尚處于成長期,尤其是一些民間寫作者,他們以自發性訴求以及內心的虔誠信仰,構建了散文寫作的純粹性因素。而純粹性恰恰是當下文學語境中極為稀缺的東西。散文是一種偏于老年的文體,對于學識、閱歷、思想沉淀、靈魂的境界有著特殊的要求,基于此,將諸多地方性70后散文作家冠之以“新銳”稱號,并不為過。
下面言歸正傳,進入具體文本的解析層面。本期專號中,劉景婧的《天堂圖書館》以夏、秋、冬、春為標簽,書寫主體與他者相互碰撞并展開靈魂對話的過程。以夏為開篇,這是因為作為四季之一的夏天,其具備的烈度與杜拉斯構成一種隱喻關系。盡管有不少中國作者對杜拉斯展開了多向度的解讀,有一個事實卻必須直面之,即解讀和解讀者皆容易隱沒,而杜拉斯依然如此清晰。同樣作為女性,杜拉斯對于文藝青年而言,所產生的影響如其本人一般,有著足以致命的“毒素”。或者可以這樣說,杜拉斯及其作品不大適合承擔啟蒙者的角色,但足以打開另一個世界。心中若有足夠的熾熱,與杜拉斯,與她十七歲時的愛情(裹挾著諸多惡的因素的愛情)之間的相遇,就成了某種宿命。秋之篇由祖母的死亡為引題,過渡到海子詩歌以及海子之死。其基本情感基礎為里爾克的一個判斷——死亡是生命的成熟。通過海子的詩篇,作者試圖重建一種生與死的辯證關系。冬之篇的主角是卡夫卡,這位孤獨、陰冷的小說家,擁有文學最本質的特性——偉大的詩性。他的內心如喪失一切星光的海洋,進入他的內心通道必然風險重重。春之篇則為內心獨白體,描述自我內生長的一個過程。四個小篇章歸為一文,可歸入文藝漫筆的體式,其書寫方式從特性上看主觀性甚為強烈,這種主觀性非我向性的主觀性,而是因客體的碰撞而產生的投射性書寫方式。而這種強烈的主觀性也決定了行文的高蹈,一種語氣、一種聲音取代了散文錯落有致的結構,很容易造成散文書寫的虛空,這應該是作者以后的寫作中要注意的問題。
唐女的兩篇散文具有很強的發散性,經驗、記憶、現實三個因素相互穿插,隨性而發,思及則筆及。結構上的散漫加上篇幅的長度,使得此類散文不大容易掌控,不過作者似乎擁有自己的秘密武器。這武器在我看來有三,其一為發達的感覺主義系統。文學中的感覺主義系統或者來自天賦,或者來自后天的藝術熏陶。一旦形成就會浸透到文字書寫的任何一個碎片之上。也因此,作者在充滿灰霾的山西之行中能夠洞見一只喜鵲的叫聲,在匆匆行色中癡迷于小牛犢吃奶的過程。其二為作者自身所具備的靈氣。靈氣訴之文字,就會形成寬窄深淺不一的顏色。靈氣在散文中的呈現不是彌漫的,而是偶發的,倏然跳脫而出的語詞抑或句子就會使得文章的氣息峰回路轉。《世說新語》所記載的“頰上三毛”之典故,即為如此。如第二篇散文中作者寫到故鄉的越城嶺,云霧纏繞下的山峰,使用了“薄”和“柔軟”這兩個形容詞。其三為作者繪畫的專業背景。這一要素與感覺系統及凸顯的靈氣遙相呼應,同時也對其書寫形式產生影響。紙張上有跨度的涂抹與散文書寫的發散性有著內在的相通性。除此之外,作者在兩篇文章中彰顯出的植物學、動物學、地質學知識,也是可圈可點之處。知識考古學乃散文從業者的基本功,盡管這一基本功往往被當下急功近利的寫作現狀所忽略。
作為2014年度華文最佳散文獲得者,林虹的敘事能力毋庸置疑。《釘子被移來移去時》在行文上老練而從容,這篇散文圍繞舞劇《瑤妃》的編劇及創作構思而展開。就敘事進程的把控而言,可謂收放自如。比如收的方面,場景和細節的剪裁簡潔流利,歷史深處的瑤妃,賓館前臺的服務員,賣楊桃的鄉下大姐,耄耋之年的母親,還有漫步沉思中的“我”,這些人物皆被巧妙地串聯于“行走”的生活態度之上。而放的方面,如果把散文寫作比喻成植樹的話,作者相當注意樹冠的蓬松情狀,在主干之外,蟬的鳴叫也好,鳥的叫聲也好,賣楊桃女人的膚色也好,瑤鄉的行走也好,皆輕易鋪展開來。這種旁枝逸出的寫作方式一方面彰顯了散文的自由精神以及結構靈活的特點,另一方面也體現出寫作主體技術方面的自信程度。收放的自如,使得作為讀者的我們一旦和這樣的文字遭遇,就會有舒服和放松之感,而一旦再往深處行走,陡生一絲惘然,這惘然或許是來自作者路數上的討巧吧。
寒云的《風把什么吹走》兩章,為鄉愁和親情題材的疊加。親情題材容易上手,同樣也容易陷入劉勰提及的“為文而造情”的泥淖。新世紀以來涉及親情題材所出現的撕裂式的、反向的寫作范式,實際上就是對真情實感論的一種矯正。從技術處理上看,作者避開了苦難敘事的常見路數,對家族中的兩位女性,姑媽和祖母,延伸到村莊和鄉土文化的坐標系下加以觀照。兩位不幸的寡婦,其生活史當然充溢著苦難,而作者筆觸的焦點卻在于這兩位再普通不過的女性對于村莊生活的重要性,比如姑媽的竹曬坪和她胸中源源不斷的故事,比如祖母敬天地、事鬼神的生活細節。她們的離去使得村莊的記憶格局和人倫格局被改組。也正是通過坐標系的拉伸,進而取得審美上的間離效果。從語言傳達的層面來看,作者的敘事過程一直以拙語為主體,看上去平鋪直敘,少有光澤和跳躍,卻能夠去偽存真,將家族中兩位女性的本真細節加以再現。不過,作者的引子部分與后面的行文并不統一。第一刀下去,切口深,可見出詩歌寫作的專業背景,后面的刀法那么慢,看似清淺,卻吻合舊時光的滴答聲。
《父親書》之前,我讀過梁曉陽的伊犁題材系列,其中的《從春末到秋初的勞動》一章,有泰山崩于前之感。之所以使用這么高的評價,是因為梁曉陽是位真正親近泥土的作家,其伊犁題材系列致力于修復業已斷裂的人與天地間的交互關系,而文字上的淡然和釋懷,與陶淵明的躬耕傳統相對接。與伊犁系列對比鮮明的是,《父親書》的書寫過程伴隨著緊張和焦慮,這也使得文本的基調偏于沉郁。這篇散文既是寫給承受苦痛的受難的父親,也是寫給自己那段青年時期動蕩輾轉的歲月,復線寫作的手法使得文本趨于豐厚。
由朱塞佩·托納多雷執導的《天堂電影院》是電影史上的經典名作,一座小鎮,一個孩子和一個放映師的故事,實際上構成了整個意大利藝術電影發展的縮影。三十載的光陰在很多電影中或許僅是一個服務劇情的索引,但《天堂電影院》卻將時間賦予了電影院這個電影不可或缺的載體以滄海桑田的人間百態,每個人都擁有屬于自己的美好,但這份美好卻無以化作永恒終會成為記憶,誰的人生又能是完美無瑕的呢?其實我們心中都有自己的一家天堂影院。上面這段話可以用來評述電影,也可以作為黃慶謀散文《眸眼深處影千重》的注腳。文本中,黃慶謀用生動的筆觸講述少年時候的觀影故事,在城市里,觀影對于普通觀眾來說,作為消遣、休閑的活動而存在,即使沒有電影院的存在,依然有其他的替代品完成休閑消遣的功能。而對于身處巴額寨子里的“我”來說,電影或電影院本身就是強大的能指,可借以完成童年時代對“世界”的窺探,如維特根斯坦所言:“想象一種語言就是想象一種生活方式。”也因此,電影比吃肉、比求學重要得多。另一方面,作者盡管沒有將小說化的片斷帶入散文文本之中,但其自身講故事的能力以及直感的能力,使得記憶中的重要片斷被照亮,同時也將他者的故事融匯進去,打造了一條豐沛的河流。
羅南的《豁口》與梁曉陽的《父親書》在題材上相似,皆是圍繞父親的離世展開記憶的掘進,以細節照亮現實。但在具體處理上卻差異甚大。《豁口》一文的節點是死亡及其儀式化的過程,以此延伸出存在之問。作品中關于死亡儀式化的細節再現相對繁復和翔實,而生和死的儀式化恰恰是傳統文化的核心組件,人們通過這個過程完成生命意識的啟蒙,完成祖先崇拜下的家族記憶以及文化的傳承。而且,儀式并非為一次性完成,而是循環往復,隨歲月的遞進,身處其中的我們逐漸領會其間的含義。所以具體到這篇散文中,作者首先呈現的是祖母和六堂哥的死,然后才是父親的離世以及二姐在死神逼迫之際的反應。另一方面,《豁口》的敘事風格趨于銳度和力度的結合,閱讀的前半段,我一直有一種錯覺,認為是男性作家寫就。散文即人,此處的人指向的應該是主體的文化個性了。
陶麗群的四篇散文走的是鄉土書寫的路子。卻并非如通常所見,通過描摹器物、人物、事件等,向內灌注鄉愁和依戀之情,而是從情感場域抽身而出,進入現實關懷的層面。家國訴求為鄉土小說寫作所常見,即使落定到散文中,則大多有隱微的趨向。其實,家國訴求不分文體,寫出關心糧食和蔬菜詩句的海子,我們不會將其誤認為恬淡的田園詩人。盡管新世紀以來,家國訴求往往被批評界認定成宏大敘事之一種,并加以消解,但我個人認為這一訴求的后面挺立著寫作個體的情懷和立場。將散文定位成柔軟文體,無疑是一種井底之見。北島、高爾泰、王開嶺,這三者的散文堪稱大品,決定性因素何在?乃情懷與價值立場使然。當然,與小說中借助人物性格及命運來加以表現不同的是,散文中的家國情懷需要立足于作家個人真實的情思之上,這是最基本的物理基礎,并借助具體的場景加以寄托。雕刻這些場景需要細部刻畫的能力,陶麗群的這幾篇,除了《深夜的火車》稍弱,其他三篇皆很結實。老宅一篇涉及家族內部的戰爭,讓人反思傳統觀念、鄉俗之丑陋的一面,另外三篇則觸及鄉村空心化的現實,這現實是由茂盛或荒蕪的菜園、鄉村老人寂寞的死、門戶上的鐵鎖、地里的莊稼等,奠定地基。
廖蓮婷的兩篇散文將敘事的焦點集中于人物之上。新世紀以來隨著敘事散文的勃發,人物題材散文隨之茁壯。這類散文在藝術處理上注重發掘對象身上的故事元素和經驗元素,以此觀照出獨特的生命獨在的狀態或者社會關系的縱深區域。就審美指向方面,因為涉及人和社會兩個著重點,與小說更為靠近,但是兩者還是有著顯著的區別,人物散文更注重微小單元的刻畫,由此引申出“我看”“我想”之“我”的特性,其中寫作主體與對象間是相互吁請、相互激發的關系。而在短章式小說的處理中,情感關系處于可有可無的狀態,“我”是要被隱藏起來的,主體與對象的呼應關系大致處于被取消的狀態。《背影消退之處》由家族中一位“爺爺”離去的背影作為切口,激發起“我”探究家族歷史淵源的熱情,并遠足他處,在家族親人的相互探尋中發現血脈的相似情狀。《沒有靠岸的人》一篇述說一位文友的顛沛之旅。一個人的故事,只能稱之為起伏而無法命名為傳奇的人生故事,幾次相見的片斷,卻隱喻了純文學落寞的命運,以及理想與現實之間充滿相互傷害的關系結構。兩篇相比較,還是第一篇在細節和場景的鉤沉上更為準確和有力。
李海鳳的《青年看老年系列》包括三篇散文,第一篇和第三篇所寫對象為不熟悉之人,為了營造某種心理場,使用了代物懸擬的手法,而這種手法與散文的“我見”“我思”的特性相抵牾。第二篇敘及的對象為熟知的鄉土人物,因此顯得自如很多,但總體來看,這個系列的寫作普遍存在隔的現象。造成隔的原因在于作者始終處于人物心理的外圍,筆力因素(案例為作者的行文方面,許多語句的最后一個字為“的”“的”“了”等字放在句子結尾乃語句不夠簡潔,缺乏張弛有度的標志)加上散文真實性的要素使得作者難以深入進去。
宋先周的《疼痛時光》寫的是自我的青春經歷,其間的情感萌動、焦慮、孤獨以及生命意識的大面積蘇醒皆訴筆端。記憶重現式的寫作,亟須王國維所言的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人生境界,入乎其內意味著個體體驗的深度,出乎其外意味著因觀照而獲得的某種亮度,如清水濯洗過的草地,自然沖刷掉蕪雜的東西。對照此篇散文,入的方面做得不錯,出的方面尚欠火候。
孟愛堂的《天使的歌唱》 《村莊上空的音符》可歸類于傳統的抒情散文,20世紀九十年代,學者劉錫慶將其命名為“藝術散文”,以凈化散文的文體。這種類型的散文,對于語言、結構、意境三個因素要求極高,三者的和諧統一方能使情思生發出一唱三嘆的詠嘆調。兩篇文章的立足點皆在于對生命的憐憫與珍惜,戛然而止的四歲的燕燕、玉江奶奶、黎小妹等人,在生命的困頓中保持一種努力提升的姿態。肉體也許會萎縮,會因為疾病而弱小,但比肉體更加不可思議的是精神。貝克萊指出,存在就是被感知,所有的生命,無論性別和其他,其實可以建立一個共同的通道,作者的散文寫作,恰恰就是往這方面的努力。
陳洪健《喜鵲飛往天堂》與寒云《風把什么吹走》兩者在題材上趨同,皆為家族敘事的類型,且敘事的對象都落定在“祖母”身上。不過,兩者的敘事方式卻大有不同,寒云走的是外圍切入的道路,扮演著離去—歸來的形象。而陳洪健選擇了由內而外的生發,仿佛置身于事件內部,將祖母、大姑、七姑的故事近距離地剝開并還原。其敘事非常有力,從祖母的少女時代開始,帶入南桂大地鼎革前后的歷史與民情,講到她的努力生育,她和孩子們的關系,以及她如何一步步確立精神的權威。對禁忌的確立,對村莊人倫關系的積極介入,則顯示了其智慧的一面。家族敘事一旦突破了善的層面,進入智的層面,其文化觀照意義自然凸顯。所以這篇散文讓人很容易讓人想起湖北作家方方的中篇名篇《祖父在父親心中》,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
顏曉丹的兩篇作品讀來讓人喜歡,軟性的筆觸,寫出來的卻非軟文。她的作品里面女性的氣息比較濃郁,濃郁的原因不在于敏感與多思,而是因為有一種特別的觸覺在里面。具體而言,此處的觸覺對應著作者本真人格下的善意和包容。所以在文本中,她對瑤族小伙子的舉動有著準確的感知,對周圍鄰居活潑的民間言談甚為好奇,對執拗的父親充滿理解,對雕刻師的絕技大為贊賞。她的散文里有著自我明亮的生活態度,這種生活態度沒有必要拔高,但是不虛偽、不做作、不世俗,已經非常難得。另外,善意可能出自本心,容易抵達,而寬容的生活態度,卻是當下浮躁的社會語境中最為稀缺的東西。
羊狼的《絲路三千里》與他者的鄉土或者親情題材有所不同,水上絲綢之路湮沒了諸多的歷史煙云、人物傳奇,如果以人文地理的視角深度切入,以地方志書寫的形式呈現,并仔細考證材料,從中自然可以發掘出歷史細節的奇光異彩。遺憾的是,作者將這個系列處理成了抒情的篇章,尤其是第一篇,似乎成了加長版的散文詩。上揚的調子以及蹈虛的話語風格,消解了文本中的地理、人文、歷史的重量。
楊仕芳的《月滿西樓》篇,題目上容易讓人想到易安居士的“月滿西樓,獨上蘭舟”句,實則兩者之間往相反的方向奔跑,李清照的詞句清麗可人,即使有憂愁,也是淡淡的,哀而不傷的憂愁,或者說成為文藝式的憂愁也可以。而楊仕芳筆下的月滿西樓,卻是一根針刺,刺向人們內心中最柔軟的地方。因為對生命有了透徹的理解,所以這篇文章透出幾分悲涼。一座木樓,幾許故事!其中有幼子身上嚴重的依賴感,以至于小小的他做出大人難以理解的舉動,面對如此情景,作為父親的“我”非常無奈,又必須承受。有阿杰以命相搏的自尊,有木樓居民群體的分化,也有自我在寫作道路上的回望和體悟。或許是直筆書寫的緣故,使得文本中充溢著難得的坦誠。當然,若從閱讀接受的層面加以考察,這樣的散文一旦遭遇,就能判斷出作者顯然是受過系統寫作訓練之人。作為最后的補充,此文在行文上有個小小的缺點,即“了”字出現在很多句子的結尾,雖是小節,但也極大地影響了文章的氣韻。
本期散文專號在題材上相對集中,鄉土和親情書寫占據極高的比例。如果從地方省份的角度出發,這未免有些窄化,畢竟,文史隨筆、思想隨筆、性靈小品大有作為,且新世紀以來,隨筆類散文影響極大。在此希望廣西能夠涌現出多元化的散文寫作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