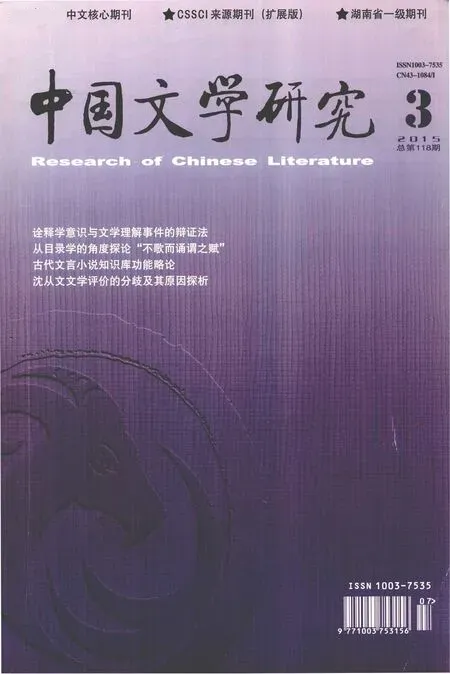那一代人的“怕”與“愛”——論《雷雨》的情感倫理
唐 偉
(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湖南 長沙 410081)
在談及《雷雨》的創作發生時,曹禺曾坦言,“寫《雷雨》是一種情感的迫切的需要……《雷雨》是一種情感的憧憬,一種無名的恐懼的表征……這‘怕’本身就是個誘惑。”,觀照整部話劇,我們不難發現,曹禺所言的“怕”以及“情感的憧憬”不僅構成《雷雨》創作的內在動因,其實也是《雷雨》作為敘事詩的結構法則。也就是說,勘察《雷雨》的人物心里圖景,我們同樣會發現這種難以言說的“怕”及“情感憧憬”也如影相隨地傍著話劇人物始終——毋寧說劇作家就是以一種象征寄托的方式,將創作主體心里投射在了蘩漪、周萍甚至是話劇所有人物的身上。換言之,在《雷雨》中,劇作家和話劇人物取得了某種同構的心理形構。因而,從這一意義上說,對劇作家的“怕”以及所謂“情感憧憬”的內涵探究,就不再簡單的是一個創作發生學的策略闡釋,同時也是向話劇人物心理縱深挺進的迫切需要。
“怕”和“愛”的耦合
《雷雨》人物的“怕”,在話劇的一開場就被凸顯了出來。在話劇的第一幕,從魯貴詳盡的敘述中,我們得知了周公館鬧鬼的事實,公館鬧鬼為接下來出場人物的“怕”做了最好的注解。從最日常的生活角度說,人怕鬼,怕那些實則并不存在的亡靈與精怪,反之似乎亦然,鬼也怕人,也見不得人。雖然,周公館的“鬼”不能以實存本體的方式來理解,但如果從“鬼”是人之所怕的對象這一角度而言,稱周公館鬧鬼其實并非無稽之談——《雷雨》中的“鬼”當然不是猙獰恐怖的青面獠牙,而是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換言之,“秘密”是周公館里鬼的肉身。秘密的生成以及最終暴露,即是《雷雨》中“鬼”的現身及活動過程。
話劇中的第一個“鬼”出現在周萍和蘩漪心里。當兩人的亂倫成為既定事實之后,他們兩人的“怕”也隨之產生,二人心里有了一個共同的“鬼”:無論是蘩漪面對丈夫周樸園和兒子周沖,還是周萍面對父親周樸園和弟弟周沖,懷揣不可告人秘密的二人有著共同原始本能的怕,他們怕東窗事發而受到道德上的嚴厲譴責以及身體上的嚴酷懲罰——而從根本上說,這種怕乃源自其所承受的人類對于最原始懲罰的畏懼。周萍和蘩漪觸犯的是人類最古老的亂倫禁忌,弗洛伊德認為,“對于人類最早的刑罰體制我們可以遠溯到禁忌時期”,禁忌本身“包括了神圣的和超出尋常的及危險性的等意義。”當包涵危險的禁忌像潘多拉魔盒那樣被打開之后,禁忌的嚴懲會找上門來,肇事者的怕也就隨即產生。周萍和蘩漪顯然知道,如果奸情敗露,父子關系、夫妻關系、兄弟關系將會遭受毀滅性的打擊——他們實在不敢想像,那將會是怎樣一種不堪的后果。但在《雷雨》中,有意思的是,觸犯亂倫禁忌的肇事者,對刑罰的怕本身,其實是源自另一種怕的催生,換言之,亂倫的發生很大程度上也是“怕”本身催化作用的結果。
追溯周萍和蘩漪的亂倫心里根源,二人的媾和其實不單是出于兩性間的吸引,周樸園的蠻橫專制也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蠻橫的父親面前,軟弱的周萍畏懼有加,但敢怒不敢言,他怕嚴厲的父親,即使內心存有反抗念頭,也不敢公然挑戰父親權威。但不能公然正面挑釁,并不意味著在其潛意識里不存在反抗意念。在弗洛伊德看來,“女人被視為反抗父親的起點”,在弗氏對古希臘神話的分析中,他認為像Attiis,Adonnis 和Tammuz 等神的觀念的產生,其實就是“為了違抗他們的父親而與母親有親密的關系”,也就是說亂倫具有反抗父權的指向寓意——從這一意義上說,風流成性的周萍,即使不是有意識、有預謀地通過蘩漪來反抗嚴父,至少也在亂倫之后得到了一種象征式的弒父滿足。而對蘩漪來說,“在監獄似的周公館,陪著一個閻王十八年”,面對周公館唯一合法的專制者,面對她那威嚴得不近人情的丈夫,蘩漪自然也是畏懼三分,對這個崇尚自由的女人來說,反抗夫權是情理之中的事。簡言之,周萍和蘩漪相互的男女之愛里都包含著“怕”的成分——對周樸園的畏懼,兩人也最終因反抗共同“敵人”的需要而暗通款曲走到一起。
如果說周萍和蘩漪的“怕”,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他們畸形的愛的發生,那么三十年前的周樸園和魯侍萍,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類似的怕而葬送了兩人原本美好的愛情。從周樸園的家庭格局布置及他跟魯侍萍三十年后見面時對當時魯的評價來看(很賢惠,也很規矩),我們不難看出當年周對魯的至深情感。由劇本所知,周樸園和魯侍萍的關系是因雙方身份的不對等而遭到周家極力反對。這里潛藏的一個問題是,既然周氏家長極力反對他二人的來往,那么,為什么魯侍萍在第一個孩子出世時沒被趕出門而要等到第二個孩子出世才被周家掃地出門?唯一的合理解釋是,在魯侍萍的第一個孩子降生至第二個孩子出世期間,盡管兩人關系遭到周氏家長的極力反對,但周樸園一直都在努力向父母求情以爭取對他和魯侍萍關系的認可——周樸園顯然不忍心將和自己有了愛情結晶的魯侍萍掃地出門。而在他們的第二個孩子出世后,可以想象,無論周樸園再怎么努力爭取,最終還是未能頂住周氏家長的壓力,因害怕觸犯家長制權威和周家利益而不得不忍痛拋棄侍萍。他們兩人的愛,最終也因“怕”而被迫中斷了結。有意思的是,三十年后,因怕而中斷的這段愛則又衍生成彼此心里的另一種“怕”。
在《雷雨》中,周樸園的心里有兩種類型的“鬼”:第一類是魯大海所說的“礦上死的工人”,這類鬼或許由于周作為一名民族資本家的良心發現而現形,但他所擔驚害怕的并不在此;糾纏他的是第二類或者說是第二個鬼——這個“鬼”遠在南方無錫,但卻形影相隨地跟了他三十年,這個“鬼”既是他的心里負擔,也是他的情感寄托,特別是在面對長子周萍以及現實生活中并不太美滿的婚姻時,這個“鬼”更是成了他心中一個永遠的牽掛,他對遠去的侍萍是既怕又愛。盡管魯侍萍三十年前被周家無情地趕出家門,但從三十年后她和周樸園見面時的對其稱呼中,我們也不難發現她對周樸園仍飽含著當年的深情,“樸園,你找侍萍么?侍萍在這兒。”魯侍萍離開兒女去幾百里遠的異地謀生,并非那里有更適合她的生計,而是她心里藏有一種深刻的隱憂——她怕在住居地見到她仍愛著的周樸園——她顯然知道魯貴就在周公館做事。她的怕里包含著蘊藏發酵了三十年的愛,也就是說,三十年前的那段愛成了二人心中共同的怕。
可以看到,《雷雨》人物的怕和愛是互為因果緊密纏繞在一起的,或因怕而生愛,或因愛而生怕。除了周樸園/魯侍萍、周萍/蘩漪的愛—怕交織外,周公館其他人也概莫能外。單純的周沖愛得熱烈,但“他愛的只是‘愛’,一個抽象的觀念,還是個渺茫的夢。”,在對四鳳的思戀中,周沖同樣也擔心害怕——他怕父母的反對,因此在跟蘩漪說出自己喜歡的女孩以及向周樸園請求將自己的學費分出一部分給四鳳的時候,他顯得猶疑不定戰戰兢兢。而心地善良,本分質樸的四鳳在周公館兢兢業業,心里本無“鬼”的糾纏,可由于和公館大少爺之間不對等的戀愛關系,她也開始擔心害怕,在即將見到要回家的母親時,她內心的“鬼”開始現形了:我的媽最疼我,我的媽不愿我在周公館做事,我怕她萬一看出我的謊話,知道我在這里做了事,并且同你……,面對既定的事實,作為一名孝順的女兒,四鳳的良心因沒聽媽媽的話而受到譴責,她覺得背著母親在周公館做事而對不起她。四鳳的“怕”,源自其內心的良善和一個孝順子女的本分。愛/怕的糾纏推動《雷雨》劇情的發展,更深刻的則在于這種感情憧憬直接影響著人物的性格形成。
有論者指出,從一個女人的角度來說,蘩漪“這類女人總有她的魔”,“蘩漪一方面是‘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經歷了苦難,可同時又是一個魔鬼”,但需要進一步解釋的是,為什么這類女人會“總有她的魔”?為什么說蘩漪是一個魔鬼呢?蘩漪的魔性是與生俱來還是后天生成的呢?顯然,“魔性”或“魔鬼”仍是一夸飾性的說辭,它并沒有揭示出人物的內在心性本質。蘩漪魔性的存在,說到底還是與她的愛有關,“愛與嫉妒結合時,給人以魔性,甚至把人變為暴君,這在女子那里常可發現。”,在周萍那里,蘩漪激發起一個女人內心強烈的愛,而四鳳的出現又讓她妒意叢生。與其說魔是自始至終附在蘩漪身上的,不如說愛和嫉妒都是人的原始本能——作為女人的蘩漪有嫉妒的本性并不奇怪:當周萍變心由當初喜歡自己轉而喜歡四鳳時,蘩漪的嫉妒之心就被激發了出來——四鳳的年輕和單純已不是她所再能擁有的,“假如有人想象著他所愛的對象與另一個人結有相同或更親密的交誼,勝過他前此獨自與他所結的友誼,那么他將恨所愛的對象,并且嫉妒那另一個人。”需要指出的是,此時的蘩漪盡管對周萍已懷有某種恨意,但除了對四鳳的嫉妒之外,她仍然抱有期待對方回心轉意的幻想,仍一如既往的愛著周萍。換言之,嫉妒并不純然是否定性的破壞,正如耀斯在分析《追憶逝水年華》時所指出的那樣:在普魯斯特的長篇小說《追憶逝水年華》中,每當期待的東西得以實現,愛情之火總會熄滅,而當嫉妒使人想象心上人為他人所占有時,愛情重又萌發。在亂倫成為既定事實之后,對蘩漪、周萍二人來說,其實最為迫切的已不再是愛情的經營,而是如何來面對他們的家人以及怎樣來防止奸情的泄露。四鳳的出現讓蘩漪妒火中燒,在看到周萍另有新歡之后,于是重又燃起了強烈的愛情火焰,從而將所有的種種顧慮拋之腦后。
如果說嫉妒與愛的結合,只是催生了蘩漪魔性的生成,那么,嫉妒和愛的結合似乎還不足以導致其魔鬼邪惡本性的充分展露。對蘩漪來說,從魔到鬼進而成為一個不管不顧的“魔鬼”,除了嫉妒的天性外,她還被一種怕籠罩,如前所述,她時刻都在擔心害怕她和周萍的奸情被知情的魯貴給敗露出去,“最可怕的人就是被怕所控制的人。怕的作用是破壞性的。”,由前所述,她的怕源自對觸犯禁忌所招致懲罰的本能害怕。也就是說,是魔的召喚導致了鬼的現身,是愛、嫉妒、怕三重情感的混合交織讓蘩漪最后淪為了一名有著“復雜人性、充滿魅惑性的魔鬼”。
愛和怕的糾纏構成《雷雨》作為敘事詩的詩性結構法則。正如曹禺所說的“怕是個誘惑”那樣,對于《雷雨》里的周家人來說,不惟怕是個誘惑,其實還有個比怕更大的誘惑,那就是愛。“愛”和“怕”互為加強,愛愈濃,則怕愈深,反之亦然。當“愛”和“怕”的纏繞開始加速加深并越出常規,走向了非理性的失控也就在所難免了。
“怕”和“愛”的贖救
處在畸形的愛與非常態怕的縫隙間的人,墮入了痛苦的深淵,也淪為了情感的奴隸,服膺于一種虛空的幻覺,喪失了本真的主體性。如何恢復人自在的主體性來獲得贖救性的自由,《雷雨》一劇在最開始就對此做了暗示性的回答。
在話劇的序幕中,曹禺精心設置的背景音樂是巴赫的“High Mass in B Minor Benedictus qui venait Domini normini”,亦即著名的《b 小調彌撒曲》,這支宗教意味很濃的名曲在最后一幕收尾的時候再次奏起。對于背景音樂的選擇,曹禺曾說過“那點音樂是有點用意的,請設法借一唱盤,爾便會明白這點音樂會把觀眾帶到遠一點的過去的境界內,而又可以在尾聲內回到一個更古老,更幽靜的境界內的”,因此實有必要厘清這支曲子的紋路。
眾所周知,被譽為近代音樂之父的巴赫是巴洛克時期最偉大的音樂大師,也是最后一位把為教堂創作音樂視為最大關懷的偉大天才。在他的創作中,教會音樂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作為虔誠的新教教徒的巴赫,他一共創作了5首彌撒曲,6 首經文歌;為教會創作了5 年內每周禮儀所用的康塔塔(一種大型聲樂套曲)共200 首;在其創作的大量管風琴曲中,有144 首圣詠調。巴赫對教會音樂作出了杰出貢獻。在這些作品中,被視為巴赫代表作的就是《b 小調彌撒曲》。這首彌撒曲被認為是同類音樂中最深刻、最壯觀、最杰出的范例之一。它包括傳統的《天主矜憐頌》、《榮福經》、《信經》、《至圣經》、《羔羊經》5 個部分,共24 首分曲。其中滲透著新教的改革精神和人道主義思想。綜觀全劇,不難發現隨著劇情的跌宕起伏,其實這種安帖人心的宗教贖救意味貫穿了全劇始終。
我們看到在話劇第一幕的大幕拉開時,首先映入觀眾眼簾的是這樣一幕:
開幕時,四鳳在靠中墻的長方桌旁,背著觀眾濾藥,她不時地搖著一把蒲扇,一面在揩汗。
煎藥作為話劇人物動作來說或許并不稱奇,但背著觀眾煎藥這種刻意的設計作為話劇的第一個場景出現就有點耐人尋味了。也就是說作為話劇關鍵情節線索的“藥”一開始就被置于隱匿的場境,而其隨后所展開的劇情也的確如此:面對四鳳端上的藥,蘩漪感到莫名其妙,“誰說我要吃藥”,生病的人既然不知道自己有病需要服藥,這著實有點匪夷所思。既然是背著當事人抓藥,那么抓錯藥也就在所難免了,這也賦予了“藥”在劇中的另一個特性——錯位。《雷雨》中的藥因而就獲具了它的多重隱喻意味。現實生活中的“藥”是一種悖論性存在:既是病痛和不健康的征兆,而本身又寄予一種拯救和希望,生活中人們希望遠離它,但必需之時又不得不依靠它。我們知道蘩漪事實上的確有“病”,但并不是“老爺說的肝郁”這一生理疾病。作為一個正值中年盛期的女人,周公館的太太其實是心里有病。蘩漪年齡上比周樸園小一圈,兩人志趣又不盡相同,作為一個有追求的女人,無論是在精神上還是身體上,蘩漪都處于生命中的旺盛期,可在周公館她正當的生命欲求無從得以釋放,久而久之也就郁積成病。蘩漪病急亂投醫,她抓的是周公館的大公子這根救命稻草,并天真地以為周萍就是她的希望、是醫治她心病的最好的“藥”,但這無異于飲鴆止渴——就在蘩漪身心暫時性地獲得療救的同時,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亂倫包袱成了她心頭的新病,而這“病”又多了一個受害者——周萍。周萍“病”發之后感到后悔了,為醫治療傷他也開始了尋找救藥的過程:
“他見著四鳳,當時就覺得她新鮮,她的‘活’,他發現他最需要的那一點東西,是充滿地流動著在四鳳身里”,“現在他不得不愛四鳳了,他要死心塌地地愛她,他想這樣忘了自己,當然他也明白,他這次的愛不只是為求自己心靈的藥”。
很顯然,周萍不過是用一種逃避的方式來處理自己的病情。如果說蘩漪是有意地背著世人抓錯藥,那么周萍則是無意識地在毫不知情地情況下抓錯了藥。
對周萍和蘩漪這兩個觸犯亂倫禁忌的大膽肇事者而言,其觸犯禁忌所受的懲罰非但關涉他們自己,還牽連到了無辜的他人,“在早期,破壞禁忌所遭受的懲罰,無疑的,是由一種精神上的或自發的力量來控制:即由破壞的禁忌本身來執行報復。稍后,當神或鬼的觀念產生以后,禁忌才開始和它們結合起來,而懲罰本身也就自動地附隨在這種神秘的力量上了。”,《雷雨》中亂倫的再度發生——周萍和四鳳間的兄妹亂倫,即是由破壞的禁忌本身來執行的報復——這是周萍事先所沒意識到的。“隨著文化型態的改變,禁忌形成為一種有它自己基礎的力量,同時,也慢慢的遠離了魔鬼迷信而獨立。它逐漸發展成為一種習慣、傳統而最后則成了法律,可是‘埋藏在所有禁忌里的那種無言的命令,雖然因為隨著時間和空間而造成了無數的變異,可是它們的起源只有一個而且只有一個即:當心魔鬼的憤怒!’”,如果說禁忌里包含著“魔鬼的憤怒”,那么周萍和蘩漪對禁忌的觸犯顯然是驚醒了魔鬼的憤怒。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稱“雷雨”為“魔鬼的憤怒”似乎再貼切不過。
周萍和蘩漪一樣也沒對癥下藥,也就是說這兩副病急亂投醫所抓的藥都錯了位,也因此注定是無效的,而服錯藥的后果是當事人的“病”情進一步惡化。隨著劇情的推動,周公館里病人們的病情也愈加深重,而在人間藥物和救星都宣告破產無效的情況下,處在愛—怕深淵中的人究竟還有沒有得救的可能?會不會存在一種根本不同的新的救藥呢?我們發現當話劇的序幕大幕拉開時,觀眾所看到的背景布景恰恰是一座教堂附屬醫院,那是“藥”的集散地:不僅有作為實物的中藥西藥,更有精神救贖的藥方藥劑——彌撒和《圣經》。也就是說,在人間的藥物失效之后,作者試圖尋找一種天上的藥來醫治《雷雨》里有病的人們,用宗教的救贖來彌合有罪人的傷口,“倘若在刑罰和罪惡之間沒有某種使污濁凈化的東西,那么什么事情就不會有什么不同。這某種東西只可能是上帝。”,而對沒有信靠的人來說,怕是種永恒的生存狀態,“怕是被上帝遺棄的產物”,這就自然地把話劇主題由拯救上升到了救贖的高度。事實上,從某種意義上講,能震懾魔鬼憤怒的也只能是上帝。從這個意義上說,《雷雨》是越過了傳統民族文化的固有疆界,在尋求普世意義的人的終極救贖。
結 語
迫于情感需要以及被“怕”所誘惑的曹禺或許不僅僅在于通過一部《雷雨》來言明某種“郁熱”的生存困境,《雷雨》在觸及某一悲劇性人類境況的時候,其作者是否又想到了這一問題的解決之道呢?換言之,在《雷雨》中,曹禺是否想通過某種詩意的方式來暗示為誘惑所劫持的人的出路和希望所在呢?
人不惟是理性的動物,理性/非理性之類的二分之于人固然有認識論的意義,但顯然涵括不了人的本然存在。作為有著豐富情感的靈性存在,人從來到世上的那一天起直至歸附塵土的那一刻,無不行進在悲歡離合、生死愛欲的情感場域之中。“怕”和“愛”是人類最基本的感情。作為世間最靈動的情感主體,人體驗著情與欲的深度以及愛和恨所能企及的廣度,人性的復雜聚啟蒙與愚昧于一體,集此世的實在與彼岸的超然于一身。而對國人來說,人性除了熟知的理性和感性維度外,陌生的是,人性的深處其實還潛藏著某種不可言說的另一維度——神性。
畸形的愛與非常態的怕,在《雷雨》的詩性悲劇構成中起到一種結構性作用,依話劇的劇情發展來看,兩相融合交織而成的愛—怕情結是推動劇情發展的關鍵樞紐,“曹禺每個人物的心靈歷程,其實都是心靈辯證法的一個展示過程”,重要的或許不止在于指出一個籠統的心靈辯證法或人性糾結,且還在于分析并論證是怎樣的心靈和人性,及又是怎樣的辨證和糾結。
當怕和愛的糾纏失控之后,作為人之根本性的“藥”的宗教救贖也就成為可能。從這一意義上說,《雷雨》隱喻的又何止是那一代人的“怕”與“愛”?也恰恰是從這一層面上我們說《雷雨》是一部世界級的文學經典。如果說《雷雨》之于其誕生的那個時代具有社會/政治學參照的歷史鏡像功能而被當作“社會問題劇”來讀的話,那么在遠離那個時代的今天,話劇所探討的個人生存倫理或許應成為我們研究的一個努力方向。
〔1〕曹禺.曹禺選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2〕弗洛伊德.圖騰與禁忌〔M〕.楊庸一譯.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
〔3〕陳思和.細讀《雷雨》——現代文學名作細讀之三〔J〕.南方文壇,2003(5).
〔4〕尼古拉·別爾嘉耶夫.人的奴役與自由〔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
〔5〕斯賓諾莎.倫理學〔M〕.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6〕漢斯·羅伯特·耀斯.審美經驗與文學解釋學〔M〕.顧建光,顧靜宇,張樂天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
〔7〕尼古拉·別爾嘉耶夫.論人的使命 神與人的生存辯證法〔M〕.張百春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8〕曹禺.曹禺論創作〔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
〔9〕S·薇依.在期待之中〔M〕.杜小真、顧嘉琛譯.北京:三聯書店.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