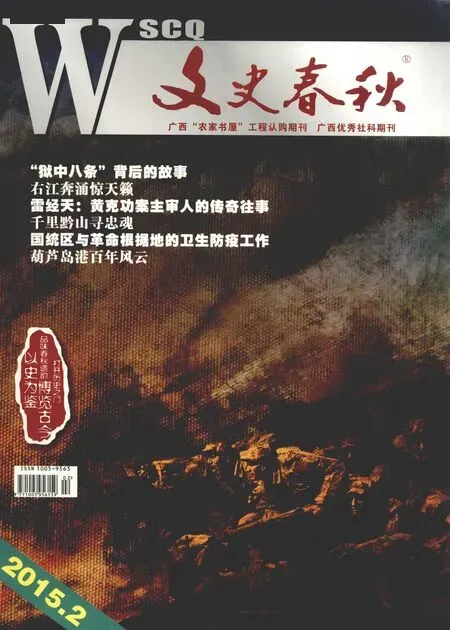從傳統(tǒng)民本到群眾路線
● 鐘 興
民,在中國古代指君臣百官及士大夫之外的庶民,后來泛指民眾、百姓、人民。 “民本”一詞,語出先秦典籍 《尚書·五子之歌》 “民惟邦本,本固邦安”,意為庶民是國家社稷的根本,統(tǒng)治者要敬民、重民、護(hù)民、愛民、親民,自我約束,慎重處理民事、國事。簡言之,民本就是以民為本。
商周時期,先哲以夏桀商紂為鑒,初步形成民本思想并推崇為治國安邦方略。動蕩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庶民的社會地位有了空前提高,孔子闡發(fā)君與民之舟水關(guān)系,孟子拋出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點(diǎn),荀子甚至說“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西漢,賈誼以秦亡為鑒力主安頓民生。唐初,魏征常以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之理勸諫太宗李世民,貞觀之治也因重民生而開創(chuàng)了大唐盛世。明末,黃宗羲痛感君主專制之腐朽和時下的民不聊生,提出 “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思想,稱: “蓋天下之治,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
傳統(tǒng)民本雖然重視和敬畏人民,并積淀了豐富多姿的治國安邦智慧,但卻有其歷史局限性——民本多被視為得民心、存社稷、固君位的手段,并不能上升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讓人民當(dāng)家作主的高度。
來自于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肩負(fù)著代表、實現(xiàn)、維護(hù)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根本利益的歷史責(zé)任的中國共產(chǎn)黨,在艱難曲折的革命斗爭和新中國建設(shè)中,傳承傳統(tǒng)民本文化精華,并在革命實踐中不斷升華為黨的群眾路線。
早在1922年,中共二大通過的 《組織章程決議案》指出: “黨的一切運(yùn)動都必須深入到廣大的群眾里面去。”1929年的古田會議決議提出,黨的工作要 “在黨的討論和決議之后,再經(jīng)過群眾路線去執(zhí)行”。1945年的中共七大,把 “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lián)系”作為黨的三大優(yōu)良作風(fēng)之一。改革開放以后,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 《關(guān)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群眾路線被確定為毛澤東思想三個 “活的靈魂”之一,其基本內(nèi)容概括為 “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群策之為則無不成,群力之舉則無不勝。本期的 《右江奔涌驚天籟》 《挺進(jìn)冀中話賀龍》,生動佐證了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是全民戰(zhàn)爭,只有動員和依靠人民群眾,才能贏得最終勝利。 《國統(tǒng)區(qū)與革命根據(jù)地的衛(wèi)生防疫工作》揭示,兩種區(qū)域的工作存在很大差異性,其深層原因正是是否堅持徹底以民為本或堅持群眾路線。 《.雷經(jīng)天:黃克功案主審人的傳奇往事》,一位幾經(jīng)冤屈而信念彌堅的革命家和黨的司法工作領(lǐng)導(dǎo)人,在革命生涯和司法工作中展現(xiàn)了深厚的民本情懷和親民作風(fēng)。
《千里黔山尋忠魂》,追憶布衣將軍盧燾愛國愛民、為民辦實事做好事直至獻(xiàn)身的光輝事跡。 《中國女學(xué)會的倡辦者李閏》,繼承丈夫譚嗣同之遺志,含辛茹苦,致力于女權(quán) (女學(xué))事業(yè),表現(xiàn)出深切的民本情懷。
《“獄中八條”背后的故事》道出一段慘痛歷史,其中飽含烈士們血淚囑托的 “獄中八條”竟與當(dāng)前的中央 “八項規(guī)定”和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精神不謀而合,這又是何等強(qiáng)烈的警示!
人民群眾是力量與智慧的偉大源泉。歷史如此,當(dāng)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