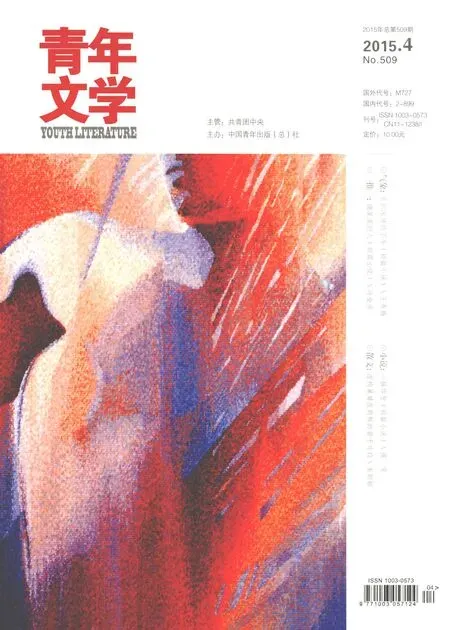草 生
⊙ 文/周 偉
草 生
⊙ 文/周 偉
周 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作品散見于《大家》《天涯》《散文》等刊。著有散文集《鄉間詞韻》《陽光下的味道》等多部。曾獲湖南省青年文學獎、冰心兒童圖書獎、孫犁文學獎等。
像一片枯黃的草葉飄落在大地上,無聲無息。
草生叔是在這個盛夏的午后,走在趕集回來的路上,搖搖晃晃,像一片草葉一樣墜地,仰面躺在馬路上。午后的陽光很亮,白晃晃的,灼熱無度。通往毛馬路的兩端都沒有行人出現,也無一點飛禽走獸出沒的跡象,只有幾只螞蟻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不辭辛勞地,在滾燙的大地上一點一點兒地緩緩爬行。午后兩點鐘左右,是最炎熱的時刻。沒有誰知道,草生叔是什么時候躺下去的。沒有誰知道,草生叔像一片草葉墜地時是什么感覺。沒有誰知道,躺在地上的草生叔在想些什么……
當我火急火燎地趕到老家的時候,草生叔已壽衣壽鞋壽帽穿戴停當,靜靜地躺在堂屋中央的門板上。草生叔嘴角還有微微地翕動,努力地呼出絲絲的氣息,盡管異常艱難和無助。我湊近他身邊,感覺到草生叔的生命還是那樣堅韌和鮮活。我說,草生叔命硬,不要緊,好好的一個人,無病無災的,不會一下就沒了。母親見我這樣說,就有點怪罪起幾個嫂嫂和嬸娘來,說還有喘氣的樣子,怎么壽衣穿得這么早?我轉過身來,看著穿戴一新的草生叔,很陌生。我也不知道,什么時候草生叔置辦起這套行囊的?他在生前好像什么也不在乎,走時卻要干干凈凈、體體面面地走。
夏夜的蚊蟲到處亂撞,一個個找不到黑暗的出口,沒頭沒腦,見人就咬。
我在還有一絲氣息的草生叔的頭兩側、腳兩邊和全身四周燒了幾圈蚊香,地上凹凸不平,難以擺放平穩。后虎嫂立馬給我拿了幾個用過的鋼絲球,正如她所說,蚊香放在上面果然很便捷,也不怕引燃其他物品。我蹲下來,看著草生叔,用打火機一一點燃每一處蚊香。每點燃一處,我總以為在幫草生叔又照見了一回光亮。
我記得,草生叔常常是在黑暗中去尋見他自己的光亮。他喜歡向很深很黑的夜中走去,一個人游蕩在漫無邊際的黑夜中。他總是睡得很晚,從不點燈,摸摸索索中,上床就睡。草生叔睡了的時候,整個村莊都睡了。也許,黑暗能消融他的孤獨和害怕。也許,黑暗中的世界,是他一個人的世界。
那么近距離接觸草生叔,我清楚地聽得見他喉腔里的絲絲氣息,真切地感受到了他身上的溫度和他身上的氣味。來看草生叔的人很多,四周都圍了人,都說草生叔人好,身體也好,又命硬,不會有事的。
草生叔一生無兒無女,無欲無求,無不良嗜好,沒有缺點,沒有愛好,也沒有脾氣,他不看電視,不打牌,不喝酒,不和婦女黏黏糊糊。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好抽個煙,高興時哼一兩句誰也聽不懂的戲文。他沒有仇人,他對生活也不怨不憎,不怒不爭,隨圓就方。我不知道,這一切,于草生叔來說,是好是壞,是對是錯?我只知道,草生叔一個人有他一個人的過法。這么多年,草生叔就是這樣過來的。
草生叔是個五保戶,他的父母就他一個兒子,他又沒生下一兒半女。
據說,草生叔也是讀過一點書的。他就那么隨便在院子里一站,抬頭看天,就說哪天要晴哪天下雨哪天飛雪,無一不準。鄉野村夫個個看天討吃,土里扒生活,栽東種西時大家都愛問草生叔。草生叔掐指一算,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臉上放光,眉角舒展,立馬說有了,哪家的牛走失在哪個方位,哪家的東西落在哪個角落,一一應驗。早年間,草生叔還去過很遠的地方修鐵路修水庫修機場,他也領過獎狀做過報告風光過一陣。但草生叔從來不說,從我們記事起,草生叔一輩子就窩在善塘院子里,一日兩餐粗茶淡飯。
大家都記得,沒有孩子的草生叔,卻最喜歡孩子,孩子也最喜歡他。他帶過我們這一班后字輩,也帶過我們下一班樂字輩,還帶過我們下下一班英字輩。我不知道,草生叔是用了什么花招,能讓我們幾輩人在童年時喜歡他,長大后也還記得他。我只記得,他沒有糖果,但他兜里常常有曬干的紅薯片子;他沒有玩具,卻能制作以假亂真的木手槍;他不會說大道理,卻能講好多奇奇怪怪的故事……奶奶還在時,時常替草生叔嘆氣,說:一個有孩子緣的人卻沒得一兒半女,真是不公呢!
草生叔早年也是娶過一房老婆的,老婆脖子上長個“葫蘆”(患甲狀腺腫),我們一幫孩子覺得稀罕,就取笑她,嫌她,用口水吐她,用土疙瘩摔她,用刻薄的言語奚落她。不久后,那個長個“葫蘆”的女人郁郁地走了。長大后,我總覺得,草生叔晚年一個人孤孤單單,我們是有一定責任的。
草生叔擺在老屋的堂屋里,靈堂也設在那里。
草生叔在凌晨五點鐘左右的時候還是走了。母親和幾個嬸娘見了我,就說你草生叔去了,去了也好。我走近草生叔,他真的走了,平平靜靜地走了。我久久地站在草生叔面前,一個人怔怔地出神,生出些許的感嘆:一個人的生命倒下去,就像一片草葉輕輕地落下,沒有半點重量,如草一樣,草生草長,草灰草白。
大家圍攏來,七嘴八舌地商量著草生叔的喪事。在農村,這是大事,絕對馬虎不得。父親提出一切從簡,火化了事,沒有一個人贊成他。其實,我知道,父親認為草生叔是五保戶,火化了,政府埋單,也不要花費人力物力和錢財。可大家都認為草生叔一生過得草草了事,最后一程還是要體體面面地走。不然,前不久草生叔也不會一個人去棺材鋪訂了一副“千年屋”(棺材)。后歸哥說,那老板還是善塘鋪里的親戚,“千年屋”的優惠價也得三千六百八十元。
后歸哥是我堂兄,是草生叔的堂侄,也是村里的村長,在家做著小生意,是村里少數幾個沒有外出打工的青壯年。村里的書記是風娥姐,這些年上得廳堂下得廚房,很不容易。他們兩個一合計,說八十歲的老人了,還是不能草率了事,也要像模像樣地辦一下。我說沒有意見,該咋辦就咋辦。父親有些干著急,我知道他急的是錢。
錢確實是個大問題。在農村辦個喪事,最簡單的,也要花個兩三萬。后歸哥盡管是村里的村長,但終究跟我一樣是晚一輩的,在村里做紅白喜事時說話擲地有聲的還是村里的長輩。我們村里的一應紅白喜事,都是德生叔坐鎮的。不用說,后歸哥請德生叔出來管賬,由他發話。德生叔一到,就說得先說錢的事,沒有錢,開不了臺。
后歸哥就一五一十地說,說草生叔的五保金還有三千八百元,估計剛好夠那副“千年屋”的價錢,還有一個低保卡存有兩千元,能燒一座像樣的紙屋吧。他說,草生叔在生前住不好睡不好,到那邊還是要有個大房子,還是要睡個好的“千年屋”。大家都說,當得,當得。后歸哥說,不搞火化,鎮里一分錢都報銷不了,草生叔沒有崽女,現在只能靠我們這些堂侄兒,大家一個出一點,湊攏來把大事辦了。后歸哥說完,第一個看著我,我迎著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點了下頭。后歸哥說,那就每人五百元,集攏來看看有多少?德生叔皺了皺眉頭,說:只怕是少了點。
說到關鍵處,大家伙全散了。不久,就聽說后湘哥不肯出,說是草生叔也沒幫他家做過什么,更沒幫忙帶過小孩。我就有些氣憤,怎都這么計較?不過,我還是看見后湘哥和后爭哥幾個去對門鳳形山里下大力氣幫草生叔挖金腳(墳坑)去了。
父親要我等等,不要太急,看大家拿多少錢,說都是一樣的親,你不要先冒頭。我說反正要拿的,早拿遲拿都要拿,還是先拿吧。母親說要拿,你也不能多拿,你一個人的工資,老婆又下崗,兒子又要讀大學了。我說,盡量還是多拿一點吧,怕是不夠花,怕是送不出草生叔呢。我不曉得,我去晚叔家解手的一會兒,母親竟替我交了錢,帶頭交的是一千元。
這時,傳來好消息,說后湘哥也肯交了,每人五百元,大家都肯交了。風娥姐還說,剛剛跟廣州打工的幾個通了電話,后彪哥答應出一千元,后升哥答應出兩千元。他們說不能回來送草生叔,要風娥姐告訴賬號,立馬打錢過來。
這時,我姐和我妹也從縣城趕了回來,她們送了花圈放了炮火,提了籠箱包了禮金。姐和妹還把我扯到一邊,說不能讓大家看扁我,說草生叔對我家也是有恩的,幫我家做過幾年農活……我知道姐和妹的意思,我沒有征求父母的意見,又去德生叔那兒交了兩千元。
父母后來知道,有點怪我的意思,但沒說什么。
草生叔在世時,常說:錢嘛,是魚口中的水,叭進叭出的。草生叔對錢不看重,一生也極少花錢。他說,你花錢,花水一樣,其實錢也在花你呢。當然,草生叔說這話的時候,沒有幾個人愿意聽,還有人取笑他,說吃不到葡萄還喊葡萄酸呢。
草生叔掙不到錢,也舍不得花錢。其實,他本來是可以掙錢的,他幫了這家幫那家,幫人犁田打耙,幫人擔土砌窯,幫人砍樹開山……按幫工工資開給他,日積月累,不是一個小數目。他卻一律不收錢,說鄉里鄉親的,都是一大家子的人,哪能出口閉口都是一個錢字?有很多時候,他都是不聲不響地把事做了,把忙幫了,把活兒干完,甚至連飯也不吃,就走了。后來,草生叔做不得重力氣活兒,就幫人操持家務事,幫人帶小孩、看屋,也都是攢起心勁的。也是怪了,草生叔看見小孩就親,小孩看見他也個個親得很。他一生舍不得花錢,比如不舍得花錢割肉,不舍得花錢買衣、吃藥,卻常常花一點小錢買一些指包糖,去逗小孩子。對自己唯一大方的,是每回趕集去買一包兩塊錢的紙煙熏。
我小時候就知道草生叔愛卷煙葉,把黃亮亮的煙葉切成細絲,然后撕下我們寫完的作業本滾煙筒。我們也學著滾,滾來滾去,總不成器,滾成了喇叭筒。草生叔就手把手教我們選煙葉,教我們切絲,教我們滾筒,教我們點火,我們總是學不好,在他吐出一圈圈的云里霧里睡著了。后來,草生叔自己眼神不好,手也不利索了,他就再也不能卷煙抽了,只能去買最廉價的盒煙。
這次,草生叔去趕集,也是去買盒煙的。他近來感覺到自己大不如前了,走起路來腿腳發顫,老高老大的身軀虛弱得像片草葉一樣,在這世界里晃蕩,在這黑洞洞的世界里找不到出口。他本來去得早早的,有很多人從他身邊一晃而過,都和他打著招呼,他知道,自己卻蔫蔫的不想出聲,有一兩次出聲,也是聲若游絲。
一路上,草生叔唯一握緊的是褲兜里那張五十元票子。今兒個,他不想割肉,只想買幾盒好的煙抽。他一腳輕一腳重地向前走去,從熱鬧的人群中飄過,沒有人注視他。也許他瘦小卑微得像一只螞蟻,爬行在別人看不見光亮的角落里。
草生叔想買了煙就早早地回去,然后,靜靜的一個人,抽著煙,瞧著天,想著事。然而,草生叔很失敗,那一直緊緊捏在褲兜里的那張五十元大票子不翼而飛。他一家家商店走過去,看柜臺上一包包精致的盒煙,走得很慢很慢,走到魚香子的時候,他看到一世界的黑,他看見白晃晃的黑,他看見深洞洞的黑,他在自己的世界里找不到一束光亮……
他像一片枯黃的草葉,飄落在自己的世界里。
出殯那天,本來安排得井井有條的。臨時,還是出了問題。總的來說,是人的問題,人手太少。村子里的青壯年大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都是“老弱殘兵”。
放炮火安排了兩個人,一個是七十一歲的中寶叔,一個是六十二歲的玉彩叔。臨時,玉彩叔說要帶自己的孫子去看病。后歸哥趕緊用小車裝了炮火事先沿路去擺放好,好在到鳳形山不遠,又一路是進村的水泥路面。中寶叔一路一瘸一拐走在前頭,點一個手中的大炮,再點一個路邊的禮炮,大炮山崩地響,禮炮一路禮花,中寶叔無憂無慮像個小孩一樣。
出殯時,抬柩是最重要的。抬柩是力氣活,個個要能下大力的,放在肩上要紋絲不動,要莊嚴肅穆,要講究穩和慢。在鄉村,抬柩一般分三班,每班八個人,前面八個,后面八個,有一班八個是用來換肩的。這次給草生叔抬柩,安排了一組、二組、七組各四個人,三、四、五、六組各兩個人。到場的,一看年紀大多是六七十歲的人,五十多歲的只有四個人,尤其是二組只來了兩個人。后歸哥大為惱火,罵了人,罵了很出格的話,說他們二組以后不也要死人嗎?罵是罵,在關鍵時刻,后歸哥和德生叔兩個人只得頂了上去。
草生叔的侄兒輩除后龍哥、后湘哥、后歸哥都在抬柩的隊伍之列,只有我一人必須要去拜路,我得領著后歸哥的兒子,還有后歸嫂、后龍嫂,后龍嫂還抱著她的小孫子,三步一跪、五步一拜,一路去拜。拜路,是表示對死者的孝敬和請求山神、土地、路神和一切陰靈開道和讓路,所以我們也很是認真和守規矩。四十多歲的我,腰椎間盤突出,一起一跪,一弓一升之間,感覺有些吃力。沿路經過哪家屋前,人家放鞭炮,我要眼尖腳快,趕去“下禮”。我下禮后,風娥姐就要給人家發毛巾。沿路炮響,沿路下禮,沿路一一發放毛巾。
草生叔的下葬地是鳳形山腳,是我們的一處祖墳,坐北朝南,視野寬闊,前面有出路,背后有靠山,兩邊有“扶手”,周圍樹木繁茂,水源流長。
一番祭井、下柩臺。我和后歸嫂、嘉儀,還有抱著孫子的后龍嫂,一一跪在墳前,等待道師拋出羅盤米。羅盤米俗稱衣食米,是死者給子孫的最后一次賞賜,預示今后子孫有吃有穿,衣食不愁。扯著衣服,拋下來的羅盤米,一粒一粒,雪白雪白的,從高空落下。我捧著,感到生命的重量。拈了幾粒米,往嘴里一放,輕輕地一抿,一絲微薄的清甜與米香,立刻讓我感覺到童年中那些鮮為人知隱秘的歡樂,有那么幾秒鐘,在我的眼里慢慢地涌起一股微熱。
站在山腰,回望送葬離去的隊伍,老的老,少的少,七零八落,潰不成軍。近千口人的村子,只有不到五六十人的送行隊伍。十六年前,奶奶走時,那送行隊伍的壯觀,和現在比起來,讓人感到心情甚是落寞。我知道,現在的鄉村,已不是原來的鄉村了,人去樓空,物是人非。我不知道,草生叔在這里,會感到冷清和寂寞嗎?
出殯回來,吃了飯,大家四散離去。
村子里一下子又恢復了往日的模樣,好像什么事都沒發生過。
做法的道師還在,他們還要為草生叔敲打一番,祈禱一番。那座富麗堂皇的紙屋已早早地抬到曬谷坪里,屋里放了籠箱、錢柜,也存放了很多的紙錢,四周齊齊地都堆放起干柴。我和后龍嫂、后歸嫂加上我母親四個人各自手執柳枝分站在四個方向,等大火燒起時,就圍著紙屋轉圈跑,一邊口中呼喊,一邊手執柳枝驅趕其他小鬼,免得草生叔在那邊收不到房屋和錢財,寄人籬下,生活沒有著落。
正準備引火時,后歸哥的兒子崽嘉儀從他家的烤煙房里跑出來,瘦小的他背著一大包黃亮亮的卷煙,他一點兒不心疼地把一大包卷煙投進熊熊燃燒的大火中。后歸嫂看到,一點不怪她的兒子,她說,嘉儀曉得草生爺爺臨死也沒買到煙,他要讓他在那邊抽個飽。
道師在燒紙屋時先是口中念念有詞,手舞足蹈,然后殺雞放血敬神。玉田叔明明是抓了兩只雞來的,有一只雞不知什么時候飛跑了,四處遍尋不著,真是怪呢。有人就說,是不是雞自己跳到紙屋里去了,那就讓草生叔吃了烤雞算了。正說著,雞從紙屋中一下跳了出來,有人說草生叔肯定是生了氣了。
當秋蔸子打掃草生叔的臥室時,竟發現白白的兩床棉絮沒有用過,還有一把明晃晃的柴刀也是閃著光。母親對秋蔸子說不用燒可以拿回家用,秋蔸子卻堅持要燒,燒給草生叔。秋蔸子只拿了那把柴刀回家,他說現在這樣的柴刀很少了,盡管現在也不用上山砍樹剁柴,但是每年清明掃墳是派得上大用場的。
秋蔸子說,草生是一輩子從不上山掃墓的,也用不著這把好刀。這倒是真的,大家都記得清明時節草生叔從不和大家一起上山掛青,就連他爹娘墳前他也從不去點個香燭燒幾沓紙錢壘一抔黃土。為這事,玉明大伯都罵過草生叔。草生叔也沒回嘴,也沒說緣由。
喪事辦完了,德生叔跟大家通報說攏共湊到了兩萬一千八百元,除去一切開支,還剩下兩千四百元。接下來,幾個玉字輩的叔叔一合計,說草生叔的爹娘幾十年了都沒有立個碑,加上草生叔自己,就立三塊小一點的毛碑吧,錢基本湊合。
大家都說好。大家都說喪事辦得也很完滿呢。
辦完喪事的時候,想起我們一大家子的長輩只有四叔、父親、九叔和晚叔等四個老人了,很是落寞和傷感。父親這一輩在族譜上都是玉字輩,大伯玉明喊明生,二伯玉堂喊堂生,三伯玉石喊石生,四伯玉悟喊悟生,五伯玉草喊草生,父親玉甲喊大生,七叔玉節喊節生,八叔玉寶喊寶生,九叔玉容喊容生,晚叔玉丁喊丁生,等等。我不知道,為什么都要喊作生,也許是懂得生之艱辛的緣故吧。
天地間,有生有死,有枯有榮,死既必然,生何以為?草生草滅,花開花落,風停雨住,云開日出,一切都將還歸平靜的生活。
有人說,草生叔走了不一會兒,里面院子后發佬家就生了一個帶把的孫,一大家子人歡天喜地得不行。一個人走了,一個人又來了。走的走,來的來,這世界就是這樣——晝夜交替,寒暑更迭,自然更新,陰陽日缺。正是如此,鄉村有鄉村的秩序,土地有土地的深情。
草生叔走了,正如草生叔沒來過一樣,一切依舊。鄉村還在,鄉里鄉親還在,我很多的記憶和美好都還在那里,我的根還在那里。每年清明,我都會如期回去,村子里的鄉里鄉親有個紅白喜事的,我也是盡量地抽時間趕回去。我知道,去鄉和歸鄉,是我一輩子永遠修不完的功課。
難怪,古人也說:“如何三萬六千日,不放身心靜片時?”泉水在山乃清,明月就在當空。其實,想想,一切都是那么簡單——
人活一世,草生一春。人有生老病死,草有榮枯盛衰。草生一世,火燒不盡,風吹又生。草生草長,人起人落。從容相愛,如葉生樹梢;從容生活,如草生堤堰。草長節,人活骨。寸草生,寸心知。泥暖草生,土深春綠。人有死,草還生……
一切,皆是常理;一切,皆有定數。
草生叔的死,讓我恍然大悟。
有道是:未知死,焉知生?
放眼天地間:小草卑微,可以鋪出盎然綠色;花兒無名,也能開出絕地風景;當然,草民平凡盡可展現浩蕩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