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胡適
(文/林建剛,來源:經濟觀察網)
Point
一般一個人死了,應該就可以蓋棺論定了。然而,胡適卻是個例外。從反傳統到對傳統的溫情與敬意,從開創學術風氣到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從胡適的小腳太太到他的情人,關于他的議論至今也還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1962年,胡適心臟病猝發逝世。五十年后,任劍濤、許章潤、高全喜等一群1962年出生的學者,以紀念胡適的名義聚在一起,重新審視與反思胡適,于是也就有了這一本《重思胡適》的學術著作。幽默一點說,任劍濤、許章潤、高全喜等先生可謂是胡適的“轉世靈童”了。
一般一個人死了,應該就可以蓋棺論定了。然而,胡適卻是個例外。從反傳統到對傳統的溫情與敬意,從開創學術風氣到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從胡適的小腳太太到他的情人,關于他的議論至今也還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很難得的是,在對胡適的價值論斷上,這些1962年出生的大陸學者,達成了一些共識,這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學界對胡適的研究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學者高全喜從蔣介石給胡適題寫的挽聯入手,向我們展示了胡適調和新舊,不偏不倚的文化姿態。在他看來,這正是古典現代性在胡適身上的恰切體現。胡適溫和的態度與清明的理性,很容易讓人想起古語所說的“極高明而道中庸”。這與以前學界多批判胡適保守的論斷截然不同。
與高全喜類似,許章潤在談到胡適與蔣介石的關系時寫道:“就以胡、蔣關系而言,君臣之間,即離兩端,德位二極,可謂做到極致了。在那樣的嚴酷條件下,他們都努力做到極致了,可算是老中國人的一脈路子。”
這也是一個極高的評價了。以往的學界,要么譴責胡適在蔣介石面前缺乏獨立性,做了蔣介石的幫閑;要么以胡適來證明蔣介石不聽勸誡,一意孤行的獨裁。其實呢,在大是大非問題上,胡適從來都保持他的獨立性,在需要對歷史做交代的重要關口上,他從來沒有含糊過。而蔣介石呢,雖然在日記中對胡適惡語相向,但是在公眾場合,基本都保持了對胡適的禮遇,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他“容納異己”的風度。
同樣的,任劍濤從胡適的家國認同出發,對胡適1949年的人生抉擇表達了理解之同情。以往的學術界,對胡適1949年離開大陸,普遍有不滿,很多人甚至以此來論定胡適不愛國。畢竟當時有“毛澤東讓胡適做北平圖書館館長”的說法,他們對胡適的離開,表示惋惜。
對此,任劍濤有不同看法,他詳細比較了國共兩黨的行事作風,對胡適為何選擇離開大陸作了精彩的學理論述。應該說,胡適在1949年的人生抉擇,體現了胡適對政治形勢的精準判斷,也體現了胡適的人生智慧。
這些對胡適認同的背后,其實也是學術界多年以來反思激進主義的一個表征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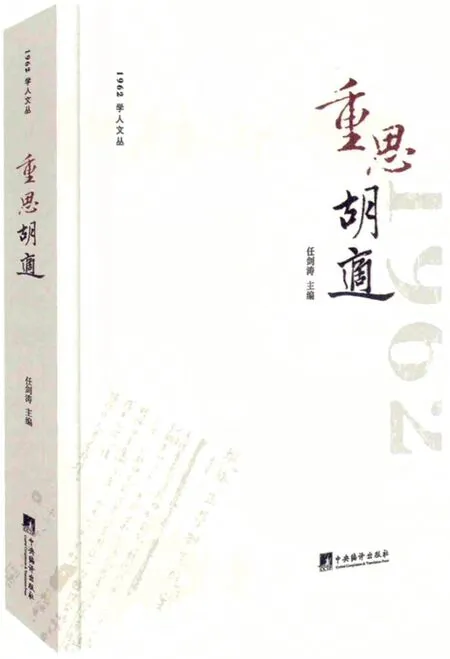
希臘史家普魯塔克有句名言曰:“對偉大思想領袖的無情,是強大民族的特征。”這些1962年的學者,在高度評價胡適的同時,也反思了他的一些迷失。
比如,在對土地公有制與計劃經濟的看法上。學者陳志武指出,胡適一方面主張自由主義,但另外一方面卻主張土地公有制與計劃經濟。對于胡適為什么會不重視私有產權制度,陳志武也給出了自己的解釋,那就是胡適留學美國時期的成績單。胡適留美時,許多科目都是優等,唯有經濟學方面,僅僅是勉強及格而已。或許正是在留學時期經濟學理論方面的薄弱,才導致胡適思想的迷失吧。
陳志武認為,胡適的這一迷失,直到1953年3月5日在關于哈耶克《到奴役之路》的演講中才真正認清這一問題。而在我看來,其實胡適在1930年代就已經意識到了這一問題。1934年,胡適在《獨立評論》上發表《建設與無為》。文中寫道:“我不反對有為,但我反對盲目的有為;我贊成建設,但我反對害民的建設。盲目的建設不如無為的休息。”
此時的胡適主張無為,其實已經意味著他對計劃經濟的否定。
到了1945年,胡適明確否定了計劃經濟。1945年2月3日,在給資源委員會成員王征的信中,胡適寫道:
關于我們曾討論的一個問題,我近來也偶然想想,我還是感覺今日國內的朋友們太注重大規模的建設計劃了。套一句老話:“為政不在多計劃,在力行如何耳。”這一句兩千年的老話,在今日仍有一部分的真實性。大亂之后,應該多注重與民休息。政治的綱紀不可不立,經濟的骨干不可不有,交通的綱領不可不完成。然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一句話源出于主張自然無為的老子。后人多注重“不漏”二字,而忘了“恢恢”二字和“疏”的一字。疏是不細密,恢恢是大而寬。“恢恢而疏”,老百姓才能充分發展其自身的能力,從各方面謀生存,謀樹立,謀發展。我曾聽我家鄉老輩說他們的祖上在太平天國亂后的恢復情形,故深信老百姓有此恢復能力。所慮者“天網”或太密耳。
這里,胡適反對的對象就是以翁文灝、錢昌照、王征等人為代表的資源委員會。這些資源委員會的委員,出于對計劃經濟的迷戀,在抗戰時期組建了一系列大規模的國有企業,并且以抗日救國的名義,大規模鯨吞民營經濟,形成了一股“國進民退”的潮流。抗戰勝利后的官僚資本主義,其實就是資源委員會實行“國進民退”策略的后果而已。
對于資源委員會的這些舉措,胡適明確表達了自己的反對意見,也意味著他對計劃經濟的徹底拋棄。到了國共內戰時期,當國民政府的經濟出現嚴重通貨膨脹時,胡適向蔣介石推薦了蔣碩杰、劉大中等經濟學家來幫助國民政府。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蔣碩杰恰恰就是哈耶克的學生。倘使此時的胡適還迷戀計劃經濟,他又怎么會推薦哈耶克的學生呢?
對于私有產權,胡適在1948年也有了新的體認。1948年,在《當前中國文化問題》一文中,胡適寫道:
我走過許多國家,我沒有見到一個國家犧牲經濟自由可以得到政治自由,也沒有見到一個國家犧牲政治自由可以得到經濟自由。俄國人民生活程度三十年來提高了多少?人民生活痛苦減輕了多少?經濟自由得到了沒有?犧牲政治自由而得到經濟自由的,歷史上未有先例。
在這里,胡適重點強調了經濟自由,而嚴格的私有產權制度恰恰是經濟自由的基礎。此外,這里胡適批判的對象,就是蘇俄。鑒于蘇俄不尊重私有財產的歷史,胡適開始重新認識到“私有財產”在捍衛人的自由方面的重要性。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胡適對私有產權與市場經濟的確認,并不是在1950年代,而是在1940年代,甚至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胡適的思想迷失,似乎是在1920年代后期的那幾年。
陳志武之外,單世聯在《信念與錯覺——評說胡適在民主與獨裁論戰中的一些觀點》中也對以胡適為首的一些知識分子進行了理論反思。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么這些一流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像蔣廷黻、丁文江等人,到了1930年代,竟然都開始公然提倡“新式獨裁”?結合當時的時代潮流,單世聯認為:當時意大利的法西斯、德國的納粹、蘇聯的五年計劃的超額完成,都對知識分子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力,而當時的中國,正面臨著日本的侵略危機。于是,在迅速富強與個人自由之間,這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面臨著非此即彼的抉擇。這也正是胡傳勝所提出的那個疑問:是不是富強與復興是至高價值,而另外的價值,不管是自由,民主,科學等等,都是次一級的價值呢?最終,蔣廷黻、丁文江選擇了富強,為了迅速富強,他們不惜飲鴆止渴,公然提倡新式獨裁,而胡適則選擇了個人自由和民主。
對單世聯的這一解釋,我非常認同。不過,我還想補充一個大背景,那就是蔣廷黻的黨籍問題。很多人認為,1930年代的蔣廷黻,還是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其實不然。此時的蔣廷黻,很可能已經是國民黨復興社的社員了。
晚年的胡適有一個“大膽假設”。他認為蔣廷黻是國民黨黨員。對此,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寫道:
我記得我們那時還談了些有關蔣廷黻的掌故。我偶爾提到蔣氏可能是“復興社”里的要員。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胡先生說當他1952年返臺蔣公約見之時,他們曾涉及胡蔣二位有意組黨之事。“蔣先生說,‘請告訴廷黻不要另外組黨了,還是回到國民黨里來吧!’”
“這‘回到’二字里有文章!”胡先生不疑處有疑地向我說,“蔣廷黻未加入過國民黨,為什么要‘回到’國民黨里去呢?”
胡先生懷疑蔣廷黻先生是個力能通天的“藍衣社”大員。我們并且把《獨立評論》找出來“考據”一下蔣廷黻加入“復興社”的可能年代。(唐德剛《胡適雜憶》,第31—32頁)
胡適的這個“大膽假設”,在張忠紱的回憶錄中得到了印證。張忠紱回憶說:
至于蔣廷黻后來(大陸撤出后)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自謂不是黨員,那卻是騙人的。他不僅止是黨員,而且是黨內許多小組織中的成員。(《迷惘集》,張忠黻著,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6月,第144頁)
張忠紱披露“蔣廷黻是黨內許多小組織的成員”,這里的小組織,極有可能就是胡適所說的藍衣社。
我為什么不憚其煩地論述“蔣廷黻是國民黨黨員”這一事實呢?因為蔣廷黻的國民黨黨員身份可以讓我們重新審視1930年代“民主與獨裁”的論戰。
如果我們聯系到當時蔣廷黻已經是國民黨黨員,甚至是藍衣社社員這一身份,我們或許就不會對蔣廷黻主張“新式獨裁”感到吃驚。作為一個事功心非常強烈的人,蔣廷黻很明白當時的蔣介石喜歡什么。于是,他就堂而皇之地在《獨立評論》上公開宣布這一主張。要知道,蔣廷黻是《獨立評論》知識分子群中最早棄學從政的人。這一論爭之后,蔣廷黻很快就作為蔣介石的密使,出使蘇俄,再后來,蔣廷黻還成為了駐蘇大使。
如果聯系到蔣廷黻是國民黨黨員的身份背景,對1930年代的“民主與獨裁”的論戰,我們或許就會看得更加清楚了吧!
——《篳路藍縷:計劃經濟在中國》評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