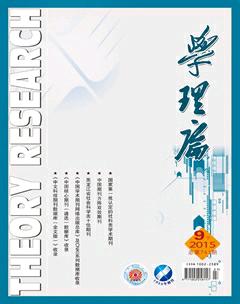曹禺戲劇中的兩代關系
黨增御
摘 要:中國的戲劇在曹禺這里發展并成熟,曹禺在廣泛吸收西方戲劇思想以及傳統思想下,深刻揭示了中國社會的兩代人的矛盾,主要從父子關系、母子關系以及養父女關系來探究,結合當時的社會狀況,體現他們之間內在的矛盾以及沖突。
關鍵詞:兩代人;沖突;父子關系;母子關系;養父女關系
中圖分類號:I206 ? 文獻標志碼:A ?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27-0070-02
20世紀30年代是一個充滿動蕩的年代,在這劇蕩的變化之中,中國的現代化逐漸發展。中國戲劇的現代化在短短的時間之內發展并成熟,在這之中,曹禺的貢獻尤為重要。
一、曹禺創作來源
(一)西方文化影響
曹禺的戲劇廣泛包含著西方希臘戲劇文化的影響,尤其是后來美國戲劇大師奧尼爾的影響,奧尼爾的戲劇是“確定一種易卜生式的現實主義,來代替支配美國的劇壇傳統。”[1]由此,曹禺一改五四時期易卜生的追隨者“承襲著只是一些ibsen主義或ibsen口號,并且勉強把這些主義或者口號裝到他們所做的未成熟的劇作里面去。”[2]從而形成自己獨特的寫作方法,從而影響著中國戲劇的發展。以前的研究者大多從曹禺戲劇中的悲劇性來著眼研究,著重表現著曹禺戲劇的時代特征,而較少去解讀其中所包含的兩代關系。
(二)幼年經歷對他的影響
只有對曹禺的生平有所了解才可能全面把握住曹禺創作的動機以及意義,曹禺的生長環境對他后來的戲劇創作影響很深,“他(父親)對我哥哥很兇很兇,好發脾氣。我總怕同他一塊兒吃飯,他常常在吃飯的時候訓斥子弟。從早到晚,父親和繼母在一起抽鴉片煙。”[3]童年的記憶影響了曹禺一生的創作,在他的劇本創作之中,處處表現著的是父輩的暴虐以及子輩的無力,正如他童年的記憶。與此同時,曹禺從母親(繼母)的懷抱里就成為戲劇的觀眾,在這潛移默化的影響之中,他廣泛汲取著中國傳統戲劇的精神,并在他日后的戲劇創作中體現出來。繼母始終將他看作是自己的親生骨肉,并終身未生育,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母親普遍擁有著對于子女無盡的愛,但這種愛往往多到無法承受。應該注意的是,他的劇作中出現的母親形象往往擁有著歇斯底里的特性,然而在這行為之中所蘊含著的生命的魅力卻也不容忽視。
二、曹禺作品中的三類關系
(一)父子關系
在古今中外的許多文學作品中,父子關系主要表現的是其中的矛盾與沖突,“父”作為秩序和固守的象征,而“子”則代表著變化與發展。“子”實現了對“父”的延續,但又表現著對“父”的背離與超越,因此文學作品中便出現了不變的“父子沖突”。曹禺劇作中,男性呈現著兩個極端的特性;一種是“懦弱型”的男性形象,包括周萍、曾文清、焦大星等,他們屬于時代的多余人,他們的生命缺少男性生命的壯美,整日在自己的思想世界之中而無力反抗,他們缺乏精神上的獨立以及敢于超越自身局限的信心以及力量。另一種則是“權威型”男性形象,包括周樸園、曾皓、焦閻王等,表現著傳統文化下所熏陶的男子,他們自私,冷漠,專制,無情。由曹禺所設置的兩類男性形象,我們可以發現作為對立面的父與子,他們有著截然不同的性格,具體表現為子輩無力反抗長輩。所以在文本之中的沖突也沒有真正形成一種對等的關系,個性軟弱殘缺的兒子們缺少了與父親沖突的勇氣與能力。這是“對于現實的一個極好的暴露,對于沒落者的極好的譏嘲。”[4]
1.兒子的仇父戀母。《雷雨》作為一部反映家庭的戲劇,父子關系是其中著力表現的主題之一,其中以周樸園與周萍的關系最為突出。周萍與其后母的亂倫之戀,被看作是一種典型的“仇父戀母”情結,他甚至對母親兼情人的蘩漪說:他恨他的父親、愿他死,就是犯了滅倫的罪也干這樣的話,周萍這時的仇父情緒相當濃烈。可以說,周萍的這一亂倫行為是對于父子關系的一種挑戰與蔑視,使得父子沖突從開始便進入了一種對等的緊張階段。但是這種緊張的沖突剛開始便結束了。“當新方式逐漸顯露,舊方式還仍然存在著,面對著尚未消亡的舊生命方式的持久力和內聚力,新方式的突進最終必定要失敗,過渡地帶是個悲劇時代。”[5]一方面,傳統倫理道德的強大壓力使得周萍感覺到深重的負罪感;另一方面,周萍的軟弱性格使他在面對父親的淫威那一刻就喪失了對抗的勇氣。所以,我們會發現周萍的言行前后判若兩人,曾發出“就是犯了滅倫的罪也干”的敢于挑戰世俗倫理的青年,不久之后就無奈地表白“我是我父親的兒子”,并后悔于以前自己的荒謬,認為那不過是因為年輕而說出的糊涂話而已,一場本來可以很有張力的“父子沖突”就這樣萎縮了。
2.父子關系的崩潰。《北京人》中曾家大兒子曾文清聰穎清俊,善良溫厚,性格卻軟弱無能,雖然已是中年卻依舊沒有生活經濟來源,是一個”廢人”,只會作詩作畫抽鴉片。曾家家主曾浩代表著封建勢力和封建思想統治,在他仁義道德的面孔下是一顆自私虛偽的心,一輩子最大的滿足就是擁有漆了幾十年的棺材,自私自利又目光短淺。他希望兒子不要抽鴉片,甚至在半夜里跪下來懇求曾文清,希望他振作,在這場景之中,崩潰的不僅是曾文清這個多余人,而且父親本身的心靈支柱也崩潰了。最終曾文清在絕望中吞食鴉片死亡,但其實他的靈魂早已經隨著他的懦弱無力而逐漸消亡了。其中的父子關系所蘊含的悲劇性使得我們震撼,震驚于其中子輩的萎靡不振以及父輩精神的塌陷。“悲劇比別的任何文學形式更能夠表現人物在生命最重要關頭的最動人的生活,它也比別的任何文藝形式更能使我們感動,它喚起我們最大量的生命能量,并使之得到充分地宣泄。”[6]
3.強勢的父親。《原野》中處在仇家與焦家之間以及妻子與母親之間的焦大星,生存于情感的“夾縫”里,直不起腰來。焦大星為留下妻子,竟然忍受妻子紅杏出墻。焦大星為了“生存”而“緩和”矛盾,屈辱地迎合他人,表現出極端的“懦弱”,但社會不需要這種懦弱的人,所以焦大星最終成了“替死鬼”。焦大星作為典型的“懦弱型”男子形象,從小生活在封建家長專制下的家庭環境里,長期受封建倫理道德思想束縛,最終導致他本身缺少陽剛雄健的男性氣質,既無雄心又無能力,表現出的是失意、落魄、屈服,缺乏精神上獨立人格。作品中直接表現焦閻王的地方不多,然而我們可以從文中焦閻王設法將仇虎送進監獄這一片段推斷出他是一個十分有手段且心狠手辣的人,并且手腕強硬,完全不同于其子焦大星。
(二)母子關系
曹禺筆下的女性洋溢著生命激情、張揚著自我欲望,即使處于人生的低谷之中,仍然充滿著奮斗不屈的生命的力感,“人作為對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種受動的存在物;而由于這種存在物感受到自己的苦惱,所以他是有情欲的存在物,情欲是人強烈追求自己本質力量的存在物。”[7]她們勇敢地抗爭,努力追尋著自我,表達著對自己生命的渴望。在這追求過程本身,她們表現了深沉的母愛,同時又表現著對子女無盡的關心。但是由于時代以及命運的捉弄,使得她們的愛表現得有些深沉,在這之中體現著人生的一種悲壯感,同時充滿著常人所無法想象的沖突,正如曹禺在其作品中所說的,“她的生命交織著最殘酷的愛和最不忍的恨,她擁有著行為上許多的矛盾,但沒有一個矛盾不是極端的。”[8]在這矛盾之中,她們最終走向了幻滅,這其中的代表如繁漪,焦母。
1.繁漪的雷雨性格。《雷雨》中的蘩漪是曹禺所有的劇作中最雷雨的性格,她美麗的心靈被環境窒息變成了乖戾。但是她的痛苦最深,渴望又最強,所以爆發得最疾,最猛,就像雷雨。“我算不清我親眼看見多少繁漪,她們都在陰溝里討著生活,卻心偏天樣的高;熱情原是一片燒不熄的火,而上帝偏偏罰她們枯干的生長在沙上。而這類女人有著美麗的心靈,然為著不正常的發展,和環境的窒息,她們變為乖戾,成為人所不能了解的。”[8]她犀利得像一把刀,刻畫了一道道傷痕。但是同時她在理智的情況下又充滿著對周沖的愛。她理解周沖支持著他接受各種新事物,明白他有著沖破這污濁世界的執念。周沖的靈魂純凈得沒有一絲雜質,擁有著常人所無法逾越的純真。她仿佛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從前的自己,那種久違了的生機。但是,這個社會不能兼容這樣的存在,因此她們一起在失落中丟失了自己。在結尾中繁漪瘋掉,周沖意外死亡,但是他們直到最后,都沒有失去自己堅守的思想。也許他們的結局不很偉大,但是他們卻詮釋了人世間最美好的母子之情。
2.壓抑下的焦母與夾縫中的焦大星。曹禺的劇作總是“深入人類精神生活領域,描寫人性的追求與毀滅,心靈的壓抑與燃燒,從思想情感、精神生活角度解釋生活的內在底蘊。”[9]《原野》中焦母是這之中的一個代表人物,在她言語的尖酸刻薄中,其實深藏一顆破碎的心,她丈夫早逝,在傳統思想下一直孤單守寡,因此她將所有壓抑的情感都給了她兒子,以至于最終發展成了“戀子情結”。焦大星生長在封建家長專制下的家庭環境里,長期受封建倫理道德思想束縛。在成人之后,焦母用思想無時無刻地包裹著他,強勢的母親總是要求他按照她的思想而行動,雖然她的初衷通常是為了兒子,但是最終卻極大加劇了焦大星身上畏懼、失意、落魄、萎靡不振的氣質。她們奇特的行為正像張愛玲《金鎖記》中的曹七巧與她的兒子,表現的是懦弱的子輩男性與強勢的母輩女性之間壓抑并努力擺脫的情感。作為一個女性,她們都有著命運控制之下無法逃脫的宿命,她們越是逃脫,越是深陷之中,最終使得自己走向了毀滅;作為一個母親,她們表達著對于子輩的關心,然而過多的愛最終毀掉的不僅是子輩,而且還有她們本身。
(三)養父女關系
在曹禺的劇作中,老一輩往往是代表著壓制的力量,是年輕人進步的羈絆,然而年輕人在最初的屈服之后,往往選擇反抗,努力逃脫,尋求自己的光明之路。正如曹禺自己所表達的,“有炙熱的熱情,一顆強悍的心,敢沖破一切的桎梏,作一次困獸的斗。”[10]
消逝的北京人。《北京人》中曾浩體現著封建的腐朽、沒落,他整天關心的就是自己的棺材。愫芳出身名門卻父母早亡,受封建士大夫文化熏陶,她有著寧愿犧牲自己,但愿能使別人快樂的情操,寄居在曾家的她成了曾家的養女。在劇中充分表現他們關系的是為愫方說媒這部分,這場戲深刻而細致地表現了曾皓要把愫方抓住不放的心思,他口口聲聲說不要想到他,要愫方想想自己,表現出那樣的寬厚、慈愛,但是在骨子里卻是要愫方陪著他一同進棺材,他的每句話,對愫方都是精神上的折磨、損傷,以圖使她永遠打消嫁人的愿望,從而屈服于他,做他的奴隸。曾皓一再說他活不多久了,暗示她不要考慮這門親事,還說“不肯嫁的女兒,我不是也一樣養嗎?”明明是他耽誤了愫方的婚事,但是卻把愫方說成是“不肯嫁的女兒”,一句“我沒有意思啊!”將她的心態表現得淋漓盡致。在最后,她跟瑞貞一起出走,向過去告別,面向未來,表現了埋葬舊生活,走向新生活的主題。
三、曹禺話劇的影響
兩代關系在古今中外都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如古希臘《俄狄浦斯王》中揭示了命運的悲劇性,而人在面對這種悲劇時的無力反抗以及命運的殘酷性,從而給人以心靈的凈化,“歐洲理性教給曹禺的是對于滲透著古陶和黃土子孫血液的民族自覺,曹禺每次迷入歐洲,對中國的理解就更能進一層。”[11]而中國古代的《趙氏孤兒》中更是充滿著脫離了個人利害得失的價值判斷,從而作為人們立身行事的一種道德取向,最終形成對于正義的理解。曹禺融匯中西,兼收并蓄,將戲劇中的兩代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向前推進了一步,豐富了中外戲劇舞臺,使兩代關系更加全面細致地展開。
參考文獻:
[1]馬庫斯坎利夫.美國的文學[M].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5:289.
[2]向培良.中國戲劇概評[M].上海:泰東書局,1928.
[3]田本相.曹禺訪談錄[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
[4]曹禺.曹禺論創作[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
[5]雅克貝爾斯.悲劇的超越[M].亦春,譯.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6]朱光潛.悲劇心理學[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34.
[7]馬克思.1884年經濟學政治學手稿[M].劉丕坤,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2.
[8]曹禺.雷雨序[M].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
[9]朱棟霖.論曹禺的戲劇創作[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27.
[10]曹禺.我對戲劇創作的希望[J].劇作,1981,6(4).
[11]田本相.海外學者論曹禺[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