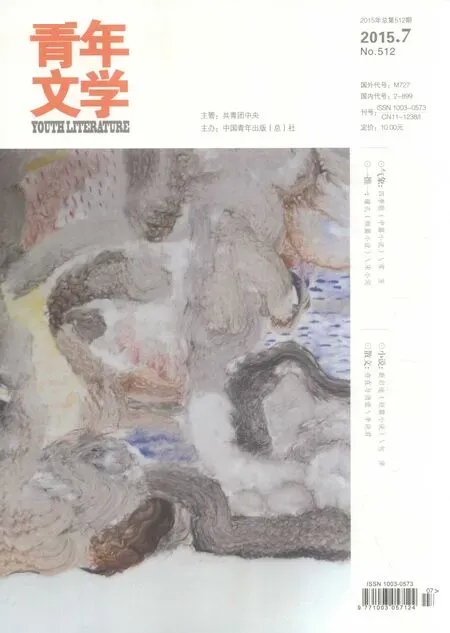山海關
⊙ 文 / 蕭蕭樹
山海關
⊙ 文 / 蕭蕭樹
蕭蕭樹:原名肖霄。一九八七年植樹節生于河北保定,二〇一〇年畢業于河北科技大學。熱愛漢語,熱愛文學。
一
關隘、黎明、詩人——此三者構成世界完美性的死亡。
亂國之大城,也是那孤苦的心鎖,此刻,介于有形與無形之間,其本身便是一種象征。人們雕琢城市,故而人類得以呈現遠高大于建筑本身物態的假象。此城城高十米有四,鐵鑄般的墻壁,橫臥于遠古的流亡之地,其廣度為四平方公里,巍峨地臨著太平洋。如若尚有什么能長久寄存童年的情緒和氣氛,那當是城,然其形式以不可名狀的、細致入微的極端方式蔓延著,如今已經深深潛伏于文明的髓里,形成了迷人的病。
所以,城的惹人憐憫又憐憫于人,是同一種情懷的遲鈍反應,它源自于后知后覺的愚昧,源自于一個終極的矛盾。
觀城,進而獲知這城的凝滯與流動,這早已形成了不同的理解方式。用語言翻譯一座城,實是最為無奈之舉。詩人所想便是,那個“超越”的文明,抑或應脫穎于此城?然而那文明已是殘篇,有幾篇文字今生也將無法完成,甚至即使尚有完美之可能,但依舊是無補。并且果真誰竟能將其或然性進行證實,其艱難與此刻的“抉擇”也應是等同的。
詩人在黎明三四點之間的獨行,偶然想到這種可能,即證實生命之死亡與證實城的存在性,其本質是統一的,那便是靈魂的一生一世。
而所謂靈魂又從何而來?大抵是人類基因中那第一次亙古長存的目光吧,那應是三只母猿望向尚未得以命名的宇宙時的淚滴吧,這目光與淚滴在宇宙中成形,被新的形勢和能量塑造成魂靈這種物質,然后一次次注入有機物質的組合之中,于是在思索、苦澀中生活,不熄不滅地燃燒,于是道德、思想與界限出現了,那便如同這大城的路途與關卡。康德曾說,在這世界將有兩種東西帶來永恒震撼,一是心中美的準則,一是頭頂燦爛星空。
而現在,隔著最為黑夜的城角,再次仰望這遠山上的星空,那是何等的偉大與廣闊。于是,詩人伸出手臂,高高擎起這觸摸的激情,卻發現它遠非遙不可及,遠非虛無縹緲。
詩人想到,這感覺的一次誕生與毀滅便是死亡了,佛說死在一呼一吸之間,大概也沒有這瞬間的覺醒更為短暫。而可悲的是,這死時至此刻,便形似一種處心積慮的陰謀,否則,如何又得以與這人間的城相遇呢?也許吧,這終將成為一種傳奇,一種對他人不可訴說、不可傳承之物。而人如何可知,人之死亡本身,從不曾包含這諸多的情感與思辨,人之死亡……
人之死亡漸入詩之冷峻,進而映射著時間與空間的奧妙。中國的城因此也是不同的,它在地域上是一個斷裂,一個可怕的隆起的疤痕。如米勒曾說,界限便是用來穿越的,那么就來此城吧。離城便是經久的陰冷的風,而山是巨壘的頑石,海亦是完美的整體。而早在文字起始之時,早在先秦與春秋時期,建設這座城的初衷,便是將那無數野蠻的離散了靈魂的人圍困,多而漫長,于是此城無始無終,但城外便是盡頭,文明的盡頭。這便是人的瘋癲,人的執著。于是此刻,這山與海便不能再爭辯什么。
每座城市相連著,每座城的氣質在這個國度傳染著,城外與另一座無名之城相連的便是一段火車的慢行道,步行而至,近在咫尺。此時是三月,北國的春完全沒有從蟄伏中解脫,陰冷的城外的戾氣構成的風,依舊在錘擊著高筑的墻。隔年未死的長草葉子,反射夜色的靈光,進而便可以撫平一種精神的患難。
詩人的精神是異常的,這一事件結束后,醫生們尚能夠分析清晰這一點。可見,詩人的精神真的是異常的。詩亦不能不與此相關。
詩人唯有寂寞地行走,此時毫無疲憊之感。
詩人深深地用力,力量便集中在了雙目之上,那是瞳孔,擴張,擴張,歸于死亡的最后一次注視,如同一顆死星,有人稱之為“末日之瞳”。這雙眼睛的留影,在日后,所多的是被描述為孤獨與絕望,偶也有人理解為悲哀與憂愁,但是卻與愛情無關。這一切人的情懷是如此的相關,卻無人能夠真正找到其中的關聯,即便在詩人已成這時代的神話之時,也是如此。
然而此刻,詩人的這雙眼真實的卻僅僅是暗淡,是屈服。黑夜過于黑暗,過于讓人無可適從。詩人努力前行,被石子打磨著腳掌,路,尤其難以辨識,在這種背景中,詩人如何尋找到了那最適于自戕的地段呢?可他已無力尋找,也無須尋找,那里已經死去了三個人,三個“普通”人,詩人卻不知曉。
詩人目光黯淡,卑微地注視,無神地注視。然而,此刻已然不是詩人在注視,而是另一個肉體,早已消亡的肉體。是的,數年之前,剛剛成年的詩人早已宣告了一個事實,他已經將某個自己殺死了,一個分裂的“自我”,他早已設想了某次自殺,那或者來自于另一個宇宙,另一個故事。但死亡已成事實,只是更加漫長。死亡的事實讓人屈服,造就這種屈服的是無數次失敗的死亡,未能完成的死亡。
這種死亡不是沒有出現過:梵高自殺之時是失敗的,他沒有立即死去,上帝讓他屈辱而卑賤地加倍體驗死的苦楚,兩天后不治身已;普希金中彈后也沒有立即死去,而是在步入死的折磨中更深刻地體驗這個世界的不公,煎熬了兩三天。因此,詩人之死的漫長尤為壯烈和可怕。
故而詩人重新造就一次分裂,來體驗這完美的死。人們猜測,人類會在死之前夕重新經歷一生,確切地說,是在死的瞬間。而詩人則應該經歷麥地、月亮和雨水和家園(畢竟詩人永遠是一個客死之人,有無數的城市,無數的家鄉,這些城市在這種時刻一定會去紀念,這也許會形成許多的死,死的幻影,死的分裂),也應該想到一些人,詩人的親人與戀人。
然而無論如何都不能通過死亡分裂出的這些東西對詩人做最后的拯救,一個失敗者拒絕拯救,詩人走過春天黎明,在高傲天宇最初的光明之中,詩人分裂,那時距離黎明一小時五十六分,一次完美的死亡便展現在世界之上,一次完美的死亡便是對死亡的雄壯碾碎,讓死亡成為一個孤立于時空之外的更大的存在。
然而詩人選擇的死亡與普通的精神病患者是相同的,這并非因為詩人失去了作為詩人的尊嚴,而是長久地被命運的漠視,堆積成一次寶貴成功。阿基米德死于野蠻人的劍,野蠻人有怎樣的精神境界可以憑借,來完成這種壯舉般的殺戮?故而野蠻是不存在的,此劍便應屬于上帝,而死亡實實在在展示給世界的,僅僅是一塊生硬的鐵。
面對這樣的生鐵,詩人沒有任何思想,此刻的空虛和平靜,便是充斥著宇宙的所有物質。除去“我”的意識之外,僅有這種絕對的靜。詩人吃掉了一瓣橘子,然后注視了自己的死去。
詩人注視自己躺在曦光之中等待,而他自己則在一旁平靜地消化著橘子的肉體,在一個胃部,空虛和饑餓的胃部,燃起了火,想將這最后的果實融化。
然而,死亡來得如此之急切,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的凌晨三四點鐘,一列火車正在通過地球東方的山海關與龍家營之間的一段慢行車道,詩人曾幻想過它烈焰滾滾的金輪,此刻它輕松地碾過了詩人,任何人都沒有發現。
詩人坐在車道一邊,看到這如真實的場景,或者說終于驗證這早成事實的場景,笑了,這座城。
二
然而城依舊是存在著,死亡如若有一種常態的話,那便也是“存在”。死亡的常態伴隨人自始至終,故而“存在”才有著一個絕對的背景,一個最為親切的參照物。甚至抑或死亡與存在本就并非參照關系,而是一種實體的兩種表象而已。
于是,一直在解釋著存在的薩特,最終的死亡與其晚年漫長的軀體痛苦的存在形成了一種強烈對照,以至于我們并不能了解其生存之痛苦源自死亡還是存在,而如果將存在定義為生存,便也顯得不甚妥當。與之相同的有在北非沙漠中斷掉了雙腿的阿爾圖爾·蘭波、因麻風病而雙目失明的保羅·高更、全身癱瘓的南美女畫家弗里達·卡蘿,他們的死亡延續了很多年,而在這種存在中,他們用語言和色彩(而不是線條)描述死亡。也許死亡有迷人的色彩卻沒有實在的線條。
然而人們不關注于其存在,所多的是關注于其死亡,于是,死亡便分裂成無數形象,繼而成為許多人的死,我們的死,虛假的死,死的存在便岌岌可危。
詩人是新的一個,他心滿意足地目擊了自己的死亡,而存在依然繼續。此時,這種存在是無疆界的,是一種更加透徹與廣泛的感官。詩人看著自己的身軀已經被碾成了兩截,橫臥在冷冰冰的生鐵上,臥在大城山海關與大海太平洋的風中,列車早已遠去,金輪的光輝成為漆黑無色的血跡,列車帶著這種勝利,駛過了離城的那片黑夜。此時距黎明尚有一個小時零五十六分鐘。
詩人觀心,心已熄滅,詩人感觸到余熱緩緩升騰,于整個空間來說它如此渺小。余熱吸引著夜鳥,幸而尚不存在可怕的無眼的丑蟲,雖然對于詩人現在的心念與存在,早已無分美丑了。詩人看著碾碎的肉體不感到恐懼,但卻有些惆悵,必定這副身體對于此刻更高的真實來說,便是虛假的,甚至從未存在,那么是否這更高的靈魂的存在,是一個欺騙者,而詩人亦不為這冷酷的心思而自責,因為這種存在已是沒有愛憎的了。于是,這存在依舊安坐在車道旁,看著自己恰巧被一分為二的胃部,竟至發覺它在緩緩地蠕動。
那便是兩瓣橘子。
哦,那么說,這就是死亡了,它與生的未盡的果實相連著,總有著千絲萬縷。然而,它因不可言說、不可再現而遠別于愛情、靈感、肉欲、夢境的體驗。而此刻,這種體驗卻呈現在了并非詩人的肢體上,而是呈現在了一個與死亡相聯系的橘子上,橘子的身軀承載著死亡的極端渴望,這渴望悲苦而高傲,如驚鴻之一瞥,故而進入了另一維度里的形態,故而與一個易逝的宇宙形成了最貼近的默契、連接。這種連接,此刻便是饑餓。
于是,夜色之中,新的存在感到了一種饑餓,詩人相信,這饑餓便是因眼而生的。于是詩人試圖閉上眼睛,但那決然是不可以的了,因為這存在的眼界又在何處?詩人已發現他的眼界是無限的,他知曉一切,以至于宇宙在這種觀看中無非是混亂的彩色,無非是一個布景簡潔的戲劇,簡潔卻又是復雜。無數其實相同的人類在這里被投入生命的情節中,思想也無非是一些程序,沒有什么高深的秘密,宇宙不過是一張張畫好的圖片而已。
詩人在這場景之中走到了人類盡頭,試圖停止觀看,可這樣的力氣卻無法實現最為簡單的動作,詩人無法像來時尋找那陌生之路一般,將氣力與心力都凝匯于他的瞳孔了,那曾經的瞳孔早已被末日光景所填滿。
詩人感到饑餓,在死亡之后,依舊是饑餓。
這種饑餓持續著,終于使詩人思想起一種對死的挑戰,他試圖拯救這可悲的身軀了。黎明將至,詩人將嘗試一場復活,他自始至終地堅信著這種力量。
三
死亡于醫學是種模糊不清的定義,城于地理學亦然。我們時刻與死亡相連,正如城的居住者時刻來往出入于它。此城因它的悠久、因那些紛繁混亂的往昔,而形成現在甚至未來的形狀,吸引異鄉的人、居住的人、路過的人,這之中便有獨自誕生的文明在生長。然而說它是囚禁者之城,說它是整個這片古國大陸的心鎖,說它是一個關閉了文明之希望的門,都僅是人類的語言。
一個世紀前,軍閥們在這里混戰,一個將領,帶著他的士兵們出了關,準備投靠異國,書寫新歷史,最終卻盲目般地被自己的部下殺害,殞身關外;一個世紀前,曾有個新國家在此建立,而傀儡政權的當權者被蒙蔽,如同盲人,使得人民承受無邊苦難,那更是城的恥辱;幾十年前,國家開始了對教授專家和知識分子的革命,人民被一種癡愚所感染,這里更成為流亡之地,許多人長久被封鎖在此,直到客死他鄉。
城的這種氣氛長久聚集,甚至來自先秦遠古的被驅逐的異族游牧者之靈魂力也更加凝重,如同寒冰深入凍土,而那些試圖給予城以新意義的人,而今安在?必定建造這城市大鎖的人們也已不再。
春天詩人的存在臨于這樣的城,便是另一個意義,這意義由詩與死亡同時構成,它進而形成了新的語言、新的抽象事物和具體事物。這種意義也將降臨于許多個人身上,語言成為新的技能,并不是為了贏得懷念,而僅為生命之巨大。
生命之巨大,即是這黎明中突然爆發的。人的悲哀之一在于永遠無法證得自身的得證,而死亡的現象,使詩人觀宇宙業已虛假,更何談微不足道的東西。人無法擺脫這種幻想——人的存在并非只是命運的作弊,但現在詩人已得證。
這個黎明,對這幻想的挑戰便在詩人這種特殊的存在中開始了,死亡后的十個新的本體復活了,涌現于橫跨亞歐大陸、縱連極地至廣闊熱帶;從王朝到王朝,從冰期到冰期,從太陽到佛的星塵世界的腦體中。十個詩人的化身熙熙攘攘,來回奔跑,直到現在還沒有平靜下來。
而這座城,與此同時便也包容從兩河流域到太平洋西岸,從西伯利亞蒙古高原到印度次大陸的各種幻影,也包容著從啟示錄到荷馬史詩,從屈原到荷爾德林,再到奧義書再到梵高的時光幻影。于是此關口被億萬即已毀滅的城的形態所附形,分解為元素的便是不可計數的碼放整齊的紅磚綠瓦,進而是思索的手掌,孤獨擎起于中國古國度的一隅。
負隅頑抗者們出現,這些流放于此地的罪人,背負罪孽的重重業報,或祈求百千萬劫之后的超生,或歡騰于此十城地獄。
詩人在這種特殊的狀態中戰斗著,距離黎明僅有一小時五十六分鐘,但是他卻不需要任何時間。詩人終將勝利,這夜色中,他已完成一個雄壯的紅色背景的大詩,這夜色中,他已完成了遺囑,這死亡將與任何人無關。
于是此刻,我流浪在從南向北的道路上,來看山海關,看到這座城,被戰斗的幻象毀滅的殘缺城角重新出現。在太平洋一端,人們看到殘缺的文字形成了真正的城的命運,人們站立于城墻的絕壁,看到瞭望中的殘垣,鷹們正從那里飛過,尋找奔跑的橘子,那是一種蔓延著的失敗,而這曾經卻是詩人的勝利。或者因為某種力量的作用過于不平衡,所以詩人早已放棄那種重建。
清晨路過山海關,看到那不遠的山岡上一座孤獨的墳,青青的麥地,沒有人悼念。我在青麥地,讀起一首詩,詩人安坐著,依舊二十五歲,靜坐之中,悲哀而歡喜,又似忍受了饑餓。大地上散落一地的是:一本《圣經》,一本梭羅的《互爾登湖》,一本海牙達爾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得小說選》。放逐似的作品中,沒有詩人的戰斗,他只是神情安然,等待。
我沒有與他說話,只是隔著時空的墻壁凝視,但我知道詩人看不到我。我知道,這封鎖心靈的大城依然如故,故而詩人從來都盲目。
我看到他也許痛苦地等待著一列出城的火車,仿佛時光之中被記憶的部分永恒地停息于黎明前的黑暗。詩人走過麥地孤身一人,卻從未轉身,于是我知道本文關于復活的構想也完全是虛假的。
我看了很久,然后獨自走在回家的路上,青青麥地如古河奔流不息,豐收的日子還有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