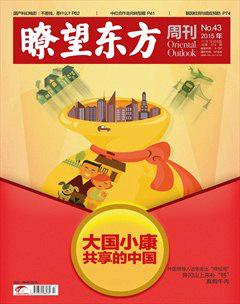俞峰:用外來形式講好中國故事
陳莉莉

歌劇《圖蘭朵》劇照(費斌/ 攝)
北京市朝陽門外大街,“中央歌劇院第七屆國際歌劇季”的巨型演出廣告異常醒目。
在中央歌劇院原創歌劇《我的母親叫太行》的排練現場,俞峰的指揮棒有韻律地揮舞著。它似乎有著強大的魔力,所有的節奏都從這里釋放出去又被收攏回來。除了藝術總監、首席指揮,余峰自2009年2月起還擔任了中央歌劇院院長,這令他的指揮棒在劇目之外還須兼顧更多職責。
當這部歌劇在2015年10月中旬亮相時,觀眾還沉浸在9月底中央歌劇院版瓦格納歌劇《眾神的黃昏》激發的興奮之中。
2015年,中央歌劇院生產了3部原創歌劇,并將《圖蘭朵》帶進普契尼的家鄉,完成了自2013年開始的瓦格納歌劇的“指環系列”。
“這些讓中央歌劇院有理由認為自己在高原上有了高峰。”俞峰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對中央歌劇院版的瓦格納歌劇,英國《金融時報》評論說:“作為中國歷史最為悠久的歌劇院,他們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引進與原創并行
《瞭望東方周刊》:歌劇是外來形式,這些年它在中國的發展情況如何?
俞峰:歌劇從意大利起源,有400多年的發展史,是最綜合的藝術載體,承載著民族的歷史、文化與情感。
在中國,中央歌劇院成立于1952年的延安。那時候,歌劇這種國際性的藝術形式之所以能夠出現在中國,跟當時比較開放的文化氛圍分不開,這是根源。在“文革”期間,歌劇也停了下來。這些年來,一直停停走走,最近幾年才開始快速發展。
相比世界水準,中國歌劇才剛剛起步。這些年來,在創作形式上,我們采取“引進國際作品”和“原創”并行。
我們希望能善用歌劇這種外來形式來講述中國故事。中國的第一部歌劇《白毛女》及后來的《洪湖赤衛隊》,都是影響很廣泛的講述中國故事的作品。
《瞭望東方周刊》:在表達中國故事的層面上,應該如何嘗試?
俞峰:2008年以來,中央歌劇院堅持每年一部原創作品,2015年一年就生產了3部,這樣加起來一共有10部。
我們的原創作品可以說是“十年磨一劍”。歌劇作品需要反映時代、又要傳播正能量,尤其是現代題材,又不能像古代題材那樣可以虛構,而且最終它要進入市場去贏得觀眾的認可。所以創作難度非常大。

《眾神的黃昏》劇照(費斌/攝)
比如說,留守兒童等題材適合藝術表現,但是怎么傳遞正能量很難把握。再比如莫言的《蛙》,從藝術的角度,我認為它是一部好作品,但該如何通過歌劇來表達也不容易。所以現在我們很多原創作品主要關注的題材是讓人感動的平凡人平凡事,就像《北川蘭輝》。
我們既要在藝術上探索,還要傳達正能量;既要有藝術成就,還要有社會和經濟效益。還有一個現實問題是,中國文學很多只寫故事,不寫心理。而戲劇往往需要通過心理來表現。
《瞭望東方周刊》:在原創題材上,有沒有特別想表達的內容?
俞峰:我特別想通過歌劇把倉央嘉措的故事表達出來,它涉及人性的糾結,又涉及佛性。這部劇我早已在腦子里想好了每一幕怎么來表達,那些畫面在我腦海中經常出現,并不斷完善。但與宗教有關的人物和故事要出現在大眾視野,需要走很多流程。
創作是發動機。要做文化大國、藝術大國,必須有作品,作品是永恒的。在創作經典作品的道路上,我們還要摸索。
有自己的工廠,還要有專賣店
《瞭望東方周刊》:這些年中央歌劇院的演出場次和票房收入怎么樣?
俞峰:2014年中央歌劇院是所有院團中票房收入最高的。
但我一直堅持認為演出場次不重要,不要在這里迷失了方向。一年到頭不停地演,那是什么?是大篷車。我們應該做國家隊應該做的事情,那就是沉淀出好作品,要有引領性。
中央歌劇院最早提出票務改革,因為不管是政府還是我們都希望老百姓進入市場。我們根據各個國家的平均收入,對比他們的票價,然后再研究美國大都會劇場的票價,制定出自己的票價標準,歌劇最高300元,交響樂200元。近兩年我們一直在推票價瘦身策略。此外,5年來,我們每年還有公益免費日,推出一兩場免費的演出吸引更多人關注。
《瞭望東方周刊》:怎么去平衡成本與收益兩者之間的矛盾?
俞峰:《眾神的黃昏》可能30年才能收回成本。我們對多數劇目的策略是慢慢收。
等我們有了自己的劇場以后成本會更低。2018年我們的新劇場將正式落成,現在地基已經打好了。以前中央歌劇院的狀態就像是一個著名品牌,只有自己的工廠而沒有專賣店。劇場建成后,我們希望更好地培養觀眾看歌劇的習慣和氛圍。
《瞭望東方周刊》:你對于中國歌劇的發展現狀怎么看?
俞峰:中國歌劇的發展,用外媒的說法是“后發展,有后勁”。西方劇院建設都是以歌劇院的標準來建的。我們的硬件已經大批興建起來了,現在是商場開了,但是沒貨。對于很多劇場來說,最重要的是要建好人才隊伍。
中國歌劇發展目前極缺指揮人才,因為沒有更多的練習機會。我當年就是在歌劇院當學徒的,連續好幾年跟著鄭小瑛老師。現在這樣的機會很少。中央歌劇院在給未來的指揮人才提供練習的機會,就得現場拿著指揮棒真正去做,就像踢足球和軍事演習一樣。
演出瓦格納歌劇相當于“神九”上天
《瞭望東方周刊》:從2013年開始,中央歌劇院就在演瓦格納的“指環系列”。了解世界歌劇史的人都知道瓦格納作品的難度,做這件事的意義是什么?
俞峰:瓦格納的作品,尤其是“指環系列”代表著歌劇的最高水準。他改變了整個歐洲的歌劇,從他開始,音樂才可以講述故事。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曾說到過“瓦格納”,這讓我特別高興。
2013年是瓦格納誕辰200周年,我們演出了他的《尼伯龍根的指環》系列,時間長達5個半小時。這是歌劇領域中演出時間最長、演繹難度和演唱難度最大的超大規模作品。演出這個劇目,是中央歌劇院國際性地位的一個標志。
2013年以來,中央歌劇院版的瓦格納作品演出場場爆滿。
我們介紹瓦格納的作品并在中國上演,就像人民文學出版社翻譯世界名著一樣。重要的是,我們借這樣高難度的作品打造自己的團隊。
中央歌劇院要成為亞洲第一大歌劇院,必須有這些標志性作品,這代表著國家藝術形象。
國際上很關注這件事情,2013年我們首演指環系列第一部《女武神》時,《紐約時報》評價說這相當于中國的“神九”上天。
這些已經完成首演的瓦格納作品是中央歌劇院的鎮院之寶,將來還會一直演下去。
中國版《圖蘭朵》感動了普契尼的孫女
《瞭望東方周刊》:這些年中央歌劇院不僅把經典引進國內,也去國外演出經典作品,比如2015年8月底在普契尼家鄉演出《圖蘭朵》,這是借助了什么樣的契機?
俞峰:普契尼藝術節是世界上幾大藝術節之一,中央歌劇院是受邀的首個外國團體。
2012年正值中央歌劇院60年院慶,我們收到了羅馬藝術基金會的邀請。他們觀看過我們的《圖蘭朵》,非常震驚,邀請我們到羅馬演出。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但是,我們的演出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連續幾天場場爆滿。
整個歐洲由此都知道了中國的歌劇演出水準。所以后來我們就收到了普契尼藝術節的邀請。
歌劇《圖蘭朵》是中央歌劇院于1989年引入國內的,1995年中央歌劇院第一次完整演出。20年里,《圖蘭朵》對中國歌劇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89年我還是學生時,就跟著中央歌劇院排演《圖蘭朵》。當時打出的口號是“砸鍋賣鐵也要把《圖蘭朵》給立起來”。
這是歌劇大師寫的中國題材的故事,我們相當于免費請了一個外國作曲大師來幫助我們傳播中國故事。我們要學習人家怎么寫中國題材,怎么運用中國的二十七八個民歌,通過西洋的思維方式和作曲技法做出來。
《瞭望東方周刊》:把《圖蘭朵》帶到原創者的家鄉,觀眾中還有他的后裔,會不會有點冒險?
俞峰:中國歌劇正在以很快的速度成長,只是很多人不太了解。這次我們在普契尼家鄉演出的《圖蘭朵》,他的孫女看完后非常激動,說這是她近30年看過的最好的《圖蘭朵》,這給我們很大鼓舞。
國際上的劇評家和普契尼研究者以及劇迷,也認為我們中國人演《圖蘭朵》絕對不亞于意大利人。這相當于外國的劇團到中國北京來演京劇,并被國內戲迷和評論界高度評價一樣。
《瞭望東方周刊》:這次演出還帶來了什么樣的效應?
俞峰:演出結束后,意方主動對我們說,歡迎你們中國自己的劇目。但我認為,對于剛剛起步的中國歌劇來說,在國際舞臺演出國際經典作品,是一條走向世界的必經之路。在國際大舞臺上,首先要有實力講話,這樣才可以帶動本國文化傳播,讓外國人愿意了解中國故事。
我并不完全認同“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就像承辦奧運會一樣,先要在國際主流項目上讓世界看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