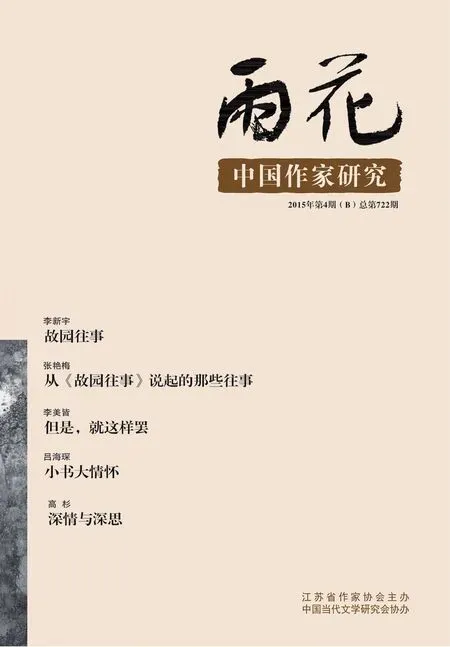學者的詩性情懷
■ 本刊編輯部
學者的詩性情懷
■ 本刊編輯部
當下時代的知識分子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專以潛心治學,皓首窮經,經年端坐案頭的純粹學院派學者;另外一種就是以多種筆墨書寫人生的憂患型學者,他們在嚴謹的學術研究之余,常常以文學作品來展示其詩性的一面,展現其對社會的擔當。這種類似于公共知識分子的學者,近幾年來涌現出不少,他們在治學的同時,都寫下了不少見出真性情的詩性文字。從這些迥異于嚴謹學術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窺探其作為學者的詩性的一面,此可謂學者的詩性情懷。
其實,在現代中國,學者的詩性書寫是一個傳統,好的學者往往都是好的作家或者文學家。魯迅、胡適、陳獨秀那一代五四學者就不用說了,他們之所以能夠稱為大家,就是因為不僅學問做得好,其道德文章更是令人欽佩。可惜的是,這樣的一個好的傳統,在建國之后就有所中斷了,許多人一頭扎進了書齋里面,樂此不疲地做起了“學術考古”者,或有意或無意地丟棄了學人的另一副筆墨——見出真性情的詩性文章。好在,這個傳統在近年來又得到了接續。
本期,我們刊發了著名學者李新宇教授的長篇散文《故園往事》。此前,李新宇先生曾經出版過同名散文集。這次,他又專門為本刊撰寫了一些新的篇章,仍舊以《故園往事》為題。從中,我們可以充分領略到李新宇作為學者的詩性情懷。
在這些文字當中,有對歷史的追問,更有對家園的眷戀;有對風俗的展示,更有對血親的懷念;有對成長的記憶,更有精神的尋根。李新宇教授在關照自我來路的同時,道破了時代的鄉村精神密碼。這些文字雖為文學作品,卻仍舊和李新宇教授的學術文字有相通之處——他的所有文字幾乎都有著高度的“自覺”。
集詩性的學者和學者的詩性于一身的李新宇教授,在學問、思想和散文諸多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績,他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憂國憂民的詩性學者。如果說,“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是魯迅先生的精神寫照,如今,它也是如李新宇教授這樣的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寫照。李新宇先生孤獨而又堅強地行進在魯迅先生曾經走過的道路上。從這個角度來說,魯迅先生不孤單。而在李新宇先生身旁身后,正有許許多多的同道和后來者緊跟著,所以,他也不會孤單。
2015年4月8日,于江蘇師范大學作家工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