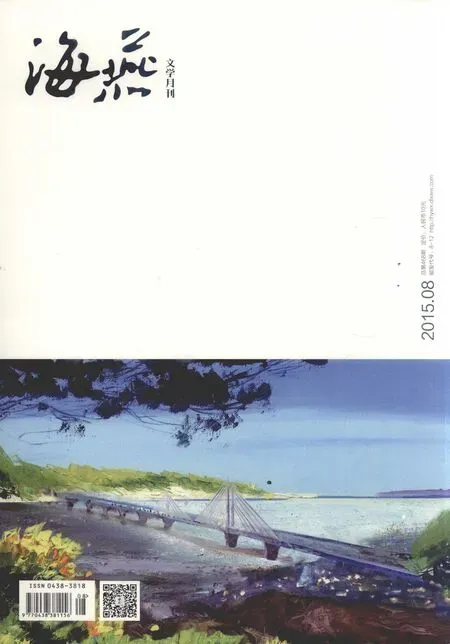真情寫作:記憶照亮詩歌
——曹宇翔與郭曉曄詩歌述評
□李犁
真情寫作:記憶照亮詩歌
——曹宇翔與郭曉曄詩歌述評
□李犁
曹宇翔是一個有溫度的詩人,他的詩歌像秋天臨近中午的陽光,溫暖而不灼烈,而且不僅熱還有光芒,照耀得讀者的內心也一片明亮且暖融融。有人說好詩人要同時具備靈氣、頭腦和心腸。前兩個讓詩人寫出好詩,加上好心腸詩人就能寫出大詩。心腸就是情懷,在曹宇翔的詩里就是仁愛,就是菩提心。他的詩里有慈悲,知足、感恩、珍惜的同時,他在用愛去拔出和熨平一切眾生的苦難,給予他們安樂和幸福。所以他的詩歌離我們離心靈很近,親近親切,像一個大哥一個兒子與自己的兄弟母親嘮嗑。他的詩歌就是凈白而暖和的棉花,他舉著它為親人、受難者還有故鄉和祖國擦去額角的汗水和血痕。所以他的詩歌中就不是簡單的隔岸觀火似的同情和憐憫,而是視別人的痛苦為自己身上的疾患,那些寫給村莊和大地的詞語就是自己心靈里剜下來血肉,真誠真切有切膚之感。這讓他寫祖國這樣抽象的詩,也少了那些大詞,而是從具象和細節出發,讓人感到祖國就是“祖母干草垛,一個孩子搖響鈴鐺”,就是他的豐收在望的東勝村,就是健壯的兄長,黑黑的大嫂,還有麥茬和壟間跳出的一簇野花。祖國變得就在我們眼前,呼出的熱氣在我們面頰上繚繞。
需要指出的是,曹宇翔不論是直接寫家鄉,還是當下生活題材里的喻體,使用的都是鄉村的物與事。這說明童年的記憶已經成為一個人一生的胎記,它是血脈,流淌在詩人的作品里。鄉村的品格就是他詩歌的品格,更是他寫作的胚胎,一切由此發軔,一切都濡染了鄉村的色彩。所以讀他的詩歌你會情不自禁地發出:“真真啊!”的感嘆。這是鄉村的真誠和樸實讓他一絲不掛地赤裸著自己的情感,這就是古人說的“直尋”,就是不花里胡哨,不忽忽悠悠,語言與情感零距離。情真而語直,情感激烈的時刻,誰會故意繞來繞去呢?何況還是與親人說話。所以讀他的詩歌總有要流淚的感覺,即便是詩人面對豐收時金黃田野的欣喜之情,也讓人的眼圈有點溫熱。這是從漫長的苦難和艱辛中熬過來的農人,屬于他們的幸福是那么渺小而且來得又那么艱難,還一直脆弱著。而艱苦歲月中的母親即使承受再多的苦與累,也要把全部的愛給予幼小的兒子。這些感動天地的溫暖瞬間,就是巨大的鄉愁,一直梗在游子的情感里,像針埋在皮膚里,詩人捅破了它,就等于捅破了情感的淚腺。
當然我們不可能返回農業時光中去了,但是對鄉愁的緬懷和回首,就是對自己身份的確認,就是讓人和文學不要偏離真實和人性,這是一個永恒的主題,是整個文學的方向。找到了它,詩歌就找到了回家的路。所以曹宇翔在回家的路上喜悅、感動、敬畏,并把心靈清洗得一塵不染,這純凈的情感讓他的詩歌變得清澈而澄明,像剛剛出山的泉水,透明而清新,這是有氧的詩歌,冒著鮮漿的詩歌,讓人的心脾都充滿了綠色和清亮。在當下污濁混亂又自私冷漠的詩壇,曹宇翔詩歌的樸素簡單,還有清澈得透出亮來,尤其是真誠和溫暖就顯得彌足珍貴。
與曹宇翔的鄉村童年記憶相比,郭曉曄寫的是青春和城市的記憶。青春期與城市生活讓郭曉曄的記憶像繽紛的燈球,閃爍的色彩讓人產生一種迷離和迷惘,那是記憶的碎片錯位了人的感覺,還有拼合了記憶卻無法回到記憶里去帶來的情感落差。這就是郭曉曄說的“懷舊是傷”。傷,一是無法返回記憶的失落和遺憾,這是懷念之傷,時間之傷。二是年輕時的幼稚與懵懂使記憶中的事物沒能完美,這是青春之傷,成長之傷。記憶在這里是一個喻體,首先記憶代表著美、愛和永不再來的圣物。懷念它就是用過去照耀現在,用記憶縫補現實之傷。另一方面記憶是傾訴的對象,也是要傾訴的內容。讓詩人像面對上帝一樣面對記憶說出對記憶本身的體會,這其中交織著懷念痛惜和懺悔。這后一種回憶就成了寫作的技藝和方式。但是郭曉曄不是通過回憶讓往日再現,而是以現在的經驗立場和情境,對記憶和當時的經歷進行梳理和審視。事是過去的,感受是現在的。所以他不敘述記憶中的具體事件,充盈在詩中的記憶都是一些碎片,我們只能從他詩歌的標題上知道他寫的是哪件事。譬如:《我曾有過清澈的生活》《那時的風箏我放到現在》《父親曾是我的屋頂》等等。標題說了個事物,這是他的抒情點,是他詩歌要去的方向,然后站在現在的角度在詩中表達對那時那件事的感覺。這種對過去的再認識和緬懷讓他的詩歌充滿了疼痛和激蕩,這是情感被點燃后自動地彎曲與伸展。所以雖然記憶是零散的片段的,但由于情感的連貫性讓詩歌依然有著完整的秩序,起承轉合非常緊湊。情感是鏈條,瑣碎的記憶是構成鏈條的材料,一首詩又是構成整組詩的環節,整組詩又顯影出一個翩翩少年,一個才子,他多情敏感,沉湎于內心,有點孤獨甚至有點抑郁,常常對別人忽視的事物沉思懷想,譬如一小塊草地、一杯清澈的水、隕落的風箏、融化的雪花,他的身體里藏著閃電,還有無限的夢想和愛,所有這些都是他的秘密,更是他的能量,驅使他開了天眼,看見常人無法看見的美。所以他的整個少年時光就是“一滴穿行于火焰的水”,是美是詩,是苦難,更是戰勝苦難后的釋然與幸福感。所以這組詩就是一個詩人的成長史,它代表了理想、藝術、境界和愛之源,以及生命的全部意義。這也是《懷舊是傷》的傷之美之審美價值。
需要強調的是這組詩歌的技術探索,這組寫于上世紀80年代的詩歌反映出郭曉曄的技術覺悟,他較早地引進了現代詩歌的直覺、幻覺,意象的強制嫁接和跳躍,他打破時空的秩序,讓所有的意象服從于情感的邏輯,這讓他的詩歌有了陌生感和出人意料的效果。這說明郭曉曄寫作時進入了沉迷的狀態,沉迷中詩人仿佛有神靈附體,讓想象力開始接通天地,這時產生的技藝不是人力,而是神力驅使下的自然天成。
借用一個關鍵詞給郭曉曄詩歌總結就是:情執。是指感情專注到執迷不悟的極端程度,人生很多苦惱源于此。但對于創作來說,它讓郭曉曄把記憶冶煉成詩,把詩歌技藝操練成黃金術。
時值建軍節,選發了兩位軍人的詩歌,但我沒選他們軍事題材作品,而是選了這些反映人性深度的詩歌,也讓讀者看看我們軍人更廣闊的內心,還有他們溫情多情的另一面。
責任編輯 李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