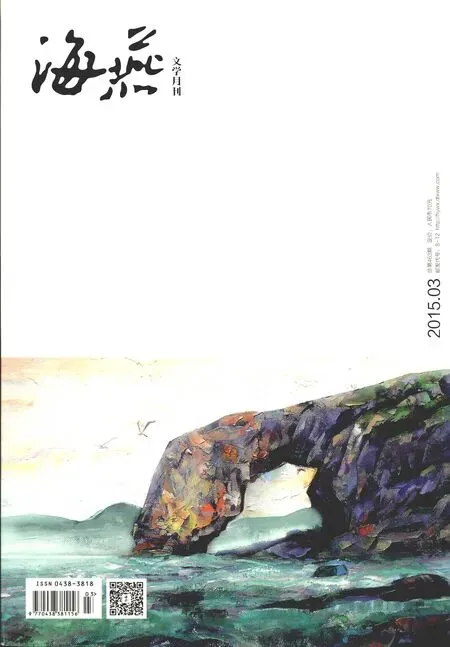靜靜的母親
□段文武
母親是靜靜地離開我們的。
當我在睡夢中接到母親的電話時,窗外正降著這個冬天的第一場雪。雪是悄然而下的,正如母親悄然地離開。電話那端弟弟的敘述是簡單的:凌晨三時許,母親觸碰東西的聲音驚醒了他。他說,好像母親這一夜總是輾轉反側的。她是在沒有開燈,沒有叫醒身邊人的情況下艱難地摸索水杯而不小心“觸”醒了弟弟。其時,母親已是胸悶氣虛,難受口渴。弟急,要送母親去醫院。母親斷然道:“你們睡吧,不去。”又加重。弟要打電話告訴不足一公里遠的姐姐過來,母親不讓:“別叫她了,天黑路滑的。”弟又急著要掛電話給我,母親又制止道:“別告訴你哥哈,大連那么遠,別叫他急三火四地往回跑,不安全。”母親在這之后的不長時間就永遠地閉上了眼睛。待我一個半小時后趕回家里時,見到的是母親靜靜睡著了的模樣:她的臉面如月色般的安然與寧靜。
這一天是二〇一二年的十一月十二日。
母親的一生總是靜靜的,靜靜地來而靜靜地走。母親之靜甚至讓她的兒女們至今想來仍有著隱隱的痛。
母親的一生其實是在極不平靜的年代里走過的。她是長女,在只有姐妹兩個女孩的農耕家庭里,母親其實承擔著長子的責任和男孩的勞累。母親從未跟我們述說過她那個時候的艱辛和對兩個家庭所做的一切。但我的父親說,當我未謀面的姥爺病逝于大饑荒年代后,母親便與父親商議著帶我們從大家族聚集而住的故里遷到了姥姥和小姨居住的另一個村莊。姥姥的最后歲月我是記得的。那時她已臥床不起。中年的母親這時候既要照顧臥床的姥姥和年邁的奶奶,又要操持我們兄妹幾個的飯食和一些院子里的農活。那時候,母親給我的印象總是靜靜的,沒有怨言,沒有脾氣,像在做著她理所當然要做的事。年長的姐姐們說,那時候母親的身體其實并不好,嚴重的風濕病常常讓她疼痛難忍。所以,我最早認識的家里必備藥就是中國百姓那時候最常用而又廉價的去痛片。母親一直到去世,這白色的藥片就沒有離開過她。粗略算來也有幾萬片了。去痛片的最主要功效是去痛的,母親沒有痛嗎?
母親的靜是善良和凝重的。
我記得,在我們這個家庭因為出身的原因而遭受苦難的那些歲月里,母親從沒有去罵過曾經辱罵和攻擊我們家的一些出身優越的鄉鄰。小時候我們卻不理解,母親怎么會把我們都難得吃到的蘋果靜靜塞給批斗父親最狠的那個貧下中農的孩子呢?她怎么還會去幫助一個我們認為的“仇”家呢?他可是搜走了我們家僅存的一點糧食而使我的姥爺、母親的父親在死前想喝一碗粥的愿望都未能實現呀。在社會環境遭受嚴重“污染”的鄉村,民風不再純樸而母親依然是純樸的。純樸的母親讓她的鄉鄰們感慨,這個人沒說的。而在我們那個鄉下,“沒說的”就是沒有一點可挑剔的意思。這是他們能夠給予母親的最高評語。
在送走母親的那天,遠遠近近的鄉鄰們來了。他們有的甚至沒有跟生前的母親搭過話。他們來送母親是聽說母親這個人好。親戚鄰居們對我說:“你們做她的兒女是福啊。”有福分的我們這些兒女最為難過的是在母親口中沒有聽到一句她要求我們為她做點什么的話。我每次從城里回到鄉下問母親想吃點啥用點啥,她都是一副很知足的樣子說:“啥都不缺,別老惦記我。”一直到她去世,我們兄弟姐妹回憶下,母親用過的東西竟沒有一件是她張口向我們索要的。沒有張口要兒女們給他買這買那的母親,在她離世的前些天靜靜地把一個錢包交給姐姐說:“云云快要結婚了,這點錢留給她買點啥。”四萬六千元不是一個大而完整的數目,但這是沒有一點工資收入的母親給她最愛的孫女全部而完整的愛呀!
母親靜靜地走了。兩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