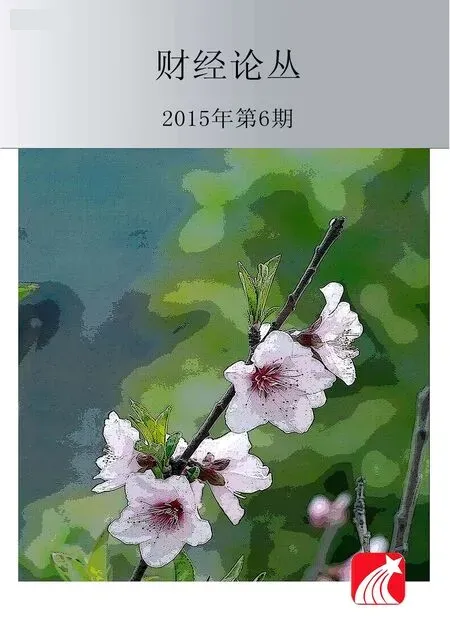人力資本與外出農民工職業選擇
——基于河南省三縣市調研數據的實證分析
陳書偉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河南 鄭州 450046)
?
人力資本與外出農民工職業選擇
——基于河南省三縣市調研數據的實證分析
陳書偉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河南 鄭州 450046)
本文基于河南省三縣市外出農民工的相關調查數據,考察該區域農民工的職業選擇狀況,并著重分析人力資本因素對外出農民工職業選擇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過專業培訓對外出農民工獲取或從事具有向上流動性強、社會聲望相對較高的職業影響十分顯著;更多低水平人力資本特征的外出農民工主要集中于制造業、建筑業和賓館餐飲服務業等低層次職業就業。據此,我們認為大力發展農村職業教育、加強專業技能培訓是促進農民工職業向上流動的有效途徑。
人力資本;外出農民工;職業選擇
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向城鎮非農流動和遷移是現階段中國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伴隨著這種流動和遷移,農民工職業選擇日益成為當前重要的社會經濟現象[1]。當農民工走出農村和土地,面對眾多職業選擇時進行決策的影響因素是什么?即使是來自同一社區或村落的農民工,從經驗積累來說,有的選擇從事有利于人力資本積累的行業,有的從事純粹重復性體力勞動,進一步細化從業領域,有的選擇從事賓館零售業,有的選擇在制造行業就業,這背后是基于何種考量?此外,農民工選擇職業時普遍存在選擇范圍較窄、領域過度集中[2],從某種程度上影響著農民工非農流動和遷移的良性發展,如何提高農民工職業選擇的層次也需從根本上找出完善之道。在調研時本課題組發現人力資本因素對農民工職業選擇的影響非常明顯。基于此,本文擬利用相關調研數據,針對人力資本與農民工職業選擇進行分析,以期考察人力資本從哪些方面作用于農民工的職業選擇及如何影響農民工的職業選擇。
一、相關文獻綜述
關于農民工職業選擇或職業流動影響因素的研究,學術界主要集中于城鄉二元結構、城市勞動力市場分割等方面[3][4][5][6][7][8],而有關人力資本對外出農民工職業選擇影響的研究相對較少。國外學者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程度這種人力資本對農民工職業或職業階層的影響。Alan de Brauw et al(2002)基于我國六省農戶調查數據研究表明,年輕且受過良好教育的農村勞動力在非農就業中占有主導地位。Xin Meng和Junsen Zhang(2001)基于職業選擇的多元Logit模型,對上海勞動力市場上農民工和本地居民的職業分析結果表明,教育、職業培訓等人力資本因素對二者在選擇同類職業時有著不同影響。Andrea Bassanini(2006)基于ECHP數據分析發現,年齡與教育水平對勞動者工資水平的提高具有顯著作用[9][10][11]。姚先國等(2006)、楊曉軍等(2008)分別從農村勞動力職業流動、農民工職業分層、農民工就業決策等角度,分析了人力資本對農民工職業選擇中的重要影響因素[12][13]。史清華等(2007)、白菊紅(2004)等以農戶為單位,考察農戶家庭成員人力資本對整個家庭職業選擇及工資收入的影響[14][15]。此外,還有學者從職業分割與向上流動角度對人力資本的作用進行了分析[16]。
綜合上述文獻,在有關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的研究中,對農民工就業實現及有效轉移給予了相當多的關注,而有關農民工職業選擇、職業流動等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對影響農民工職業選擇因素的研究更是鳳毛麟角。基于此,本文嘗試通過對來自河南省三縣外出農民工的調研數據分析,對人力資本因素進一步細化,在此基礎上對人力資本與外出農民工職業選擇進行實證分析,以期彌補以上文獻研究的欠缺之處。
二、數據選擇、變量說明與統計性描述
本文數據為2013年2月和2013年7-8月兩次在河南省滎陽市、寶豐縣、正陽縣等三縣市進行的調研,樣本點選擇根據河南縣域經濟排名按高、中、低三個層次抽取,每個縣隨機抽取2個行政村,調研對象以農戶為單位,每個行政村隨機調研60個農戶(共計360個農戶),調研方式為入戶調研。調研內容涉及外出流動狀況、流動區域、人力資本狀況、農戶收入狀況及贍養系數等。根據調查樣本數據分析,我們得到有效樣本315戶。
為考察調查區域外出農民工人力資本特征與其職業選擇之間的關系,首先對人力資本變量進行設定。根據經典人力資本理論,具備較高人力資本水平的勞動者能在勞動力市場上獲得更好的就業機會、更高的收入和更有利的職業選擇空間。本文的人力資本變量選擇主要基于舒爾茨(1961)對人力資本的分類,即從健康狀況、受教育程度、培訓、流動及經驗等五個方面考量。基于數據的可獲取性和計量分析的科學性,本文的受教育程度變量主要通過正規國民教育序列衡量,以年齡來代替健康變量,以是否接受過培訓作為培訓變量,以轉換工作次數代替流動變量,以每年平均在外務工時間代替經驗變量。
此外,對職業選擇分布變量進行設定。在外出農民工的職業分類中,根據我國職業標準分類方法并結合本文研究群體的特征,我們將外出農民工職業選擇劃分為零售服務業人員、從事第二產業生產和運輸等人員、辦事員和辦公文員及有關人員、專業技能人員、不便分類的其他人員(如打零工)等五大類。考慮到Logit模型分析對樣本量的要求并結合有關學者的研究,借鑒李春玲(2006)根據職業聲望與社會經濟地位對職業層次的劃分,我們進一步將以上五大類職業選擇綜合為四大類,并按照社會地位和向上流動空間由高到低排列:管理、專業技能類職業;辦事員、辦公文員及相關職業;零售、服務類職業;生產類職業(包括制造業、建筑業等)。被調查外出農民工人力資本特征及職業選擇分布如表1所示。
表1反映了外出農民工總體人力資本特征和職業選擇分布狀況。從表中可以看出,被調查農民工總體人力資本與職業選擇的匹配關系,但就人力資本具體的某一特征對某一類型職業選擇影響的統計性描述并不能得出一個清晰的認識。基于此,在調研問卷中,我們設計了某一人力資本特征對應的職業類型的分布狀況,進而建立人力資本特征與職業選擇對應狀況的矩陣(結果如表2所示)。

表1 被調查外出農民工人力資本特征與職業選擇分布

表2 被調查外出農民工人力資本特征與職業選擇對應關系矩陣(人)
表2顯示,年齡總體上與從事的職業成正比,即年齡越占優勢,從事職業社會聲望的可能性越大。例如,16-30歲從事管理、專業技能類職業和辦事員、辦公文員及相關職業等社會聲望相對較高職業的比例最高,隨著年齡的增長,從事零售、服務類職業和生產類職業等社會聲望相對較低職業的比例逐漸升高。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外出農民工從事社會聲望較高的前兩類職業的比例也在逐漸上升,而從事社會聲望較低的后兩類職業比例卻逐漸降低。轉換工作次數對職業選擇的影響不顯著,但總體上也呈現從事生產類職業的外出農民工轉換職業的次數較少。接受培訓的外出農民工從事社會聲望相對較高職業的比例較大,在社會聲望相對較低職業就業的外出農民工接受培訓的比例較小。每年平均在外務工時間與選擇職業的社會聲望成正比,即在外務工時間越長,在社會聲望相對較高職業就業的外出農民工比例也越高。可見,代替健康變量的年齡指標、受教育程度、培訓狀況和代替工作經驗的每年平均在外務工時間等與外出農民工職業選擇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而代替流動變量的工作轉換次數與農民工職業選擇不如前四個指標顯著。
三、理論模型構建與實證結果分析
(一)理論模型構建
根據前面的分析可知,外出農民工的人力資本表現出來的特征對其職業選擇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主要體現在人力資本特征對選擇某一職業概率的影響。本文采用職業選擇的多元正態Logit模型,并對這種聯系進行實證分析。
在多元正態Logit模型中,外出農民工將按照如下的式(1)做出職業選擇的決策:
(1)
其中,Yi為外出農民工職業類型變量,Xik為外出農民工人力資本特征變量,αm和βmk是模型估計的參數,ui是隨機誤差項。
在職業選擇中,把“零售、服務類職業”作為參照組,其他類型職業選擇與參照組進行比較。本文設置參照組“零售、服務類職業”為1,其他職業選擇數值設為j(j=2,…,J)。因此,相應的Logit模型為:
(2)
其中,Yi=1代表參照組,Yi=j(j=2,…,J)為比較項。自變量x(人力資本變量)對影響因變量Y(職業選擇變量)分布的概率(P)的多元正態選擇模型為:對于比較項m(m=2,…,J),估計相應的多元正態Logit模型為:
(3)
對于參照組,估計相應的多元正態Logit模型為:
(4)
在本文中,對第i個外出農民工來說,Yi=1表示從事“管理、專業技能類職業”,Yi=2表示從事“辦事員、辦公文員及相關職業”,Yi=3表示從事“零售、服務類職業”,Yi=4表示從事“生產類職業(包括制造業、建筑業等)”。
(二)實證結果分析
在人力資本影響外出農民工職業選擇的因素中,我們選取受教育程度、健康狀況、培訓狀況、流動及在外務工經驗等人力資本變量,分別以接受正規教育程度、年齡狀況、是否接受過專業培訓、轉換工作(職業)次數和每年平均在外務工時間來指代,從而形成五組變量,每組變量的賦值情況如表3所示。
基于研究的方便,本文選取零售、服務類職業作為參照組并令該組系數為1,根據調查數據并運用Stata12.0軟件對多元正態Logit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外出農民工職業選擇概率的多元正態Logit模型回歸結果(以零售、服務類職業為參照組)
注:“* ”、“** ”和“*** ”分別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顯著。
基于回歸結果表明,相對于選擇“零售、服務類職業”的外出農民工,性別對管理、專業技能類職業和辦事員、辦公文員及相關職業的影響不顯著,而對生產類職業則比較顯著。年齡較大者趨向于選擇社會聲望相對較低的以體力勞動為主的生產類職業,受教育程度較高者更傾向選擇社會聲望相對較高的管理、專業技能類職業和辦事員、辦公文員及相關職業,轉換工作的次數對社會聲望相對最高和社會聲望相對最低的職業影響顯著,接受專業培訓對管理、專業技能類職業影響顯著,在外務工時間對選擇任何職業的農民工均顯著。
1.相對于參照組,外出農民工選擇管理、專業技能類職業受“受教育程度、轉換工作的次數、接受專業培訓和在外務工時間”等影響較大且均為正影響,系數分別為4.614、1.526、1.878和2.659,并在1%、5%和10%的概率水平下顯著。性別作為控制變量,對外出農民工選擇管理、專業技能類職業影響雖不顯著,但具有正的影響,這意味著男性更多地集中于這一類職業。年齡對外出農民工選擇管理、專業技能類職業的影響是負的,這可能是因為管理、專業技能類職業需要相應經驗、技術的積累,而較高技術或較多管理經驗需較長時間的累積,所以年齡與從事這一類職業的人數并不是必然的正向關系。
2.相對于參照組,外出農民工選擇辦事員、辦公文員及相關職業受“受教育程度、在外務工時間”等較大的正影響,說明受教育程度和每年持續的在外務工時間對選擇此類職業的影響的重要性。性別和年齡對外出農民工選擇辦事員、辦公文員及相關職業的影響較小,分布也比較分散。就轉換工作次數而言,選擇辦事員、辦公文員及相關職業的外出農民工比較穩定,轉換工作的次數普遍相對較少。接受專業培訓對選擇辦事員、辦公文員及相關職業的外出農民工也有相對較大的影響,這說明專業培訓作為一種人力資本累積的形式,在向上流動類職業的選擇中具有重要意義。
3.相對于參照組,外出農民工選擇生產類職業受性別、年齡和每年平均在外務工時間的影響顯著且是正向的。選擇這一類職業的外出農民工的年齡和性別都十分集中,即此類職業的外出農民工主要為年齡相對較大的第二代農民工。而受教育程度卻是負的影響,說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傾向于不選擇這類職業,而選擇向上流動較強、社會聲望相對較高的職業。轉換工作次數的系數為-1.033,說明轉換工作(這里指更換工作的性質)的次數對外出農民工選擇此類職業具有較大的負影響。一般地,在生產類職業就業的外出農民工很少在此類職業以外的行業就業。專業培訓的影響也是負的,說明接受專業培訓的機會與選擇這一類職業成反比,即機會越多,越容易放棄這一職業而選擇其他更好職業。
四、結論和討論
本文基于向上流動和社會聲望等標準,以二元勞動力市場作為分析理論背景,以性別作為控制變量,從年齡、受教育程度、轉換工作(職業)次數、是否接受過專業培訓和每年平均在外務工時間等方面探討了外出農民工人力資本特征對其職業選擇的影響。分析結果表明,相對于參照組(零售、服務類職業),受教育程度、轉換工作次數、是否接受專業培訓及每年平均在外務工時間均對管理、專業技能類職業有顯著影響;對辦事員、辦公文員及相關職業而言,轉換工作次數和是否接受過專業培訓的影響不顯著;對生產類職業而言,受教育程度和是否接受專業培訓的影響不顯著。由此可見,受教育程度和是否接受過專業培訓是影響外出農民工向上流動的關鍵因素。
目前,我國有2.6261億農民工,其中外出農民工1.6336億,但由于職業分割的固化和農民工自身人力資本較低,外出農民工職業選擇比較單一,一般集中于建筑業、制造業和賓館餐飲服務業等向上流動小、社會聲望相對較低的職業。農民工職業選擇的可及程度及其分布不僅不利于外出農民工自身的發展,也不利于我國“人口城鎮化”戰略的推進和產業的升級轉移。基于此,針對農民工的現實特征和流動事實,我們可以有針對性地發展多層次職業教育體系、加強外出農民工技能培訓和專業培訓力度,增強外出農民工通過職業選擇向上流動的機會,提升職業選擇的寬度和廣度。本文雖然得出外出農民工的人力資本特征對其職業選擇具有顯著影響的結論,但由于篇幅和研究主題所限,對外出農民工職業選擇時人力資本之外的其他影響因素及外出農民工職業選擇的家庭決策的影響等方面并未展開深入分析,有待于后續研究的進一步深化。
[1] 張錦華,沈亞芳.家庭人力資本對農村家庭職業流動的影響——對蘇中典型農村社區的考察[J].中國農村經濟,2012,(4).
[2] 高文書.人力資本與進城農民工職業選擇的實證研究[J].人口與發展,2009,(3).
[3] 顧海英,史清華等.現階段“新二元結構”問題緩解的制度與政策[J].管理世界,2011,(11).
[4] 潘澤泉.中國農民工社會政策調整的實踐邏輯——秩序理性、結構性不平等與政策轉型[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1,(5).
[5] 郭繼強.中國農民工城鄉雙鎖定工資決定模型[J].中國農村經濟,2007,(10).
[6] 張慧.農民工就業歧視問題分析[J].上海經濟研究,2005,(10).
[7] 李春玲.流動人口地位獲得的非制度途徑——流動勞動力與非流動勞動力之比較[J].社會學研究,2006,(5).
[8] 李強,唐壯.城市農民工與城市中的非正規就業[J].社會學研究,2002,(6).
[9] Alan de Brauw,Jikun Huang et al.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ural labor markets during the reforms[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2,30(2):329-353.
[10] Meng Xin,Zhang J.S.The two-tier labor market in urban China: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and wage differentials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1,29(3):485-504.
[11] Andrea Bassanini.Training,wages and employment security: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European data[J].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2006,13(8):523-527.
[12] 姚先國,俞玲.農民工職業分層與人力資本約束[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5).
[13] 楊曉軍,陳浩.農民工就業的職業選擇、工資差異與人力資本約束[J].改革,2008,(5).
[14] 史清華,徐翠萍.農戶家庭成員職業選擇及影響因素分析——來自長三角15村的調查[J].管理世界,2007,(7).
[15] 白菊紅.農村家庭戶主人力資本存量與家庭收入關系實證分析[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5).
[16] 符平,唐有財,江立華.農民工的職業分割與向上流動[J].中國人口科學,2012,(6).
(責任編輯:化 木)
Human Capital and The Career Choices of Migrant Workers——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in Three Counties of Henan Province
CHEN Shu-we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46, China)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ree counties of Henan Provinc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areer choices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region,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on the career choices of migrant work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ir educational level and whether they have gained some professional training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areer choices of migrant workers, especially on those who want to get a job with greater upward mobility or higher social prestige. Those migrant workers with low-level human capital characteristics are mainly stuck in low-level jobs of manufacturing, construction, hotels and food service industrie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more efforts should made to develop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s in rural areas so as to help migrant workers move upward professionally.
human capital; migrant workers; career choices
2014-11-01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資助項目(11YJC790017);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13XMZ082)
陳書偉(1981-),男,河南正陽人,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博士。
F241.4
A
1004-4892(2015)06-0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