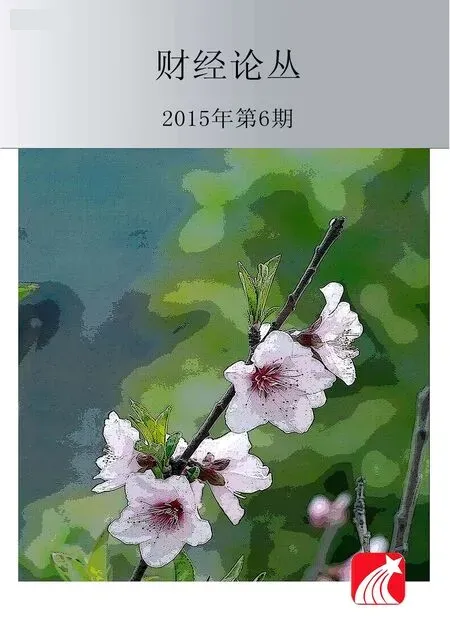監管體系失衡與產品質量選擇
凌 超, 張 贊
(1.復旦大學管理學院,上海 200433;2.上海大學經濟學院,上海 200444)
?
監管體系失衡與產品質量選擇
凌 超1, 張 贊2
(1.復旦大學管理學院,上海 200433;2.上海大學經濟學院,上海 200444)
加強監管力度往往被認為是應對監管失效,促使企業提高產品質量的主要途徑。然而,當監管體系作為一個系統發生失衡時,僅通過加強監管力度往往難以起到作用,需要對監管體系的結構進行調整。本研究的結論表明,在一個監管體系中,事前審批對企業的質量選擇有負向影響,而事后監管則有正向影響。當監管體系發生失衡,出現"重審批,輕監管"的情形時,企業的研發成本將被提高,而違法成本則被降低,企業更愿意選擇低質量的產品。此外,本文發現,最低質量標準作為常用的監管工具,能否發揮作用取決于事后監管的力度。
監管體系;質量選擇;最低質量標準
一、引 言
產品質量對于消費者的效用有著最直接的影響,對產品質量的監管或者規制,是政府進行微觀干預的主要領域。而食品、藥品的質量更是直接關系到消費者的生命健康,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近年來,中國有關食品、藥品質量和安全問題頻發,諸多事件曝光之后,備受指責的除了相關肇事企業外,還有各層級各部門的監管機構。例如,執法力度不足,質量標準過低等。因而,通過加大執法力度,提高質量標準,來改善產品質量和安全問題,已成為各方共識。但是從嚴監管并不必然意味著有效監管,當前的食品藥品質量問題并非簡單地源自于監管不力,而是整個監管體系的失衡,即“重審批,輕監管”。
“重審批,輕監管”是把監管的重心放在市場準入環節,提高進入壁壘,強化事前審批,而忽視生產、流通環節的事后監管,從而造成了監管體系的失衡。而這實際上是中國諸多行業監管體系的通病,例如中國的資本市場監管、安全生產監管、環境規制以及食品、藥品監管等都普遍存在這一問題。“重審批,輕監管”對各行業的共同影響在于提高了企業的進入壁壘,卻降低了企業進入之后的違規甚至是違法成本,從而扭曲了企業的行為決策,難以實現行業監管目標,并最終降低了社會福利。
另一方面,受到各自行業特征的影響,“重審批,輕監管”對于不同行業的具體影響也各不相同。本文重點針對直接關乎民生的食品、藥品監管領域的“重審批,輕監管”問題進行討論。在理清監管體系對企業質量選擇的影響機理的基礎上,進一步說明“重審批,輕監管”會如何扭曲企業的質量選擇,以及其對最低質量標準等質量規制策略效果的影響。
二、文獻回顧
本文討論的核心問題是產品質量監管,而在政策實踐中,最低質量標準(MQS)是一種常見的質量規制手段,理論界對于這一規制政策也有著較充分的討論。Ronnen(1991)[1]認為最低質量標準會提高產品質量,而Kuhn(2007)[2]則指出在低質量產品主導的情形下,最低質量標準會降低社會福利。此外,Maxwell(1998)[3]認為最低質量標準會降低企業的創新積極性。而程鑒冰(2008)[4]則具體討論了最低質量標準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就食品、藥品領域的最低質量標準問題而言,陳艷瑩和楊文璐(2012)[5]以中國乳業為例,認為如果考慮到集體聲譽的問題,設置較高的最低質量標準有助于提高社會福利。同樣以中國乳業為例,浦徐進等(2013)[6]考察了市場結構和消費者偏好對于最低質量標準作用的影響。但是上述對于最低質量標準規制的討論是建立在最低質量標準能夠得到落實的前提下的,而在“重審批,輕監管”的監管體系中,未達標企業完全可以進入市場,最低質量標準可能形同虛設。
具體到食品質量和安全監管的問題,王耀忠(2005)[7],顏海娜和聶勇浩(2009)[8]以及顏海娜(2010)[9]從監管部門間的權力分配及協調合作的角度進行了討論,指出了中國食品安全監管體系中存在的部門協調問題。而浦徐進等(2013)[10]從企業與監管部門間的演化博弈視角討論了食品安全監管體制的缺陷及優化建議,倪國華和鄭風田(2014)[11]從媒體監管的交易成本角度,討論了媒體監管對于食品安全監管效率的影響,吳元元(2012)[12]則從聲譽機制的角度出發提出了構建食品安全監管的長效機制。此外,王常偉和顧海英(2013)[13]還從社會福利的角度討論了最優的食品安全規制程度。上述研究指出了中國食品監管中的部門協調,以及多元監管等問題,但是缺乏對“重審批,輕監管”這一更為根本問題的深入討論。
而在有關藥品監管的研究中,Grabowski and Vernon(1977)[14]以及Grabowski, et al(1978)[15]通過實證檢驗,指出FDA對新藥審批的規定導致了新藥研發的大幅減少,Wiggins(1983)[16]則對此進行了反駁。而Thomas(1990)[17]的研究則表明,雖然整體上看,FDA的審批規定導致了新藥研發的減少,但是對于不同規模企業的影響并不相同。這些研究雖然是針對美國的藥品監管實踐進行的實證分析,但是所討論的問題卻是中國食品、藥品監管同樣需要面對的,即更嚴格的審批是否會帶來更高的產品質量?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重點針對中國食品、藥品監管體系中存在的“重審批,輕監管”的問題進行分析。具體而言,本文試圖通過構建理論模型,探析監管體系對于產品質量選擇的影響機理,從而說明“重審批,輕監管”將如何扭曲企業的質量選擇。
二、理論分析框架
為了更好的理清監管體系對企業質量選擇影響,本文基于寡占的市場結構,以縱向差異化模型為基本分析框架,并借鑒楊其靜(2011)[18]的討論,構建了一個兩階段的博弈模型。
(一)基本假設

同時,市場上存在兩家相互競爭的企業a和b,共覆蓋α比例的消費者。假設兩家企業在0時點之前生產同質產品,差異化始于0時點,并且企業在0時點之前的定價過程中,僅考慮同期競爭。在0時點,每家企業都擁有K單位的資源(作為固定成本的資源),可以選擇投向研發,以開發高質量(質量水平為qH)的產品;也可以選擇繼續生產低質量(質量水平為qL)的產品,同時將資源投向渠道拓展(例如,投放廣告或者向醫院提供商業賄賂),使得該企業的市場份額直接擴大單位。
值得注意的是,企業的資源只夠支持一項決策,即只夠支付研發的固定成本或渠道拓展的固定成本,無法同時覆蓋兩種成本,不失一般性,假設資源數量K=1。此外,開發高質量產品的成本一次性投入,即高質量產品與低質量產品的成本差異僅為固定成本的差異,生產過程中的邊際成本相等為c。
然而,高質量的新產品須經過審批才可以上市流通,審批周期t取決于審批流程的復雜程度。監管機構規定的最低質量標準為qR,并且qH≥qR>qL。因而,當企業選擇生產低質量產品qL時,其不會向監管機構申請注冊審批。但是,企業也必須承受被發現后的處罰風險,假設企業每期被發現的概率相同,為γ,而處罰的份額為單位產品毛利的f倍。*為使本文的分析更有意義,全文做出兩個假設。首先,進行某項投資的利潤一定大于零,即企業進行投資一定比不做任何投資有利,這樣可以集中于討論企業在兩種投資決策中的選擇。其次,假設1-γf>0,因為1-γf<0時,企業選擇低質量產品的利潤為負,企業一定會選擇高質量產品,沒有進一步分析的必要。此外,此處假設處罰為銷售收入的f倍更符合現實,但計算會更為復雜,且并不改變本文研究結論。
(二)模型求解
基于上述假設,如果在第一階段兩家企業同時選擇高質量產品或者同時選擇低質量產品,則將在第二階段面臨同質化的Bertrand競爭,從而利潤都為-1。如果在第一階段企業i(i=a,b)選擇高質量產品,而企業j(j=b,a)選擇低質量產品,則在第二階段將面臨差異化的價格競爭。具體而言,當第一階段企業i選擇投資高質量產品,并進行研發投入,而企業j選擇低質量產品,并進行渠道拓展時,兩家企業的利潤(期望利潤)分別為:
(1)




表1 收益矩陣
注:作者自制。
三、監管體系對產品質量選擇的影響
基于前文模型構建所得結論,本部分將通過均衡分析,探討監管體系對于產品質量選擇的影響機理。
(一)純策略納什均衡
由表1可知,當1-γf>0時,第一階段的純策略納什均衡為(高質量,低質量)與(低質量,高質量),即兩個企業將采取差異化的競爭策略,低質量企業與高質量企業并存。從而,可以得到命題1:
命題1:市場上是否存在低質量產品,取決于事后監管的力度,并且,當事后監管力度較弱時,低質量企業將與高質量企業并存。
命題1表明,杜絕低質量產品的關鍵在于事后監管,而非事前審批。直觀上看,企業是否選擇低質量產品取決于相應的期望利潤,當企業預見被查出的可能性很低,即違法成本很低時,無論事前審批是否嚴格,企業都會選擇生產低質量產品。事實上,命題1意味著單純依靠事前審批對于防止低質量的產品而言是無效的,質量規制的重點應當是加強事后監管的力度。
(二)混合策略納什均衡
進一步地,考慮企業的混合策略,企業a分別以概率m選擇通過研發提供高質量產品,以概率1-m選擇提供低質量產品。則均衡時企業b選擇高質量和低質量產品的收益應當無差異,即需要滿足(3)式:
m(-1)+(1-m)=m+(1-m)(-1)
(3)
可以解得m*滿足(4)式:
(4)


命題2:事前審批對產品質量選擇有負向影響,而事后監管則對產品質量選擇則有正向影響。
命題2表明,事前審批越復雜則企業越缺乏選擇高質量產品的激勵,而事后監管越嚴格,則企業越有選擇高質量產品的動力。其原因在于,更復雜的事前審批實際上增加了企業選擇高質量產品的研發成本,而更嚴格的事后監管則增加了企業選擇低質量產品的違法成本。因而,“重審批,輕監管”實際上是在提高企業研發成本的同時,降低了企業的違法成本,從兩個方面誘使企業選擇低質量產品。
推論1:給定事前審批的復雜程度,事后監管越嚴格,則事前審批對于產品質量選擇的不利影響越小;給定事后監管的力度,事前審批越復雜,則事后監管對于產品質量選擇的正向影響越小。
推論1實際上表明,從激勵企業選擇高質量產品的角度來看,加強事后監管,適當放松事前審批可能會更為有效。而加強事前審批,忽視事后監管,即當前中國普遍存在的“重審批,輕監管”的監管體系最為糟糕。
命題3:在給定的監管體系中,渠道拓展的效果對企業的產品質量選擇有負向影響。
命題3的現實意義很直觀。投入研發以提高產品質量,和加大渠道拓展力度以擴大市場份額是企業需要權衡的兩種策略。企業渠道拓展的效果越好,其提高產品質量的激勵就越小。因而,在“重審批,輕監管”的監管體系中,渠道拓展的預期效果會加重監管體系失衡的不利影響。而這也正是當前中國食品、藥品行業存在的亂象之一。以藥品為例,復雜的新藥審批大大加重了醫藥公司的新藥研發成本,而事后監管不力則使得醫藥公司敢于生產低質量的藥品,最后,向醫院提供商業賄賂的盛行則使得醫藥公司更愿意將資源投向渠道擴展。上述三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就是中國低質藥品泛濫,醫藥腐敗嚴重。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為何國際醫藥巨頭進入中國之后也會把重心由研發轉向渠道拓展,并且商業賄賂的丑聞不斷。
四、監管體系對最低質量標準作用的影響

命題4:最低質量標準對企業的產品質量選擇有正向影響,并且,這種影響受到事后監管力度的正向調節。
命題4指出了最低質量標準的作用以及其發揮作用的條件。最低質量標準對企業選擇高質量產品的促進作用依賴于事后監管的力度,事后監管力度越強,則最低質量標準的作用越強,反之則相反。特別是在低質量產品被查出的概率為零這一極端情況下,最低質量標準將形同虛設,毫無約束力。
因而,本文的分析表明,最低質量標準能否起到促使企業提高產品質量的作用,是以是否有嚴格的事后監管為前提的。相對于質量標準的高低而言,標準能否得到貫徹執行顯得更為重要。例如,對于此前討論較為激勵的瓶裝水、袋裝奶等產品的質量標準問題而言,提高質量標準實際上是提高了市場準入門檻,如果不能同時強化生產、流通環節的監管,而只是單純地提高質量標準,可能會適得其反,強化市場上劣幣驅逐良幣的過程,導致質量的普遍下降。或許,強化事后監管應當先行于提高質量標準。
五、基于保健食品行業的案例分析
(一)行業亂象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國民收入穩步提升,人們更加關注生活的質量,而保健食品作為一種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日益受到消費者的青睞。根據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數據,截至2012年底,全國共有2006家保健食品生產企業,年產值達2800多億元。*《新組建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管總局首次亮相,第一戰指向保健食品領域》,中國青年報,2013年05月17日,http://zqb.cyol.com/html/2013-05/17/nw.D110000zgqnb_20130517_1-05.htm。
然而,在市場需求快速增長的大背景下,中國保健食品行業卻亂象叢生,企業缺乏創新動力,市場中充斥著各種假冒偽劣產品,以至于新組建的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以下簡稱食藥總局)方才成立便開展了保健食品專項行動。*據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網站公告,http://www.sfda.gov.cn/WS01/CL1523/93614.html。截至2013年10月,這次專項行動共立案10698起,涉案貨值達5億多元,罰沒金額近8千萬元,責令停產停業797家,吊銷保健食品生產經營許可證47家。雖然成果顯著,但也說明了問題之重。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大量違規生產經營的中小企業外,眾多行業領軍企業甚至是上市公司也不時地卷入質量丑聞。追根溯源,從企業的資源投向來看,國內諸多保健食品企業將大量的資源投向廣告、宣傳和包裝,而非研發和創新。有業內人士曾指出,國內許多保健食品企業的研發支出占總投入不足10%,遠低于國外同行水平。*《保健食品企業平均壽命僅兩年 研發投入低準入成本高》,新快報,2014年8月19日,http://money.msn.com.cn/business/20140819/08291717378.shtml。作為例證,表2列舉了國內四家具有代表性的保健食品上市公司在2013年和2012年兩年中,各自的銷售費用和研發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即表中的銷售費用占比和研發支出占比)。可以發現國內保健食品企業,重視渠道擴展,輕視研發投入的傾向十分明顯。

表2 保健食品上市公司銷售費用與研發支出占比
注:數據依據各公司年報中披露的銷售費用、研發支出和主營業務收入計算所得,其中,碧生源因在港股上市,選取的營業收入而非主營業務收入。
(二)失衡的監管體系
上述亂象背后的重要原因正是中國保健食品行業存在已久的“重審批,輕監管”的監管體系失衡問題。不同于英美等國將保健食品(又稱膳食補充劑)作為普通食品進行監管,中國保健食品新產品上市前需經過食藥總局審批認證,事前審批程序極為繁雜。具體而言,所有準備投產的新研發保健食品,都必須經過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注冊審批,地方監管部門沒有審批權限。并且這一注冊審批的程序極為繁雜(耗時長,耗費多)。據媒體報道,“申請保健食品批文最快也要一年半,而且需要進行大量的動物實驗乃至人體實驗,而且需要跑很多部門拿批文,耗資達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修正藥業保健品違規套牌》,網易財經,2013年10月24日,http://money.163.com/13/1024/13/9BV1VUDJ00254TI5.html。高昂的時間成本和審批費用使得大量的保健食品企業望而卻步。
但是,與此同時,保健食品生產和流通環節的監管卻缺乏力度。不僅查處頻次低,而且處罰力度小。更為重要的是各地區食品、藥品監管部門人員短缺嚴重,難以進行高頻次的監管執法。公開數據顯示,食藥系統的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一共不到9萬,區縣一級大多缺少分支機構,而作為對比,全國工商系統公務員約為42萬人,分支機構遍布區縣甚至鄉鎮一級。*《地方食藥監管體制改革遭遇人才荒 進程緩慢》,網易新聞,2014年10月6日,http://news.163.com/14/1006/08/A7S2TBEB00014JB5.html。
上述“重審批,輕監管”所造成的結果是在增加企業研發成本的同時,降低了其違法成本,使得企業敢于違法而不愿創新。雖然,輕視研發并非保健食品行業所獨有的問題,也不能完全歸因于監管體系失衡。但是,“重審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業的研發成本,誘使企業將更多的資源投向營銷而非研發,而“輕監管”則直接降低了企業的違法成本。特別是,保健食品行業虛假廣告和夸大宣傳的盛行,使得企業可以通過廣告有效提高銷量,因而企業更愿意生產低質量的產品,并將有限的資源投向廣告。從而,在保健食品廣告鋪天蓋地的同時,保健食品行業的各種質量丑聞也不斷曝光。
雖然2013年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對相關部門進行了合并,以解決部門間協調的問題,并壯大了執法隊伍。但一方面地方機構改革遲緩,并未與中央同步,另一方面,機構合并同時也增加了執法的業務類別,分散了執法力量。特別是食品、藥品監管作為專業的執法任務,還需要大量時間對執法人員進行培訓,因而,單純的機構合并至少在短期內并不能夠增強執法力量。更為重要的是,機構改革并不能解決“重審批,輕監管”的監管體系失衡問題,后者是制度設計的問題,需要從監管思路入手,進行體制革新。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監管對于企業質量選擇的影響是系統性的,監管體系失衡對于質量選擇行為的扭曲比單純監管不力更為嚴重。本文研究結論表明:在一個監管體系中,事前嚴格審批會加大企業選擇高質量產品的研發成本,降低企業的研發積極性;而事后監管不力則將降低企業的違法成本,誘使企業選擇低質量產品,特別是當各種形式的渠道拓展具有較好的市場效果時,企業更加缺乏選擇高質量產品的激勵。此外,本文的結論還表明,最低質量標準能否發揮作用取決于事后監管的力度,沒有有力的事后監管作為支撐,最低質量標準只能是形同虛設。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認為要改變當前中國食品、藥品以及其他行業存在的質量問題,不應當僅僅是簡單地加強執法,而是要從監管體系的角度進行系統考慮。特別是要基于企業行為決策的微觀視角,改革監管體系,改變“重審批,輕監管”的現狀。
具體而言,一方面需要適當放松事前審批,提高審批效率,另一方面則需要提高查處頻次,加大處罰力度,并嚴厲打擊非法的渠道拓展行為。
[1] Ronnen U.Minimum quality standards,fixed costs,and competition[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22):490-504.
[2] Kuhn M.Minimum quality standards and market dominance in vertically differentiated duopol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2007(25):275-290.
[3] Maxwell J.Minimum quality standards as a barrier to innovation[J].Economics Letters,1998(58):355-360.
[4] 程鑒冰.最低質量標準政府規制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8,(2):40-47.
[5] 陳艷瑩,楊文璐.集體聲譽下最低質量標準的福利效應[J].南開經濟研究,2012,(1):134-144
[6] 浦徐進,何未敏,范旺達.市場結構、消費者偏好與最低質量標準規制的社會福利效應[J].財貿研究,2013,(6):96-104.
[7] 王耀忠.食品安全監管的橫向和縱向配置——食品安全監管的國際比較與啟示[J].中國工業經濟,2005,(12):64-70.
[8] 顏海娜,聶勇浩.制度選擇的邏輯——我國食品安全監管體制的演變[J].公共管理學報,2009,(3):12-25.
[9] 顏海娜.我國食品安全監管體制改革——基于整體政府理論的分析[J].學術研究,2010,(5):43-52.
[10] 浦徐進,吳亞,路路,蔣力.企業生產行為和官員監管行為的演化博弈模型及仿真分析[J].中國管理科學,2013,(11):390-396.
[11] 倪國華,鄭風田.媒體監管的交易成本對食品安全監管效率的影響——一個制度體系模型及其均衡分析[J].經濟學(季刊),2014(2):559-582.
[12] 吳元元.信息基礎、聲譽機制與執法優化——食品安全治理的新視野[J].中國社會科學,2012,(6):115-133.
[13] 王常偉,顧海英.食品安全規制水平的選擇與優化——基于社會福利函數的分析[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3,(3):54-60.
[14] 楊其靜.企業成長:政治關聯還是能力建設?[J].經濟研究,2011,(10):54-66.
[15] Tirolf J.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M].Cambridge,MA:MIT Press,1988.
[16] Grabowski H,VERNON J.Returns to R&D on new drug introductions in the 1980s[J].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1994(13):383-406.
[17] Grabowski H,VERNON J,THOMAS L.Estimating the effects of regulation on innovation: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8(21):133-163.
[18] Wiggins S.Product quality regulation and new drug introductions:Some new evidence from the 1970s[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81(63):615-619.
[19] Thomas L.Regulation and firm size:FDA impacts on innovation[J].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1990(21):497-517.
(責任編輯:風 云)
Unbalanced Regulatory System and Product Quality Choice
LING Chao1, ZHANG Zan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Stricter regulation is always thought to be the main way against failure of regulation, and to promote the product quality. But when the regulation system loses balance, stricter regulation alone will not work, and an adjustment in the regulation system is necessary.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approval procedure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quality choice, whereas supervis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A regulatory system with strict approval and light supervision will improve the enterprises’ R&D costs, reduce the illegal costs, and make enterprises more apt to choose the low-quality products. The paper also finds that whether the MQS works or not depends on the strength of supervision.
unbalanced regulatory system; quality choice; minimum quality standard
2014-11-09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71102027)
凌超(1987-),男,安徽明光人,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生;張贊(1978-),女,河南鞏義人,上海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F062.9
A
1004-4892(2015)06-009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