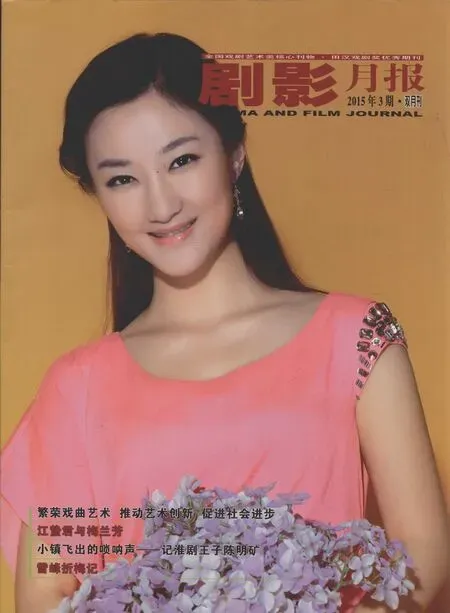江蟄君與梅蘭芳
■梁冰
江蟄君與梅蘭芳
■梁冰
京劇四大名旦之首的梅蘭芳雖然生于北京,長于北京,但他的祖籍是江蘇泰州,同江蘇有著特殊的桑梓之情。早在上世紀20年代初,年方25歲的梅先生應“末代狀元”張謇之邀,初到南通演出時,就曾受到江蘇父老和梨園同行的熱烈歡迎,出現過“千車爭聽”、“萬巷都空”甚至“擲果盈車”的動人場面。故鄉人的盛情,令他終生難忘。
梅蘭芳同江蘇京劇界也有著千絲萬縷的感情聯系。上世紀50年代初,江蘇京劇名角王正堃(大武生)、王琴生(老生)、于金奎(銅錘)、楊小卿(小生)、孫玉祥(老旦)等就曾同他到南海前線慰問人民解放軍,演出配合默契,十分成功。1956年春,他應邀來南京演出后順道回故鄉泰州尋根,時任江蘇省京劇團負責人的江蟄君全程陪同,同他結下了親密的友誼。
蟄君同志是資深劇作家、戲劇評論家。他知識面廣,中外古今、文史數理皆有涉獵,對古典文學、京昆藝術情有獨鐘。早在1937年抗日烽煙乍起,他剛新婚不久即在六叔江世侯(江上青烈士)的指引下,從揚州遠赴皖東北投入艱苦的對敵斗爭,并于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后,江蘇建省前,他曾獨當一面,擔任蘇北實驗京劇團團長。1955年受命參與組建江蘇省京劇團,并擔任首任副團長。他在1956年陪同梅先生回故鄉泰州期間,同梅朝夕相處,意氣相投。途經揚州時,一道游覽了瘦西湖的長堤春柳,拜訪了平山堂的名剎高僧,品嘗了美不勝收的揚州早茶。其間,他以淵博的學識,向梅介紹了揚州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梅先生非常喜歡揚州的翡翠燒賣,蟄君由此及彼,從富春的翡翠燒賣、千層油糕到大麒麟閣的京果粉、京江臍;從素有儒商之稱的揚州鹽商對中國戲曲的貢獻到四大徽班進京;從揚州八怪到鄭板橋的道情十首;從唐代詩人李白的“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到杜牧的“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娓娓道來,如數家珍,梅先生為之神往。梅也就京劇的求新、革新、創新問題同他做了多次探討。蟄君一向認為戲曲藝術的生命在于推陳出新,他主張“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學藝術,必須緊跟時代的步伐,不斷求新、更新,才能發展下去。”對于毛澤東主席提出的“推陳出新”口號,他認為是“辯證地闡明了戲曲藝術繼承與發展的客觀規律,指出了戲改運動的正確方向。”他還認為,“過去有成就的表演藝術家,都曾不斷地予以革新和豐富,對我國戲曲藝術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這些觀點,都與梅先生一貫的創新精神和“移步不換形”的主張不謀而合。50年代中期和后期,蟄君曾率江蘇省京劇團多次陪同梅先生到各地巡回演出,足跡遍及中南、西北、華北、華東各省,幾近半個中國,因而更加深了他同梅的感情。
梅蘭芳愛詩,早年便將自己的書房命名為“梅花詩屋”;蟄君出于家學淵源,也愛唐詩宋詞。梅蘭芳愛畫,曾先后拜吳昌碩、陳師曾、齊白石為
師,善畫佛像、仕女、翎毛、梅竹;蟄君也愛畫,早年曾就讀于上海美專國畫系。所有這些,都使蟄君在與梅的交往中有了許多共同語言。在藝術見解上,他們也有許多相同之處。蟄君長期在一線劇團工作,深感演員加強文化學習,提高文化素養的迫切性。梅先生也有同感。1956年冬到武漢演出時,梅在武昌東湖賓館曾同蟄君談到他演出《霸王別姬》的感受。他說,演員如果不了解楚漢相爭的歷史背景,不知道這出戲的祖本《千金記》傳奇的梗概,就不可能體會到劇中所表現的意境。正如沒有讀過湯顯祖的《牡丹亭》,就不可能演好《游園驚夢》。蟄君對此十分贊同。因此,他后來每次到北京出差,都要到護國寺甲一號看望梅先生和梅夫人,受到梅家的熱情款待。他的儒雅風度和談吐,給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梅家上下都親切地稱這位“江團長”為“揚州才子”。他也高度贊揚梅的藝術成就,認為他“不僅出色地繼承和發揚了我國優秀的古典戲曲傳統,而且始終表現了勇于革新、勇于創造的進取精神,為我國民族戲曲事業作出了不朽的貢獻。”對于由王瑤卿創立、經梅蘭芳使之更加完美的“花衫”這一新型京劇行當,他十分欣賞,一直希望創作一個可以充分發揮“花衫”之所長的京劇劇本。1959年,梅先生為了向國慶10周年獻禮,排演了新戲《穆桂英掛帥》。蟄君對于梅在這個戲里的大膽創新十分欽佩,進一步加強了自己的創作欲望。后來終于以《王昭君》一劇實現了他的夙愿。
作為劇作家的蟄君同志,參與創作或整理、改編的劇本除京劇現代戲《耕耘初記》、取材于《水滸》的《元夜鬧東京》、取材于徽劇的《贊貂蟬》以及《寇準罷宴》等,而根據曹禺同名話劇改編的《王昭君》則堪稱他的代表作。他通過對大量正史、野史、民間傳說以及其他有關資料的研究、分析,客觀、科學地對比了歷來對和親題材的不同處理和當時國內對話劇原作的不同意見,肯定了曹禺的創作思路,在原著的基礎上,發揮京劇特有的優勢,并借鑒梅先生在《穆桂英掛帥》中的創新精神,綜合運用唱、念、做、打、舞等表現手段,多視角、多側面地塑造了女主人公的藝術形象。他不僅充分調動皮黃聲腔的藝術表現力,而且在《出塞和番》一場中采用【梧桐雨】、【楚漢吟】、【牧羊關】等曲牌,載歌載舞,細膩傳神地刻畫了王昭君在規定情境中的復雜心情,從而彌補了話劇原著的不足。在立意上,劇本截然不同于馬致遠的《漢宮秋》以及《樂府詩集·昭君怨》、《西京雜記·王昭君》、敦煌《王昭君變文》中悲劇色彩的描繪,以積極樂觀的態度塑造了一個為民族團結而“自愿請行”的王昭君。特別通過反復出現的“主題歌”,熱情頌揚了她和匈奴呼韓邪單于“長相知,不相疑”的和平愿望和真摯愛情。把歷代文學作品中的一個“哭哭啼啼”的深宮少女變成了一個深明大義、顧全大局的和平使者。在藝術表現手法上,借鑒梅蘭芳《穆桂英掛帥》的創作實踐,融青衣、花旦、刀馬旦于一體,
充分發揮了花衫之所長是一個同尚(小云)派《漢明妃》各有千秋的梅派《王昭君》。
一代巨匠梅蘭芳離開我們已經54年了。才華橫溢的“揚州才子”江蟄君離開我們也已26年。26年前,當蟄君同志在江蘇省腫瘤醫院病逝時,同他手足情深的三弟、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同志曾手書《子夜歌》一闋,以寄托沉痛的哀思:
弟兄哀樂何能免,
追思飛越情無檻。
湖畔攜同歸,
江頭唱落暉。
東圈門里醉,
淮上尋芳翠。
山水曲中音,
溪翁翰墨瓶。
【注一】文中所涉江蟄君藝術觀點,均引自《江蟄君文選》(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 10月版)。
【注二】《子夜歌》中的“淮上尋芳翠”指江蟄君赴皖東北參加革命,投入艱苦的對敵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