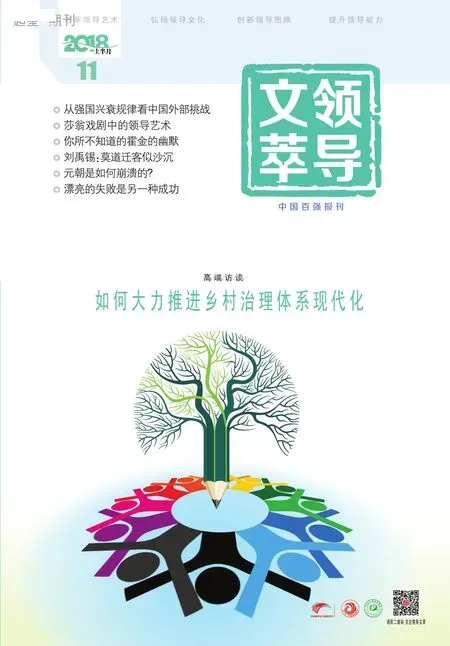毛澤東與斯大林
□李海文
毛澤東與斯大林
□李海文
毛澤東未能向斯大林一吐積郁
毛澤東對斯大林評價甚高,稱他是 “世界人民的導師和朋友,也是中國人民的導師和朋友”。
斯大林對毛澤東的評價也不低。1949年毛澤東首次訪蘇,蘇聯隆重歡迎,精心安排火車在正午12點到達車站。當天下午6時,斯大林率全體政治局委員在克里姆林宮會議廳的門廳列隊歡迎,這是很破格的。當時斯大林緊緊地握著毛澤東的手,端詳了一陣說:“你很年輕,紅光滿面,容光煥發,很了不起!”他對毛澤東贊不絕口:“偉大,真偉大!你對中國人民的貢獻很大,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子!我們祝愿你健康!”又說:“你們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祝賀你們前進!”
但是這兩位偉人之間的相處并不融洽,在首次會談中,毛澤東見到斯大林后想表明自己的心跡。他說:“我是長期受到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可是不等毛講完,斯大林立即插話:“勝利者是不受審的,不能譴責勝利者,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的這句話使毛沒有把內心的話講出來。
戰略配合還是戰術配合
實際上,毛澤東和斯大林產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如何處理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的關系。斯大林在處理與兄弟黨的關系時,更多地站在愛國主義立場上,表現了大國沙文主義的傾向,缺乏平等精神。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后,斯大林致電毛澤東,以商量的口吻詢問中共能不能抽調若干旅或團擺在長城附近,牽制日軍。毛澤東回電斯大林如實地講明我們的情況,說明我們的力量一集結,目標就大了,就會遭到襲擊、圍剿,會吃大虧。另外,我們武器很差,無法同日本進行大會戰。
當德軍打到莫斯科城下時,斯大林再次致電毛澤東,希望派一部分力量向長城內外方向發展。毛澤東沒有給以肯定的回答,只說部隊調動有困難。
1942年7月德軍向斯大林格勒進攻。雖然日本正忙著進行太平洋戰爭,但仍有不少日本要進攻蘇聯的傳聞。斯大林無法判斷這些傳聞的真偽,一方面積極組織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另一方面3次致電毛澤東。
在第一封電報中,斯大林要求中共抽調八路軍一兩個師的兵力到內蒙古和外蒙古邊境地區,接受蘇方提供的可裝備一兩個師的新式武器。
毛澤東研究后回電說:武器,我們自然是需要的。但調一兩個師的兵力通過蒙古草原到達邊境去接受武器卻是不可想象的,因為敵人有空軍,而我們沒有。這樣,我們的部隊在未到達目的地之前,就會被敵機消滅掉。這個方案恐怕難以實現。
過了一段時間,斯大林第二次來電說:可否分批派出較小型的游擊部隊到滿蒙交界地區輪番接受較小批量的武器,以加強抗敵力量。當時日本在這一帶制造無人區,控制甚嚴。毛澤東也否定了第二個方案。
1943年初,斯大林第三次來電建議中共中央考慮調若干個師團部署在長城內外一線,雖不是為了進行大戰役,但也能牽制日軍力量,或增加它的后顧之憂。
斯大林是世界無產階級導師,他的建議遭到拒絕恐怕只有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敢為之。所以,斯大林格勒戰役后,蘇聯進入反攻,斯大林與毛澤東很少有電報往來。蘇聯從未向毛澤東透露雅爾塔協定的內容。
能不能勝利,敢不敢勝利
引起毛澤東不快的第二件事是抗日戰爭剛剛結束,蔣介石要搶奪勝利果實。而斯大林卻致電毛澤東說:中國不能再打內戰,否則,就可能把民族引向滅亡的危險地步。毛澤東看后很生氣地說:“我就不信,人民為了翻身搞斗爭,民族就會滅亡?!”
為了回答斯大林,毛澤東在1946年4月寫了《關于目前形勢的幾點估計》,這篇文章認為:目前人民民主力量超過了反動的力量,美、英、法同蘇聯不會破裂,遲早會妥協。毛澤東十分慎重,直到解放軍打到外線,穩操勝券,才將此文于中央內部公布。由此可見當初斯大林的電報對毛澤東的壓力有多大。
1948年在大決戰前夕,蘇聯政府轉來國民黨政府給蘇聯的一封信,請求蘇聯居中調解國共之爭,要求首先停止內戰。蘇聯的這個舉動客觀上對即將面臨決戰的中國共產黨潑了一瓢冷水,所以毛澤東寫了1949年元旦社論,針鋒相對提出“將革命進行到底”。
毛澤東處理美、蘇關系有本質的區別
蘇聯人對中國共產黨和美國人的來往一直不放心。1944年7月美軍向延安派了觀察組,隨后美國總統羅斯福私人特使赫爾利到延安談判。美國是反法西斯的,特別是在太平洋地區,對蔣介石政策影響最大。因而,中國共產黨和美國建立了半官方的外交。
蘇聯人對此種關系以及雙方的頻繁往來十分關心,同時又感到不安,有所疑慮。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宣布“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并派劉少奇到莫斯科向斯大林匯報中國革命進展情況及其政策,派江青以養病的名義到蘇聯。隨后規定與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在方法、態度及時間上應有的區別。
毛澤東無時無刻不在維護民族尊嚴、獨立與自主,從不聽命外人的擺布。當他不能向斯大林直言時,就采用東方人的智慧和做法,以柔克剛,堅持由周恩來到莫斯科簽訂中蘇條約。雙方僵持了半個月,最后斯大林做出讓步。他的讓步是不情愿的。就在周恩來已到莫斯科開始談判后,斯大林還給毛澤東打電話做最后一次努力。毛澤東直截了當地回答:“我沒有什么新的意見,一切由周恩來商談辦理。”
斯大林去世后,毛澤東在接見米高揚時一吐積郁,講了自己對共產國際、對蘇共及對斯大林的意見。他最大的意見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分“老子黨”“兒子黨”的做法,認為“一方發號施令,另一方得俯首貼耳,唯命是從”,“往往危言聳聽,借以嚇人”。
(摘自《中共黨史拐點中的人物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