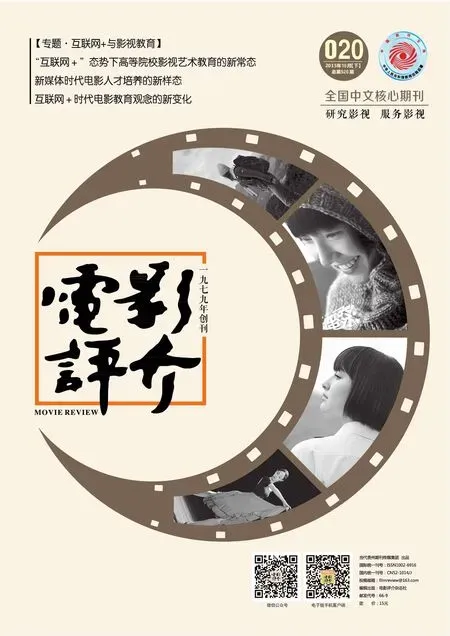互聯網+時代電影教育觀念的新變化
康 寧
目前,我們的社會已經進入了多屏的互聯網+時代。互聯網的出現,不僅改變了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閱讀方式,同時也改變了普羅大眾的認知方式和社會文化的傳播方式。互聯網已然是影像生存、發展和傳播的利器,移動媒體和多屏時代的到來,又進一步改變了信息的傳播渠道和傳播景觀。對于電影而言,創作者從投融資、到策劃、宣發、檔期的確定、放映形式等等,都嵌入到了互聯網。
一、“網生代”的出現顛覆了傳統電影的生產模式
與互聯網+時代相伴而生的,便是“網生代”。“網生代”的出現截然不同于過去任何一種電影代際,它讓電影生產的每一個環節都涂抹上“互聯網+”的色彩,縮短了電影制作者和觀眾之間的距離,便捷的消息互通使得電影的制作更能最大程度地滿足觀眾的期待視野。
之前中國導演的代際劃分,大致都是按照時間來進行的:建立了中國本土電影雛形的鄭正秋、張石川等為第一代;創造了三四十年代社會寫實風格的蔡楚生、孫瑜等為第二代;1949年后致力于社會主義語境表達的崔嵬、謝晉等為第三代;1979年后追求影像語言電影化的張暖忻、謝飛等為第四代;1985年后使中國電影走向國際的陳凱歌、張藝謀等為第五代;90年代后嶄露頭角的張元、王小帥等為第六代。而在“網生代”出現之后,首次出現了用空間來對電影產業進行劃分:具體分為四個層面:網生的電影產品、網生的觀眾、網生的導演以及網生的電影企業。四個層面共同交織、相互作用,構成了“網生代”這個概念。
網生代的誕生對整個電影的生產過程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很多電影會基于網絡對于觀眾的期待進行數據統計,根據大數據來判斷什么層級的觀眾關注什么樣的話題,選取最受關注的熱點進行設計和包裝,在電影中呈現出來。它對電影內容選擇、用戶洞察的“預測作用”產生前所未有影響,以高人氣網絡小說以及《跑男》《爸爸去哪兒》等改編的電影為例,強大的票房和點擊量一次次印證互聯網時代電影產業發展的演變,受眾從大眾化、被動的客體逐漸變為個性化的主體。電影《黃金時代》就是一個典型的利用大數據來制作的電影,盡管最終的票房并不理想,但也不失為一種有意義的嘗試。也只有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才會產生諸如《煎餅俠》《夏洛特煩惱》及《十萬個冷笑話》這一類電影。
2015年年初上映的電影《十萬個冷笑話》投資僅有1000萬元,宣發費用僅為287萬元,全部用于互聯網營銷。影片上映第一天便收回成本,兩周后票房破億元。這部沿著“漫畫—網絡動畫—院線”一路走來的電影,沒有任何硬廣告宣傳,在國產動畫電影幾乎成為兒童電影近義詞的銀幕上,悄悄地完成了一個近乎不可能的任務。
由此可見,網生代不僅對于電影生產環節產生影響,對電影的宣傳、發行模式也有較為直接的影響。較之于傳統的海報、電視節目里的預告宣傳、電影放映之前的貼片宣傳,今天的電影宣傳主要投放于移動媒體,諸如地鐵、公交車的屏幕以及移動終端(手機、pad,個人電腦屏幕)的宣傳。由于觀眾都是“網生代”,還增加了線上線下的互動。
觀眾的本質身份也隨之發生了改變,從之前簡單的擁有觀看權利,變成了用戶,是能與產品互動,能產生具體精確數據的觀眾。這一系列的數據統計,都對整個電影產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網生代的出現對電影工業流程產生較大的沖擊和影響,電影制作者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通過大數據迎合觀眾的口味,但也并不能一味的屈尊迎合。這些大數據只是一個制作層面的參考,并不能成為電影生產的指揮棒。電影畢竟是社會文化特別重要的一部分,還是要承擔起社會文化的責任,負擔起通俗文化對觀眾應有的塑造“三觀”的責任。
二、 互聯網思維、媒介素養與高等教育的技術革新
電影生產的工業模式的轉變,促使電影創作者及電影的學習者都得轉變思維,增強對媒介素養的認知和培養,以適應整個產業的發展變化。媒介素養的培養對于國民素質的提高,尤其青少年來說至關重要。英國媒介素養教育專家大衛·帕金翰曾經指出,媒介素養教育的重心是如何通過媒介學習有效地使青少年為其未來的成年公民身份的責任做好準備。[1]
通常所說的互聯網思維,指的是給予網絡提供的大數據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是在(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科技不斷發展的背景下,對市場、用戶、產品、企業價值鏈乃至整個商業生態的進行重新審視的思考方式。[2]互聯網產生的最重要的參考指標便是大數據。關于大數據(Big Data),研究機構Gartner給出了這樣的定義:“大數據”是需要新處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強的決策力、洞察發現力和流程優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長率和多樣化的信息資產。缺少數據資源,無以談產業;缺少數據思維,無以談未來。大數據思維,是指對大數據的認識,對企業資產、關鍵競爭要素的理解。[3]培養互聯網思維和提高媒介素養,是順應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
對于大的教育觀念而言,互聯網+時代的出現,互聯網、大數據的頻繁應用,帶來了教育的技術革新。作為技術手段的電影教育而言,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加快了人類社會從“閱讀印刷書頁”為主的時代進入到以“閱讀電子書頁”(其中包含影視書頁)為主的時代的歷史性進程。電影技術和流媒體傳輸技術的結合,成了推動高等教育革命性變革的決定性因素,并成為正在孕育興起的以技術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4]北京大學胡詠教授在其演講“失控的未來:互聯網的位移趨勢”中,談到大學教育方面,認為,未來大學可能失去對于高等教育的控制權,互聯網給學生們提供了越來越多的課程選擇,正在替代現有高等教育的模式。“通過互聯網,你可以坐在全球的教室里,選擇各國最好的課程進行學習。”營銷端才是互聯網思維的核心,互聯網思維首先改造的是營銷方式,其次才是產品、服務的理念。營銷是通過研究任性來拓展市場,而互聯網思維提供的,就是在互聯網時代如何進行產品銷售的方法。[5]這就是互聯網+時代所特有的教育現象。
北京電影學院王志敏教授認為,高等教育改革的真正革命性的手段應該是電影。因為電影本身就具有記錄與合成的雙重本性,是一種可能給高等教育帶來偉大革命性變革的品質。特別是當電影技術與計算機數字技術、互聯網傳輸技術和移動通訊技術,一句話,就是流媒體傳輸技術結合在一起的時候,電影就能如虎添翼地把曾經發生過的或可能發生的,見證過的或未能見證過的,但是都同樣激動人心、頗具啟發意義,偉大歷史性或者經典型的時刻,永久定格、反復傳輸和隨意瀏覽,完成大量豐富信息從近距傳輸到遠距傳輸,從當時、定點、定量、單次傳輸,到延時、不定點、不定量(暫停、倒退、快進),反復可瀏覽傳輸,從“移媒體”到流媒體,從有線到無線,一句話,跨時空隨意多終端傳輸。[6]
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思維和認知方式,并作為一種手段為整個社會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帶來了技術革新。尤其,電影教育觀念的新變化必須同樣引起重視。
三、 電影教育觀念的新變化
電影雖然誕生時間并不長,只有120年的歷史,算是人類歷史上最年輕的藝術門類,但其發展直接影響著社會進步與精神文明建設,對提高一個民族的思想文化影響力、在國際社會中的整體形象,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高校影視文學教育是對大學生進行文藝素質教育、提高其人文素養的重要途徑之一。它不但具有最基本的娛樂審美價值,更承載著重要的社會責任,具有影視專業教育、歷史教育和現實教育、道德教育、民族文化精粹傳承教育、科技發展水平促進教育等多項社會教育功能。[7]新的社會歷史進程中的電影教育,順應時代變化,出現了觀念上的新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就電影專業的技能學習而言,途徑更加便捷和多元化;二是電影教育從專業教育走向通俗教育。
互聯網技術的推動和數字技術的沖擊下,遙不可及的電影制作已經走下神壇,成為大眾能夠觸手可及的娛樂方式。電影制作設備的數字化使得影片的制作成為已經能夠為普通大眾所接受,體積小型化的攝影機和實時監看也讓職業電影攝影師之前對膠片時代的絕對權力喪失殆盡。[8]拍電影也已經由小眾群體的職業生涯,變成了普羅大眾觸手可及的娛樂和記錄生活的方式。電影愛好者可以隨手打開互聯網,學習關于電影制作的任何方面的任何知識、技巧,從劇本寫作、影片拍攝到后期制作一應俱全。比較知名的網站包括:V電影網(www.vmovier.com)、拍電影網(www.pmovie.com)、影視工業網(www.107cine.com)、大型開放式網絡課程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除了制作,電影的傳播平臺、傳播渠道走向前所未有多樣化,觀眾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傳播渠道觀看電影。很多優秀教學影片的獲取越來越容易,一些原來只有電影專業院校的學生才能觀摩到的經典電影、藝術電影,如今電影“發燒友”們都能看到,并通過這些影片學習拍攝、剪輯等方面的技巧。這樣一來,電影專業技能的教學、學習變得比以前更加容易,不管是綜合性大學的教學開展,還是電影愛好者的自主學習,都獲得了新的機遇。技術、行業資源在競爭中的作用不像以前那么巨大,創意、人文底蘊等因素的優勢開始凸顯。[9]在電影愛好者能通過多種渠道接觸多種多樣電影的情況下,對于電影良莠的判斷日益重要,對電影的愛好和學習亟需同電影技巧一樣,變成觸手可及的通俗教育。
幫助電影愛好者,尤其幫助電影的初學者接觸到優秀的、適合他們的影片依然是個重要問題。同時,還需要幫助孩子們客觀地看待他們所處的影像世界,對影像呈現和客觀現實間的差距有較為清晰的認知和判斷,盡量減少影像世界中的負面因素,例如暴力畫面等對孩子的影響。這也是這幾年蓬勃發展的“媒介素養教育”所提倡的。電影教育和媒介素養教育都包括培養對媒介內容的批判性認知,也包括相關的媒體實踐,但電影教育更注重對動手能力的培養,它不是停留在觀眾接受層面,而是培養觀眾從受眾向創作者轉換,讓攝影機和我們受眾的紙筆一樣,成為人們日常使用的工具。[10]這是目前國內的電影教育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
談及具體的電影教育方式,可以參考較有代表性的中國和韓國兩種教育方法。就北京電影學院來說,藝術和技術緊密結合是新世紀電影教育的必然趨勢。對新技術在電影創作中的作用不僅受到學院創作專業的重視,從事理論研究的教師也對此特別關注,認為計算機技術能給電影帶來革命性的影響,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電影形態的多元化發展,另一個方面是電影制作方式的根本性”[11]。在這種形勢下,“我們必須從現在就考慮電影教育方式和專業分工的適應性問題”[12]。正如北京電影學院校長張會軍教授所說,不管是作為專業教育的電影藝術,還是作為通俗教育的媒介素養,“教育過程中,除了考慮新媒體比如網絡傳播、移動的用戶傳播的特征外,更應該考慮的是作品的整體質量、如故事、講故事的方法、影像的質量、視覺風格和視覺吸引力等等。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今天,有創意的令人新奇的驚天動地的故事越來越少,面對故事的頻發,要在內容上有所創新,我們在教學過程中強調學生將人生體驗拔到一定的高度,使之親情化、友情化、感情化,打動自己才能感動別人”[13]。重視借鑒新技術、新科技,更為重視內容和藝術。
現代社會可以說是一個以影像媒體為中心重整空間表現的時代,電影不再單單是一種藝術表現形式,而是綜合所有影像媒體的中心。特別是數字技術和其他媒體的自由融合使得電影得到了新生與發展的可能。自電影誕生以來,數字化為其帶來了巨大的技術變革,這不僅作用在電影制作過程中,就連電影發行、上映環境和實現意象再現以及電影語言等方面均帶來了巨大的模式變化。在韓國,如果說過去是偏向于以培養導演和攝影技術為中心的電影教育的話,那么現代則是需要進化電影教育方法論的時代。在數字網絡發展所形成的媒體融合的嶄新環境下,對正在經歷這種變革的電影本體性認知變得尤為重要。根據對這一趨勢的解讀方式的不同,過去傳統的電影教育課程和教育方法論也似乎應當隨時尋求新的變革,從而努力開發完善進化中的教學方法:1)向電影文化的回歸;2)融合教育。[14]
結語
時至今日,電影教育已經是普及教育極為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尤其對青少年而言,電影已經不僅僅是認識世界、了解世界的窗口,也不僅僅是記錄生活的工具,而是培養影像思維,塑造人生觀價值觀的重要的教育手段。
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網生代”對于傳統電影制作、宣傳、發行等諸多方式的沖擊和改變,促使人們培養互聯網思維,提高媒介素養。而電影作為媒介素養最為重要的一部分,它的改變帶來了教育技術方面的革新,也在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人們的電影教育觀念,不僅對于電影技術的學習變得更加多元和便捷,同時電影也逐漸成為通俗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1](英)大衛?帕爾翰.英國的媒介教育:超越保護主義[J].楊曉麗,譯.媒介研究,2004(2):71-77.
[2][5][8]李博.“互聯網思維”下的電影教育[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5(3-4):111,118,114.
[3]趙國棟,易歡歡,糜萬君,鄂維南.大數據時代的歷史機遇[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21.
[4][6]王志敏.試論電影技術引發起電影高等專業教育突破性變革的路徑[C]//劉軍,康寧.電影教育:歷史、觀念、新標桿北京電影學院首屆電影教育國際論壇論文集.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5:402,398.
[7]蔣東玲,侯英.淺析影視文學對大學生的社會教育功能[J].電影文學,2008,04:126-127.
[9][10]許航.新媒體時代電影教育的轉型[C]//劉軍,康寧.電影教育:歷史、觀念、新標桿北京電影學院首屆電影教育國際論壇論文集.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15:483,484.
[11][12]陳宇鍇,俞劍紅.北京21世紀電影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0(4):80.
[13]張會軍,馬聰敏.創作實踐型中國電影教育[J].當代電影,2013(1):19.
[14](韓)崔禎仁,范小青.數字時代的電影教育——韓國電影教育的經驗與思考[J].現代傳播,2015(3):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