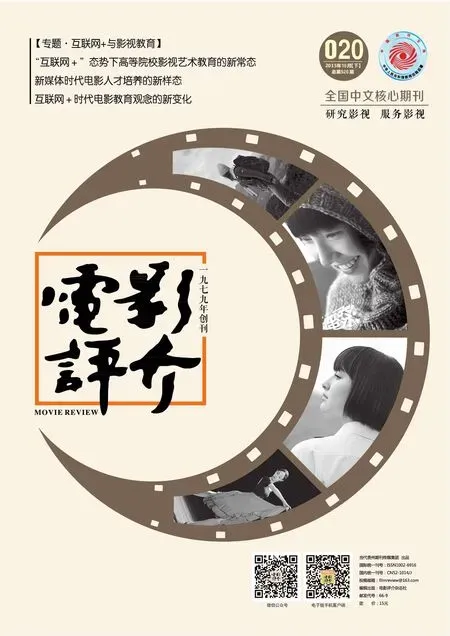論語言文學(xué)藝術(shù)向視聽藝術(shù)的轉(zhuǎn)化——以電影《活著》為例
郭 靜
隨著視聽時代的到來,在視聽為核心的感性主義形態(tài)泛濫的今天,影視業(yè)可謂空前興盛。在影視藝術(shù)的發(fā)展過程中,總是離不開文學(xué)那源源不斷的養(yǎng)分滋養(yǎng)。就經(jīng)典小說而言,其改編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zhàn)。文學(xué)改編電影的過程中,編劇、導(dǎo)演可謂其“作者”,而文學(xué)作品對于導(dǎo)演而言只是一系列堆積的素材,仍需再次加工,方可滿足影視的視聽藝術(shù)表達(dá)。在影視界總有這樣一個聲音:“改編比不上原著文學(xué)作品。”很多人認(rèn)為經(jīng)過改編和藝術(shù)轉(zhuǎn)化了的作品,難以全面展現(xiàn)原著文學(xué)作品深刻的內(nèi)涵。事實上,就改編而言,必須明確:“改編并非原著作品的復(fù)制”。
一、 從語言文學(xué)藝術(shù)向影像的轉(zhuǎn)化
就圖像性內(nèi)容而言,其實無需文字這一間接媒介,其可以直接訴諸于觀者的視覺系統(tǒng),滿足其視覺需求。文學(xué)間接所展現(xiàn)的形象,為讀者所帶來的快感幾乎全部有賴于激發(fā)讀者的想象力所實現(xiàn),其間接性反而展現(xiàn)了最為廣泛和深刻的表達(dá)力,其所能夠表達(dá)的幾乎也不受到任何物質(zhì)的限制。電影則是一系列機(jī)器運作下的產(chǎn)物,其會受到各類條件的約束,并將文學(xué)所帶給大家的自由想象,轉(zhuǎn)化為鮮明而生動的場景,而這本身就是一件極富挑戰(zhàn)性的過程。
所謂的影像,是通過攝影造型與構(gòu)成元素直觀地作用于觀者視覺系統(tǒng)的銀幕形象,就多數(shù)觀眾而言,印象最為深刻的還是影片中那鮮明而生動的視覺部分,而最具吸引力的效果往往都是先滿足于人的眼睛,然后才是滿足其耳朵的電影。很多大導(dǎo)演證明了這點,就像導(dǎo)演路易·達(dá)更所提到的那樣:“電影所具有的情緒感染力、震撼力首先在于其所賦予人們的視覺力量。”[1]阿貝爾·岡斯也發(fā)表過相同的看法:“如果畫面未充分加以利用,致使電影喪失了應(yīng)有的視覺感染效果,應(yīng)將其力量還給它,歸根結(jié)底,所有思想,哪怕是最為抽象的思想,均在形象下生成。”[2]由此可見,影視就其本性而言,其劇情的發(fā)展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影像造型實現(xiàn)的,影像就是敘述故事的基本單位。
正是由于影像塑造的逼真性及審美表達(dá)的直觀性,使得觀眾能夠無障礙地加以感知,這是電影的優(yōu)勢。正如巴爾扎克道盡千言萬語所描繪的19世紀(jì)的巴黎,就電影而言,文學(xué)作品可以不厭其煩地采用語言對人物、環(huán)境等加以細(xì)致描寫,但永遠(yuǎn)難以達(dá)到電影那般簡易而精確,同樣地,對于法國巴黎,電影只需一個鏡頭、一個影像就能呈現(xiàn)。同時,影像的直觀性、確定性,使得其在藝術(shù)審美上出現(xiàn)了如下負(fù)面作用:這樣極易導(dǎo)致影片的審美單一化與強(qiáng)迫化,導(dǎo)致多元性缺失。當(dāng)公眾觀看影片時,本身就是一個被動者,所感受到的也是影像所強(qiáng)加于他的畫面,因而限制了觀者的想象、聯(lián)想空間。
二、 影片的色彩藝術(shù)
作為最具吸引力的視覺元素,色彩在視覺藝術(shù)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早期電影而言,色彩只是為了真實地再現(xiàn)客觀事物,而隨著電影藝術(shù)的逐步發(fā)展和成熟,在電影大師的藝術(shù)實踐過程中,他們開始意識到色彩的表意、造型作用,并深化了對影片色彩功能的理解,不僅進(jìn)一步發(fā)揮了其寫實性,還借助于色彩的論說性,對作品中所存在的獨特事物加以展現(xiàn),生動地賦予其夸張性,強(qiáng)化某一色彩的存在感。在這些大師的手中,色彩成為了賦予影片象征意義的關(guān)鍵因素之一,成為烘托場景、深化主題、塑造形象的法寶。
提到色彩的象征性,不能不提大導(dǎo)演張藝謀的作品,如此復(fù)雜而鮮明的色彩運用,在影片《活著》中更是有諸多可圈可點之處。在電影《活著》的片頭,就出現(xiàn)了以大號紅色字體充斥整個黑色銀幕的字幕。片名就像是強(qiáng)行闖進(jìn)一般,將鋪張的紅色映入觀眾的眼簾,張導(dǎo)借以紅色征服了觀眾。對于電影的導(dǎo)演和制作者,開場字幕就是展現(xiàn)影片主題和意圖的第一個機(jī)會;隨著影片的徐徐開篇,作為全篇主題色彩的紅色,依然如線索一般貫穿始終。在賭場中,極具傳統(tǒng)中式風(fēng)格的大紅燈籠,幾乎遍布了賭場的各個角落,紅艷艷的蠟燭將每張賭桌點紅,雙色紅黑骰子引誘著被賭性沖昏了的心智,賬目上鮮紅色的指紋更是使人觸目驚心。在皮影戲場景中,戲臺背景是紅彤彤的,不僅映紅了演員的臉,更映紅了前臺的幕布。在鳳霞婚禮上,婚前由二喜所畫的一幅光芒萬丈的紅色毛主席畫像映入眼簾,婚禮進(jìn)行中,熱熱鬧鬧的伴奏隊伍捧著毛主席畫像走街過巷,很多人臂上佩著鮮紅的袖章。直至影片的最后,鳳霞的鮮血染滿大地,張導(dǎo)調(diào)動了該部影片的紅色因素,借意紅色向觀眾傳達(dá)主題,表達(dá)獨特的寓意。在此過程中,紅色作為一個手段,幾乎各個場景都貫徹著紅,開場的紅寓意著制約力,退場的紅蘊(yùn)意著制約力的衰減,最終一切歸于那幅照片,這種象征貫穿整部影片,可謂意味深長。
與電影相比,文學(xué)作品《活著》中的色彩卻并無重點運用,文字所傳達(dá)的色彩,雖然也有多重描述,卻也只停留在讀者主觀世界中,對于小說中,富貴對色彩的回憶,也僅僅為“黑的夜、白的雪”,只能是僅此而己。
三、 影片美術(shù)視覺藝術(shù)
無論是好萊塢大片,還是本土電影,為了能夠有效地增強(qiáng)影片的觀賞性、藝術(shù)性,在對細(xì)節(jié)的處理方面都十分仔細(xì)。在影片《活著》中,美術(shù)細(xì)節(jié)的處理可謂巔峰之作,無論對于場面恢宏的戰(zhàn)爭場景,還是街頭各式小標(biāo)語、賬本、存折、火紅的筷子,所有置景無不深刻地傳達(dá)了情感,不僅使觀眾印象深刻,更升華了影片的主題。在影片的開始,就流露出了絲絲哀傷,這不得不歸功于影片美術(shù)制作與設(shè)計的選景與音樂配置,在陜北那個古樸而純美的小街場景以及配合的主題音樂,使影片一開頭就深刻地傳達(dá)出悲情這一電影主題。
在鏡頭的推進(jìn)下,地域風(fēng)格鮮明的“皮影戲”步入臺前,歷史悠久的皮影道具,隨著燈影搖搖晃晃,影射出低落、灰暗的情緒。在賭場中,每當(dāng)全景展示皮影戲時,均為富貴、龍二賭局步入緊張局面之時,這種場景深刻地烘托了賭局的緊張氣氛。在賭債記賬本上,連串的鮮紅手印使人心靈不禁一顫,這一排又一排的紅色手印,就像是預(yù)言一樣,預(yù)示著富貴最終破產(chǎn)的必然性。
當(dāng)敗光了祖宗家業(yè)后,富貴的心情、言語、動作無不流露出其內(nèi)心的復(fù)雜性,當(dāng)?shù)吐洹o奈的家珍離家后,坐著三輪車出月亮門,并漸行漸遠(yuǎn)時,使觀眾內(nèi)心難免跟著失落。隨后的場景處理得也十分巧妙,場景中老宅廳堂的正中間,所掛著的大楷警世語,與龍二追門討債之場景相互映襯,給人無盡而深刻地諷刺蘊(yùn)意。老爺子活生生被氣死之后,憔悴的富貴耷拉著腦袋,弓起身子將破什搬離,同老屋檐之下那無情而冷峻的“拆”字,使人不禁開始同情這個嗜賭成性而傾家蕩產(chǎn)的敗家子。在漫天的大雪中,寬大的灰柱下蜷縮著富貴疲憊的身子,臨街?jǐn)[著幾件家傳小玩物出售,這進(jìn)一步映襯了他家境破落之后的狼狽與不堪,較之前賭場上得意與風(fēng)光的形象對比不可謂不鮮明,而這一美術(shù)場景也意味深遠(yuǎn)。
隨后家珍的回來使富貴的人生重新恢復(fù)了活力,不僅如此,她還誕下了兒子,“小別后的重聚”與溫馨有愛都在那小小破落的一方窗中淋漓盡致地傳達(dá)出來。在接下以皮影戲為生的生計中,皮影戲中男女的嬉戲難免使人感慨萬千。在影片中,家珍始終渴望擁有一個真正的家,而這又何嘗不是觀者的期待,與觀者對家的情緒相通。
但好日子并不長,閃亮的刺刀劃破了幕布,也打碎了沉浸在皮影戲中而幸福生活的男女老少,使影片中所有人物與觀眾的深切期待都化為了泡影。自此,富貴又開啟了一段更為艱難的人生旅途,堆積如山的尸體、暴斃的好友老全,都使得他倍感恐懼,并發(fā)自內(nèi)心地感受到“活著”真好,也堅定了他“活著”回家的這一信念。在抗戰(zhàn)勝利之后,歷經(jīng)千辛萬苦活下來的富貴,提著破舊的皮影箱子重新回到了家中,此時映入眼簾的是:殘缺的頹壁、啞了的女兒和滿面淚流的妻子家珍,這些無不使其感到心酸,更讓觀眾倍感凄涼。隨后,春生后來成了區(qū)長,但他并未帶給富貴好運,反而由于倒車將墻撞塌,友慶被砸死,在該場景中,美術(shù)置景幾乎將其情緒感染力發(fā)揮到了極限,蒼茫而荒涼的曠野中,飛舞著片片紙錢,在一個孤獨的墳頭,一個泛灰鋁盒上放著20個餃子,一雙鮮紅的筷子置于下面,所有的這些都散發(fā)著濃濃的悲涼,感染著觀眾的情緒,使人禁不住淚流滿面。
生活仍要繼續(xù),女兒鳳霞也長大成人,在鎮(zhèn)長的熱心介紹下,萬二喜用他殘疾的身軀表達(dá)了對她深刻的愛,他雖然行動不便,卻熱情地幫富貴修葺家,二喜、鳳霞在院墻上生動地描繪毛主席,富貴夫婦流露出了會心的笑,這無不使人感到幸福可能近在眼前。隨后,鳳霞的婚禮到來,影片在此以樂述哀,雙喜大字鮮艷火紅,拍攝全家福的道具,都使人隱隱地感受到喜慶后可能隱藏著的悲涼。在這一場景中,喜慶的道具發(fā)揮了其作用,詮釋了其背后隱含的內(nèi)涵,如此描述使人感到這一幕就像隔壁所發(fā)生的故事一般,引發(fā)了集體的情感認(rèn)同。
當(dāng)富貴全家為懷了孕的鳳霞而倍感高興之時,全國“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地開始了,美術(shù)置景中到處都是張貼的大字報。家珍為臨產(chǎn)的鳳霞所準(zhǔn)備的紅雞蛋還未使人體味到幸福的滋味,就被影片中瘋狂的現(xiàn)實所打破。婦產(chǎn)教授被打為反革命派,不得不接受批斗、游街,情緒高漲的紅衛(wèi)兵面對著難產(chǎn)而大出血的鳳霞,似乎視而不見。死神又一次光顧了富貴這一家,在該段中到處散布的大字報,火紅滾燙的雞蛋,鮮血染紅的紙團(tuán),都成為一記重錘,沉重而猛烈地敲打著觀者的心,并進(jìn)一步升華了影片的悲情主題。
四、 影片的聽覺藝術(shù)
在利奧塔早期作品中曾經(jīng)就“語言的東西”與“影響的東西”進(jìn)行了較為全面的區(qū)分。他曾說過:“語言的東西就像弗洛伊德理論所提到的二級層面,是自我結(jié)合現(xiàn)實原則來表達(dá);而影像的東西正如首要層面一樣,是本我結(jié)合快樂的原則來表達(dá)。也就是說,如果想要將利比多能量全面地釋放出來,語言的東西就必須結(jié)合訴諸變形、詞語化形式,依托現(xiàn)實原則方可間接實現(xiàn)。對于影像的東西而言,需要全面打開感覺記憶,于無意識層面中直接實現(xiàn)。”[3]由此可見,文學(xué)是一種語言藝術(shù),因其訴諸于抽象化的聲音符號,為了深刻地理解它,必須加強(qiáng)對詞句的準(zhǔn)確理解、科學(xué)地組織方可實現(xiàn),只有這樣,才能塑造深刻的文學(xué)形象,才能將理性和反思相結(jié)合,從文學(xué)藝術(shù)中獲得快感。
在聽覺藝術(shù)方面,影片《活著》也頗有可圈可點之處。在影片的開始,音樂就采用冷色調(diào)胡琴、合成器音色進(jìn)行了首次呈現(xiàn),與其后喧嘩的賭場氛圍形成了極生動的對比,音樂取自于陜北曲種,也是為了更為生動地流露出絲絲憂傷。雖然情節(jié)跌宕變化下,音樂的變化也隨之起伏,但由于該音樂固有的特點,所有變化都是在悲情這一主題情緒上來回波動。當(dāng)賭場內(nèi)的皮影戲表演聲突然高了起來,不僅大鼓被推倒發(fā)出刺耳聲音,更是富貴即將傾家蕩產(chǎn)之時,在音樂的渲染下進(jìn)一步營造了緊張的氣氛,暗示著主人公的必然破產(chǎn)。在父親被氣死,全家不得不流落街頭之時,富貴萬般絕望,而家珍回家并為他生了兒子之時,音樂節(jié)奏加快,使人感受到了一絲喜悅,配以弦樂柔和之音,帶給觀眾一絲溫馨與希望,但音樂中仍存有悲情。友慶被砸死時,伴著家珍的痛苦嘶喊聲,背景音樂采用板胡這一悲苦的音色,不知是音樂烘托了語言,還是語言感染了音樂,也許兩者都有。當(dāng)死神帶走了鳳霞時,鼓聲漸漸熄弱,就像鳳霞的心跳聲,逐漸微弱,直至消亡。[4]隨后那熟悉的旋律重又增強(qiáng),隨著家珍的哀嚎聲,也向我們揭示了影片的結(jié)局。
有人說是影片《活著》成就了張導(dǎo),但也有人說是這部影片慶幸遇到了他,這部影片的改編不可謂不成功,而其最為成功之處,當(dāng)屬其將小說中的視聽因素,依據(jù)電影思維重新加以組合,并取其意、忘其形地加以創(chuàng)新,同時,實現(xiàn)了語言文學(xué)藝術(shù)到視聽藝術(shù)的成功轉(zhuǎn)化,可謂一箭雙雕。
[1]Robert Stam, Alessandra Raengo.文學(xué)和電影指南[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5:25.
[2]克里斯丁?麥茨等.電影與方法:符號學(xué)文選[M].李幼蒸,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2:125.
[3]愛德華?茂萊.電影化的想象——作家和電影[M].邵牧君,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3:25.
[4]崔穎.從冷漠旁觀到苦難希望——余華和張藝謀共有的“活著”[J].濟(jì)南大學(xué)學(xué)報,2005,11(2):103-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