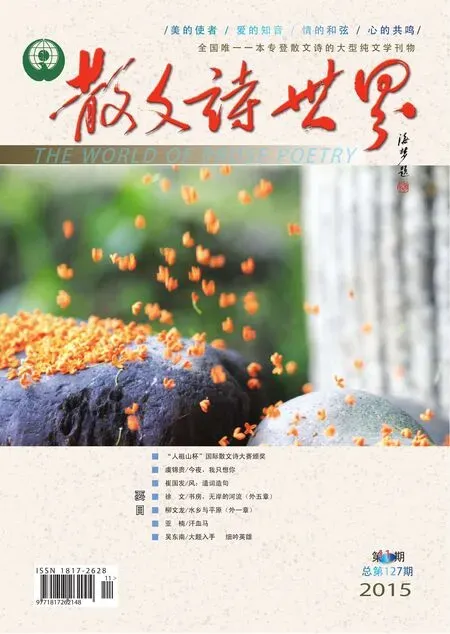旁觀者(外五章)
四川 潘玉渠
街上人來人往,河流般的風景,壅塞著視線。
十月的風,單薄而冰冷。一如久已淡漠的往事,無法裹緊世界消瘦的身體。
我時常認為——
自己可以冷眼旁觀,旁觀城池與山水自行運轉;旁觀那些似真似假的喟嘆,得到最終的慰藉。
我也堅信——
汽笛可以喚回沉溺多時的面孔;一個靈魂健全的人,便能輕易撬開偏見壓在身上的峰巒。
置身一隅,豈論江湖深遠?
旁觀,又何必牢記那些恍若煙云的身影。
一個人往返,只需靜靜地兜緊胸膛里的雨水,聆聽自己空曠的心跳而已。
過故人莊
過故人莊,雞犬相聞。
我,不是孟浩然。人無法與詩篇同不朽,恰是時光殘忍的一種佐證。因為,潦倒的肉身竟抵不過虛無縹緲的靈魂。
這在俗世,顯然是本末倒置的。
重陽節又近了。城市里的菊花哪有鄉間的馨郁。
沒有故人的故人莊,便成了一口冷寂的井。我徒然地路過這里,徒然地自我哀傷,感覺到有些溫暖的東西正在加速下沉——
連一抹影子都漂浮不起。
今日無酒,還能與誰話桑麻?
庭院早已頹敗,唯有一檐的秋風秋草,灌進了眼睛……
碎 念
藍白相間的天空,是一塊蠟染的布料——呈現著不祥的族群。
烏鴉騎著貓頭鷹周游列國,亦算王者;狐貍擅長催眠;毒蛇在洞穴醞釀私心。你愿做兔子,還是豺狼,森林都無異議!
上帝與撒旦是一對孿生兄弟。一個揮灑萬丈光芒,一個散布沉沉的黑夜。
內心的海岸線,在猶疑不定的風濤中綿延萬里。隱喻中的暗礁與珊瑚,正是為人生定調的音符——
善惡,只在一念之間。
像風一樣輕
沉甸甸的過往,一如融化不了的堅冰,從臉龐滲出霜來。
身后的視野總是空曠的。不管我如何懷念,如何忽略殘酷的時光,在記憶里蟄伏的鹽堿,都會將內心侵蝕得異常貧瘠。
要讓心情由隱晦轉為晴朗,只能自我寬慰——
騙自己前方有湖藍色的天空,有白色的月光和蓮花,有清澈而寂靜的夜,還有涅槃的火鳳凰。
像苦行僧那樣,為自己找一個可靠的說辭,讓自己淪喪,痊愈,再淪喪;讓那些已然兜不住的妄念,被遠遠地流放;讓自己變得像風一樣輕,一樣輕……
舊時光
我們習慣將過往從心底打撈出來——
曝曬,把玩,乃至煎煮烹炸。
我們松懈地把守內心的城池,讓閑愁一遍遍地殃及池魚。
我們惦念的山水,有著舊年畫的古拙;而現代化的街衢,卻涂抹了太厚的脂粉。
從來就不存在牢不可破的堡壘,包括歲月與青山。我們愿重走當年的路徑,用干凈的懷想來修補缺憾與罪責。
而不是——
在繁華的都市,盲目地左拐,右轉。
早 課
在墻上,暗黑色的時辰,正在兀自撥動。
十月的韌帶——
柳枝如鞭,抽響了黎明前的那段渾濁。
窗簾開始泛光了,晨風乍暖還寒。
對于內心,我們拒絕作壁上觀。我們希冀著湮滅的溫暖,重新回歸;消散的光明,再次崛起。
萬物怡然自得,人間如一張空白的稿紙——
這是最淺顯的道理。我們還懂得,春夏秋冬會在北國與江南間變幻;草木枯榮是一件極其瑣屑之事……
潘玉渠,1988年生于山東棗莊,現居四川金堂,課余散文詩寫作。有作品見諸《散文詩世界》 《星星》 《詩選刊》 《延河》 《中國詩人》 《四川文學》 《散文詩》等刊物,部分作品入選多種年度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