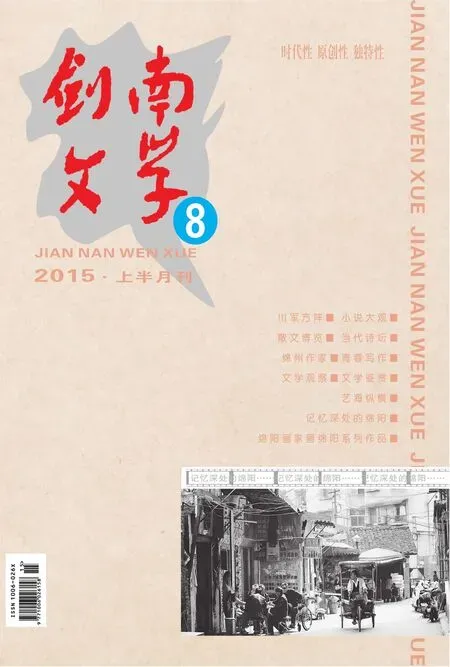艾米麗·迪金森的詩歌主題
■趙蕾
艾米麗·迪金森的詩歌主題
■趙蕾
本文試圖通過對于艾米麗·迪金森眾多詩句的分析,來討論其詩歌的主題特點,揭示出其詩歌不同尋常的主題闡釋方式。
艾米麗·迪金森認為 “詩歌就像是一個圓”。而詩歌的主題自然就是圓心。她的詩歌像是一個神秘的國度,想了解這個神秘國度里最美麗動人之處嗎?作者自己是不會告訴你答案的。我們必須要通過理解這個“圓”里各種意向來理解她的 “神秘國度”。詩歌“I gained it so—”和 “It dropped so low—in my Regard”里,中心點都是“it”。艾米麗·迪金森的詩句在這個中心點周圍反復徘徊,一直試圖接近詩歌想要討論的主旨,但是又不直接切中目標。艾米麗·迪金森在她的 “I watched the Moon around the House”當中也是這么做的,“月亮”被比喻成一個“陌生人”、一個通過長柄望遠鏡觀察的“監視者”,一朵“無莖的花”。因為無法觸摸,我們從來都無法確認月亮到底應該是個什么樣子的。在艾米麗的詩歌里,我們了解一樣事物不是通過這一事物和我們生活當中熟知的東西有多少相似性,而是通過其不同和距離感。
這種不可侵犯的自我覺醒意識成為許多艾米麗·迪金森詩歌的基本準則。在 “I reason,Earth is short—”中,觀察者和被觀察對象在每段的最后一行采取了陳述和反陳述的表達手法。在“Before I got my eye put out”中,中間三段詩的每段最后一行逐漸將焦點從 “世界”縮小為“自我”。而“自我”也成為整個段落主旋律下的微弱音符。在那些“自我”逐漸隱匿的詩歌里,比如“I felt a Funeral in my Brain”,很難說詩歌主旨到底變成了瘋子腦中的臆想還是一個美好的神秘國度,又或者兩者都不是,因為詩歌早在我們找到答案之前就已經戛然而止,只留下意猶未盡的回味。總的來說,艾米麗·迪金森和玄學派詩人們保留了人們的主觀意識和客觀事物之間的距離感,而浪漫主義詩歌則試圖填充這個距離。一個浪漫主義詩人通常會把這種疏離感隱藏起來,模糊詩歌讀者和意向之間的界限和區別。正如華茲華斯1805年在Prelude中所作的那樣:“What I saw/ Appear’d like something in myself,a dream,/A prospect in my mind”。 玄學派詩人建立主客觀聯系的方式則有所不同。如同一只鳥,起初看到的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只有使用形象生動的語言進行類比,這些不同才逐漸消失。
與同時代的浪漫主義詩人不同,艾米麗·迪金森認為和辭藻的選擇相比,對于主題的整體看法更為重要。對于她來說,一行詩中有多少個詞并不重要,都能很好地表達出既定的意思,盡管每個詞的意思可能千差萬別。她對于詞與詞之間的關系有強烈的興趣,這種興趣有很強的結構性暗示。她的情節并不刻板,也不會體現一首詩中各個細節之間的強烈聯系。在“I never lost as much but twice”中,有一系列重復的形象,人們很難從邏輯上或是語言之間的聯系上去理解它們。這一系列意象在詩歌主體部分是突然出現的:“Burglar!Banker—Father!”這一行詩中包含了意象的劇烈過渡,互相之間看似毫不相關,然而掩藏于意象之下的模式,每對之間都是相同,在詩歌當中是一個整體:竊賊-受害者,銀行家-債務人,父親-孩子。每組詞在力量上逐步弱化,但如果要說這首詩的主題即此似乎又不大適合。“Loser”,這首詩中的人物角色試圖從遠距離探尋離奇的失敗。而這失敗藏匿于詩歌之中。
艾米麗·迪金森熱愛這種在主題周圍徘徊,但是從不直接切入或者點明主題的表達方式。這種做法在“To hear an Oriole sing”當中表現的淋漓盡致。在詩歌的第一段落,列出黃鶯的兩個相反特征,這一段的最后一行針對前兩行提出了一個矛盾的維度。這一模式貫穿全詩。第一段提到的鳥兒在第二段被否定或在即將切入主題的時候故意繞開話題。各個意象之間否定表達的使用起到了幫助意象不斷轉換的作用。詩歌的第三段開始深入,但是未至詩歌主旨,只是在主題周圍打轉。每個段落之間保持著存在于內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間的疏離感。每個段落的中心都是黃鶯歌聲中未言明的主旋律。這個未曾言明的主旋律也是作者留給我們的懸念。這首歌是屬于鳥兒的,歌聲隱而未宣的主旨是屬于她的聽眾的。然而詩歌的第三節通過給聲音添加顏色在歌的意義和聽眾之間建立了模糊的聯系:“The Fashion of the Ear/Attireth that it hear/In Dun or fair.”這里元音的省略再次制造了聽眾的疏離感, “whether…whether.”詩歌外部找不到其真實意義,又不能完全相信感覺,在理解這首詩的時候,我們還能依賴什么呢?懷疑的態度成為迪金森詩歌中模糊或被省略掉的中心的佐證。詩人自己也承認很難在黃鶯這首詩中讀出確切的主旨或是找到明確的中心。
玄學派詩人的興趣點在于靈魂和軀體的二元性。這一點在多恩的“The Dreame”和艾米麗·迪金森的“No rack can torture me—”當中都有所體現。第一段落引入一個身體隱喻,“the knitting of bone”(織骨)來描述靈魂:“Behind this mortal Bone/There knits a bolder One—.”第二節的敘述沒有接續但以不同方式重申了第一節的意思,平凡的意象和異國情調結合起來:“saw”和“Scimitar”結合起來。第三節進入了一個新的圓周,是觀察者新的陣地:巢中的鷹和天空中的鷹。詩歌中心靈魂和軀體的二元性已經逐步在第三節當中開始模糊:“The Eagle of his Nest/No easier divest—And gain the Sky/Than mayest Thou—”。 在第四節中出現了自由和束縛兩個矛盾存在,鷹既要飛上云霄又受到巢的牽絆。在 “No Rack can torture me—”中,缺失的背景或者說被省略掉的詩歌中心是詩歌結構的要求,用兩個悖論連接起詩歌的第三第四節。
這種由內至外的轉移在“I felt a Funeral, in my Brain”中是靈魂發展的方式。在詩歌末尾,靈魂最終找到歸宿。詩歌頭兩節戲劇化地原地踏步,第三節到第五節加快速度。動作伴有聲音,和 “A Route of Evanescence”與“I heard a Fly buzz—when I died—”中表現出來的一樣。在頭兩節的靜止和空間限制之后,有人拖動棺材,發出吱吱的響聲,之后鐘聲響起。第四節有很強烈的靈魂四周的空間拓展,像是被搖擺的鐘強制打開似的,通過這個開放空間,靈魂開始飄蕩,輕點主題之后全詩結束。與其他玄學派詩人不同,艾米麗·迪金森對于主旨和周遭環境的分離更感興趣。當主旨離開語境,詩歌結束。詩人的視角很孤獨,從外到內,從一扇窗到另一扇,在時光中被迫移動。艾米麗·迪金森的宗教背景使得她不愿輕易總結人類對于上帝的所知。清教徒對于上帝的認識來自于日常熟悉的事物,他們認為上帝是神秘的,人類不可隨意揣測上帝的意圖。要通過類比的方式來看上帝。艾米麗·迪金森在詩歌中去除時間感,使用劇烈而使人出乎意料的動詞來連接一個個時間段落,因此我們在迪金森的詩歌中,被迪金森所使用的被動動作吸引,而忽略了從一個意象進入到下一個意象所需要的時間。
在艾米麗·迪金森的詩歌中,讀者要使自己從已知中抽離出未知。這么做的目的并非要使目標更明顯,并非要全面看清,而是要從多個角度看到永恒。迪金森詩歌的主題從不輕易告訴讀者,而是需要讀者在接近主旨周圍的距離當中不斷地徘徊,揣測,靠近。
(內蒙古科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