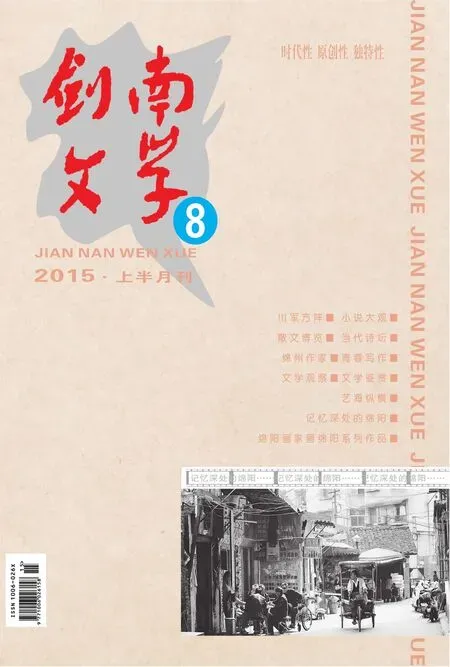鄉土之戀,鄉魂之泣
——莫言《白狗秋千架》的文學感染力
■陳智秀
鄉土之戀,鄉魂之泣
——莫言《白狗秋千架》的文學感染力
■陳智秀
莫言的短篇小說《白狗秋千架》,以看似荒誕卻合情合理的結局將感染力推向高潮,敘寫了主人公暖的悲慘命運。本文從全文線索“白狗”,主要人物暖及其鄉土主題等三方面評析該作品感染力的生發、支柱及延續。
《白狗秋千架》是一部寫得美、寫得實、寫得巧的作品。它美,美在字里行間那緩慢流淌而出的娓娓敘述,既有“涼爽溫和的東南風讓人極舒服,讓高粱梢頭輕輕搖擺”的清新淡雅又不失“又想還是‘狗道’些”的活潑風趣,它將高密東北鄉描畫得愜意又安詳,將鄉村環境涂抹得素美而不濃艷;它實,實在小說人物形象的外在刻畫與細膩的內心雕琢,力求還原人物本來的真面目;它并不避諱某些俗詞俗語的使用,“汗衫很快就濕了,緊貼在肥大下垂的乳房上”,“沒結婚是金奶子,結了婚是銀奶子,生了孩子是狗奶子”,這些詞句恰到好處的出現反而更顯作品的真實;它巧,巧在懸念隱現的小說情節,它雖并非一波三折,起伏跌宕,但“狗眼中的暗示”神秘而令人遐想。讀罷后,會感到一股股莫名的情愫涌上心頭。這種情愫縈繞于心,說不清,又道不明,卻予人震撼之感,深沉之思。這便是《白狗秋千架》自身獨有的感染力。
一、感染力的生發:狗之眼,狗之情
探尋這股感染力的生發之源,讀者會遇見一只“全身皆白、只黑了兩只前爪”的白狗。白狗雖不能被稱為真正意義上的視點,它卻成為比“我”更為稱職的見證者。作為“我”和暖之外的第三者,白狗親歷了“我們”所共同發生的重要事件,如那段解放軍進村,與蔡隊長同住的日子,如那場因秋千架斷裂而使暖致殘的嚴重事故,還如重逢后“我”的那次探訪暖家的經歷。在這里,白狗已不是聞聲便吠,遇人就咬的癩皮狗,也不是僅會看家守門、供人使喚的奴隸狗,更不是寢食無憂,與人玩耍的寵物狗。“狗眼里的神色遙遠荒涼,含有一種模糊的暗示,這遙遠荒涼的暗示喚起內心深處一種迷蒙的感受”,它不再作為普通的動物存在于小說中,而是幻化成一個會觀察,會思考,有著人類情感特征的“新生命”。這個“新生命”,在“我”剛回到故土的時候“冷冷地瞅了我一眼”,有點惱怒于“我”至今才回來,然后又“激動不安地向來路跑來跑去”,無比興奮于“我”終究還是回來了;這個“新生命”,在“我”拜訪暖家的時候,“最先應了我的喊叫”,“安安穩穩地趴在眼下鋪了干草的狗窩里,瞇縫著狗眼,象征性地叫著”,仿佛是一個常常見面的老朋友打著不冷不熱的招呼,因為它知道“我”一定會來;這個“新生命”,在“我”從暖家出來的時候,“站起來,向高粱地里走,一邊走,一邊頻頻回頭鳴叫,好像是召喚我”,就像暖的一個知心密友。
這個富有情感,明白事理的白狗,促成了“我”和暖多年以后的再次重逢。它存在于兩位主人公童年的回憶里;又存在于兩人多年后的重逢中,以“媒人”的身份點燃了兩位主人公舊年情愫:“我”剛到縣城時便遇見了它,它把暖領到了“我”面前;在“我”即將離開暖家時,它引著“我”來到暖的身邊。可以大膽地說,沒有白狗,便無所謂故事的發展和結局,它是小說情節發展的獨一線索,貫穿作品始終。在這里,“白狗”儼然成為作者創作的萌發點,成為該作品感染力的最初生發之地。
二、感染力的支柱:魂之泣,魂之訴
暖,是小說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她的悲慘命運致使我歸鄉前情緒起伏,是“我”難以打開的心結。在莫言筆下,這個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其命運的悲劇構成,是《白狗秋千架》中充滿無窮感染力的重要支柱。
魯迅曾說,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的確,在暖這個人物的身上,讀者看到了命運之神的冷酷無情,不禁憐憫于,嗓音甜美、極有唱歌天賦的暖,因為家里窮,沒有機會接受專業的訓練,未能被挑到部隊里去的無可奈何;不禁遺憾于,五官健全、相貌較好的暖,在一次與“我”相關的秋千斷裂的事故中失去了一只眼睛,成為殘疾人的不幸經歷;不禁痛心于,“十幾年前,她婷婷如一枝花,雙目皎皎如星”,令蔡隊長喜歡,使我心動的暖,如今卻成為“要不是垂著頭發,我是不大可能看出她是個女人的”,是一個乳房肥大下垂,擁有三個孩子,成日為養家糊口而過活的貧賤婦女;深切悲痛于,暖下嫁給“親能把你親死,揍能把你揍死”的啞巴,生出的三個兒子全長著一雙 “土黃色小眼珠”,“臉顯得很老相,額上都有抬頭紋,下顎骨闊大結實”的小啞巴的悲慘遭遇;十足震撼于,暖不畏世俗眼光,放下女性的自尊乞求與“我”野合,期盼能生一個會說話的孩子的荒誕請求。
“這就是命,人的命,天管定,胡思亂想不中用”,生在黃土地上是命,瞎了一只眼睛是命,嫁給啞巴是命,生出三個小啞巴是命,這是暖的思想,可以看出,她是被殘酷現實壓迫的受害者,更是感慨命運不公的哭訴者。然而,在遼闊的黃土地上,僅有暖這樣的一個悲劇發生么?誠然不是。在這悲劇的背后仍有無數個悲劇正在上演。讀到小說的結局,讀者不會再關注“我”是否真的同意了暖的請求,并與其野合,不再期待有關于“我”與暖野合過程的性的描寫,不再追究莫言為何要以設置懸念的方式來處理小說的結尾。強烈的命運悲劇感已震撼了心靈,無窮思緒在腦海中縈繞,仿佛聽見了無數的鄉魂如怨如泣的哭訴著它們的苦,它們的痛,流淌著血色的眼淚。
三、感染力的延續:鄉之戀,鄉之怨
“高密東北鄉”是莫言一貫創作的基地,其大部分作品都與“高密東北鄉”密不可分。如果說,在小說中“穿走牽引”的白狗,是作品感染力的生發之源,那么,作品四處彌漫著的,“我”之于故鄉那刻骨銘心的眷戀之情,便是支撐其感染力越生越烈的持續之力。
“我在農村滾了近二十年,自然曉得這高粱葉子是牛馬的上等飼料,也知道褪掉曬米時高粱的老葉子,不大影響高粱的產量”,這種情,浮現在“我”望見故鄉“高粱葉子”等熟悉事物時,所自然而然生出的段段清晰記憶里;“輕松,滿足,是構成幸福的要素,對此,在逝去的歲月里,我是有體會的”,這種情,融入進了“我”對暖如今生活現狀而產生的無限感慨中。
社會總在不斷地變化發展中演進,新事物必將取代舊事物而出現。于是,城市里開始崇尚時髦之風,但“故鄉的人,卻對我的牛仔褲投過鄙夷的目光”,“于是解釋:處理貨,三塊六毛錢一條……,既然便宜,村里的人們也就原諒了我”。當我看見啞巴對與“我”的牛仔褲表現得憤怒的模樣;當“我”感覺到和暖的對話無形之中變得艱難。這時,已成為大學教授的“我”,忽然深切感受到自己與曾親切熟悉的黃土地上人與物間愈行愈遠的距離。無獨有偶,魯迅的《故鄉》與此有相似之處,在離鄉后,魯迅和“我”同樣作為一個接受過正規教育,有文化的知識分子回到故鄉,那時對于故鄉的生活、故鄉的人民是如此的熱愛和眷戀。然而,當魯迅遇到麻木的閏土,當“我”因牛仔褲的事情被村民們另眼相待,終于發現了那道堅厚不可穿透的隔膜。至此,鄉村與城市,傳統化與現代化之間產生了矛盾,這種矛盾所產生的緊張感,在作品中若隱若現。一種“怨”意漸而產生,之于故鄉的“戀”情促使著“我”回歸故里,這種對故鄉的“怨”意卻是“我”猶豫是否返鄉一探的重要阻礙。
于“我”而言,當從城中返回鄉下,感受著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碰撞,這期間趨于現代化的精神思想與之于傳統化故鄉難以割舍之情的關系,是難以處理的;在自身精神的“離鄉”與“回鄉”的分岔路間,作者左右徘徊,接受焦灼地現實考驗和自省,卻是無法果斷抉擇的。兩種不可調和的矛盾在內心與精神世界里糾纏,這種糾纏通過“我”與暖荒誕的結局顯現,作品的感染力由此得以延續,震撼人心。
(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