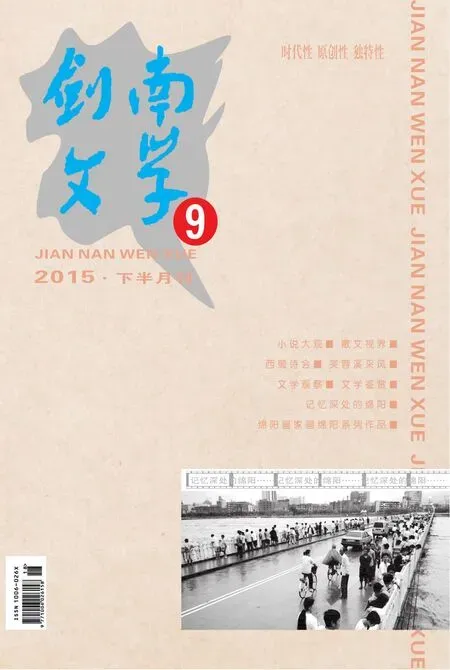看到的都成為了風景(外六首)
■靈 鷲
入眼的石頭都被體內的藥水泡過
而無法正常熱脹冷縮
所有語言的偏癱和神經的麻木都被風沙養育
而無法完成燦爛的晝夜交替
古絲綢之路上寧靜的舌苔
好像要變味了
最普通的石頭和最沒有規律的沙子
都自覺地成為身體的戈壁
干枯挺拔如白楊
這涼沁的孔雀河
要等一個季節才能看天鵝起舞
跳西北痛苦的芭蕾
十一點的夜路是城市邊緣的黑幕
比風還不會調情
去助人縮小對西北荒涼的偏見
而司空見慣的星星呢
放在戈壁的上空
它們都不會跳下來撒泡尿
澆灌口渴的紅柳
夜晚
肋骨擠出的野花
叫人無處安放
庫爾勒的柵欄
讓我吹不到海邊的臺風
喝不到盆地狂妄的雨水
所有的動蕩不安都要在車輪上輾轉
而天空再也舉不起來
遠方已經落下的帷幕
走出他的絕緣地帶
如若沉默
就如禿鷲爆炸
于密密匝匝的日光下
如若修造“宮殿”
便要扎進盆地
便要走回一個斜坡
走進暗沉
走出天堂一樣的呼吸
走出產卵的高原
走出囂張的山口和張開嘴卻說不了話的峽谷
如若干渴
便要趴在拉薩的河灘上拆線放水
看背水姑娘濕漉漉地現身
如若委屈
便坐在山的禿腦袋上發呆
給沉默止癢
把求來的風光摳掉一塊
若想了無痕跡
便要走出他的絕緣地帶
走出酥油經幡嘛尼石刻的悄悄話
藏地迷人而我難以脫胎換骨
成不了仙卻走火入魔
藏地日月同輝冷熱交替
生和死在凍土層里碎了一地
藏地從不缺乏歌詠者
而我狹窄的聲帶擠不出高原的顫音
藏地白日敞亮夜晚迷惑
讓爬升和下降都氣喘吁吁
閑時無需有條不紊——小魚的生活
在旁人看來她已經混亂了 離經叛道了
她在我不經意的時候學會了抽煙喝酒 足不出戶不拘小節語無倫次
而她渾然不知
而只有當她面對自己的時候才有空有條不紊滔滔不絕
她沒有心思說客套話奉承話打理枯草一樣的長發
走路也不像常人那么認真
甚至她對吃飯睡覺 旅游 觀光也不感興趣
所以我沒有把她趕到沙漠 湖泊里去
我怕只要我不看著她 她極有可能跟著駝隊走丟
或者掉進湖里
她說她只是來看我臉上有沒有荒涼的樣子
開始我還半信半疑
當她從綿陽到庫爾勒坐了近50個小時的硬座后
我才認為她的決定有點認真
我想離奇和偏執都應該覆蓋一層保護膜
在她身上不急于看到芒種和秋收
福地廣場
從26樓望去
溫暖如橘色的路燈照耀著奔命的城際卡車和無法睡覺的司機
白日小攤小販包圍了這座3.5環的商品房
現在在小區的中庭回蕩著繁忙的余音
我的哥哥
某醫院的一名醫生
在工作之余騎著三輪車戴著安全帽販賣淘寶山地自行車
越過大街小巷 穿過斑馬線和天橋
我的哥哥
也在為他即將到來的孩子奔命
他越來越像一家之長那樣寬大厚實
去蔭蔽妻兒老小
從26樓望去
溫暖如橘色的路燈折射出深秋的寒意
這霧和霾混合排練的迷障恰好演繹著城市的似真似幻
我蜷縮進水泥墻
仿佛窗簾遮蓋了噪音
聽西蒙·波娃誦經
你鑄造女性意識的塔尖
卻沒有背上女人的軀殼
一切就在宣戰中
搭建自己的圣經
可怕的女人
一定要說身體的真相
向著天空請求云朵
我應該親睞于我選擇的天空
請求降生云朵
控制住時間的輕度撩撥
脫離集體主義的囁嚅
一門心思向著遠方
在陌生的城池里變幻出各種瓷器的雜音
永恒而調皮的旅人
不知收斂敗壞的習氣
慢慢退至臥室
這床幽靈要睡
乞丐不能睡
盜賊不能睡
缺鈣的女人不能睡
僅一處庭院
獨身寓所
你偶爾發情
又突然按下停止鍵
樓上的嘎吱聲回聲蕩漾
大腦從此受到打擊
不再是第一個睡覺的夜晚和第一個被吵醒的人
各種詞語相互撞擊
泛濫于此
第二天
你說
肚子發脹
懷里揣著一個多余的詞
原來
滿紙荒唐言
都是個人意義的廢話
你還想把私人漢語用船載到外省
或者用飛機運走
去南極北極或者非洲
到達毛發厚重的男人和皮膚白皙的女人的枕頭
跟他們一起回憶貝多芬伍爾夫
西蒙·波娃 西爾維婭·普拉斯
馬爾克斯 切·格瓦拉
現在都沒有確定要成為他們中的哪一個
又是半夜
你跛腳起來喝茶
喝多了像個水腫的棺材
在房間搖搖晃晃
邊走邊流水
你永遠都站不直
不聽媽媽最初的指示
不管怎么長
都是一棵歪脖子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