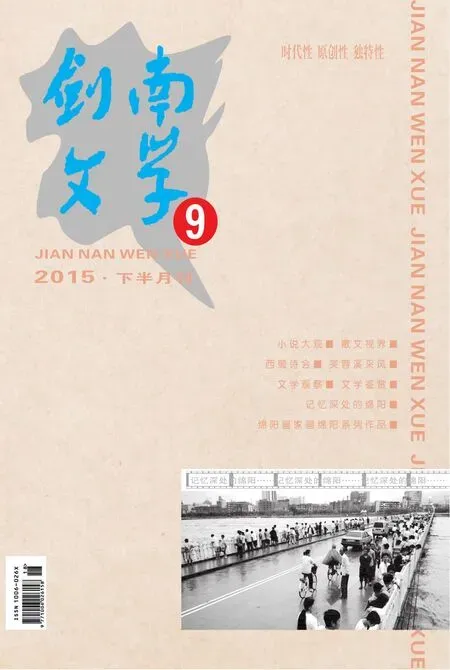評述巴斯內特之翻譯中的文化轉向
■沈克琳
本文首先介紹了蘇姍·巴斯內特認為翻譯研究已經轉向文化研究,現在是文化研究向翻譯轉向的時候了以及她對文化轉向和翻譯轉向歷史的論述,接著是筆者對她整篇文章的評述,認為此篇文章對翻譯研究很有幫助。
一、引言
蘇姍·巴斯內特和安德烈·勒菲弗爾合著的《文化構建-文學翻譯論集》是“國外翻譯研究叢書”之一。這本書共包含了8 篇論文,有講翻譯研究的發展歷史的,有總結翻譯理論研究的最新發展動態的,兩位學者甚至指出這一學科在下一世紀的發展方向,他們已經形成西方翻譯理論領域的文化學派。文化中的翻譯轉向是本書的最后一章,巴斯內特把文化研究和翻譯研究結合起來,追溯過去三十年來兩者平行發展的歷史,她認為兩學科跳出各自軌道聯合發展的時候已經來臨,翻譯研究已經轉向文化研究,現在是文化研究向翻譯轉向的時候了。這種論點比較前沿,也算一個宣言書。本文就按以下兩部分來評述這篇文章。
二、蘇姍·巴斯內特的主要論點介紹
在1990 年,蘇姍·巴斯內特和安德烈·勒菲弗爾曾合寫一本《翻譯、歷史和文化》,那時就注意到翻譯研究已經從形式主義階段轉向更廣的領域:語境、歷史和傳統。這被稱為翻譯的文化轉向。翻譯過程就牽涉到哪些文本應該被選來翻譯,譯者在選擇中的作用,出版商、編輯和贊助人又起著什么樣的作用,譯者采取某種策略的標準是什么等問題。有許多文本以及文本外的因素限制著譯者,這些限制因素成了翻譯研究中的主要關注點,處理這些限制因素過程中,翻譯的觸角就伸向更深更廣的領域了。這是首次倡導翻譯研究必須進行“文化轉向”。
蘇姍·巴斯內特認為,理論和實踐相互交織,理論不應存在于抽象之中,它應該是動態的,涉及對翻譯實踐的具體特征的研究,兩者是互相提供養分的,因此,翻譯研究不能定位于嚴格意義上的文化研究或者語言學研究,翻譯研究其實早已與飛速發展的跨學科領域—文化研究有著共同的基礎。
伊文·佐哈爾發展了“多元系統理論”的理論派別,包括了文學的、半文學的及文學以外的各種結構。他將文學研究的多元系統理論運用于翻譯研究,指出必須就(1)譯作與目的系統的相互聯系。(2)為何可以在一定時期選擇某些文本供翻譯而忽略另一些,以及(3)這些翻譯是如何采取特別的標準和行為等因素進行發問,從而為研究翻譯提供了新思路。
20 世紀80 年代末,許多翻譯研究活動發生在歐美之外,盡管多元系統論有助于我們以新的視角思考文化史等問題,但它畢竟是歐洲的產物,如拉丁美洲就把涉及原語與目的語關系的關注擴展到對被殖民和殖民者之間的關系的探討。約翰遜在論及巴西的食人主義運動時,談到作為文化身份的一種表述的隱喻—食人主義:
就隱喻意義而言,它表示對具有霸權的文化關系的一種新的姿態。傳統的字面意義上的模仿和影響已不復可能,食人者并不需要照抄歐洲文化,而是要吞噬它,利用其正面,拒斥其反面,創立一種具有原創性的民族文化,使其成為藝術表現的源泉,而非一個他處闡述的文化表現形式的貯存器。
在多元文化研究的潮流中,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文化霸權”及福科的話語理論催生了一種影響日廣的文化批判流派—后殖民主義理論。作為一種融合了多種文化政治理論和批判方法的集合性話語,后殖民主義理論旨在考察殖民時期之“后”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文化話語權力關系,以及有關種族主義,文化帝國主義等新課題,探討“后”殖民時期東西方之間由對抗到對話的可行性。這一理論影響最大的要數薩義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西蒙也關注文化多元主義,并以女性主義視角強調翻譯主體,努力消除翻譯研究中的性別歧視,“使女性在語言中顯現”。
接著巴斯內特講了文化研究的進化。經過霍加特、威廉斯和湯普森等的努力,文化研究漸漸地走出了純文學領地,把目光投向尚處于非經典地位的、邊緣的文學現象。在早期文化研究階段,文化研究努力在學術領域獨樹一幟,主要注重于重新評估口語文化和工人階級文化,重申文化是大眾文化而非單純的精英文化。文化研究打破了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天然壁壘,其跨文化性和跨學科性為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對話鋪平了道路。
安東尼認為從文學研究轉向文化研究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他把文化研究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發生于20 世紀60 年代的文化階段,為精英文化階段。第二個階段是發生于20 世紀70 年代的結構主義階段,轉向了文本和權力的關系。第三個階段是發生于最近20 年的后結構或文化物質主義階段,反映了文化多元主義。他的這個三分模式也使用于最近20 年的翻譯研究。當翻譯研究處于多元系統理論時,文化研究已經更深地探究性別理論和青年文學研究了。并且在80 年代,開始轉移英語為中心,廣泛地擴展到世界其他地區了,主要在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
文化研究在新的國際化過程中轉向了社會學、人種論和歷史領域。同樣的,翻譯研究也轉向這些領域去深化分析翻譯過程中文本是怎樣發生變化的方法。在轉向的方法上,文化研究摒棄了作為傳統文學反抗力量的福音階段,更密切地關注文本產生過程中的權力關系。翻譯研究經歷了相似的轉向,從無休止的關于“對等”的討論轉向了文本產生過程中涉及的因素。
語言學也經歷了自己的文化轉向,并且在語言學更廣領域里所做的工作對翻譯研究有很大的價值:在詞匯學、數據庫和框架理論分析方面的研究展現了語境的重要性,需要更廣的文化視角來對其審視。
翻譯研究和文化研究都特別關注權力關系和文本產生。不涉及權力關系的文本越來越難以接受,翻譯也總是陷入存在于原語和目的語文化的權力關系中。
三、對蘇姍·巴斯內特論點的評述
這篇文章首先從翻譯作為一個學科的地位低下說起,第一次轉向是勒芬研討會,這次研討會上伊文·佐哈爾的主要貢獻就是多元系統理論的提出,并把它應用于翻譯領域,給翻譯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然而多元系統理論畢竟是歐洲的產物,它注重研究目的語文化系統對于翻譯的影響和控制作用,而對處于強勢地位的文化或處于霸權地位的原語文化系統在翻譯活動中發揮的政治方面的控制和影響作用,卻很少涉及。接著提到約翰遜在論及巴西的食人主義運動時談到的作為文化身份的一種表述的隱喻—食人主義。文章然后論述了文化研究和翻譯研究平行發展的歷史,指出他們都已經開始跳出自己學科轉向更廣的領域,并且兩學科開始聯合發展,又比較了他們轉向的相似之處,及兩者共同關注權力關系和文本生產過程。翻譯研究和文化研究轉向的時代已經到來,一時都不再局限于狹隘的和歐洲中心區域,都轉向于合作,需要更多的交流和研究團隊。翻譯研究,和文化研究一樣,都需要不同的聲音,涉及不同的領域。不可否認,翻譯研究以其跨學科性和跨文化性,從眾多學科中吸取營養為其所用,已經發展為一門蔚為壯觀的自主學科。翻譯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已不同程度的受惠于其他學科,如哲學、文學、語言學等,翻譯學的“文化轉向”得到了翻譯學者的認可和積極參與,發展的如火如荼,自從蘇姍.巴斯內特和安德烈.勒菲弗爾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譯轉向”,正在被許多學科投入越來越多的關注。整篇文章邏輯清晰,內容廣泛,對我國翻譯研究有很大價值,非常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