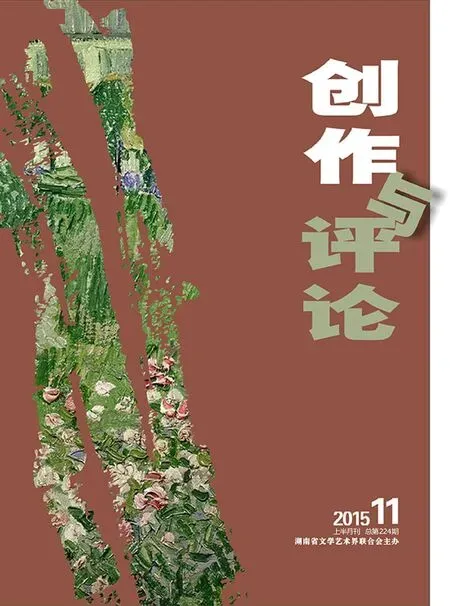權力結構與女性世界的隱秘
——池上小說論
○夏烈
權力結構與女性世界的隱秘
——池上小說論
○夏烈
小說維持著我們的精神、想象與生活的關系,這話對,但興許不夠精準。小說就是一種生活。
一方面,小說這個源自西方近代的概念在申明它與現代人及其日常生活的同一性。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一文里區分了“小說”和“故事”,認為二者都是偉大的敘事傳統,不過故事衰落而小說興起。小說是離棄上帝而困頓俗世之后的現代人懷疑、自省、理性、瑣碎的精神境界的分泌。
也因此,另一方面看,小說是非常現代的人性藝術,它不光關照生活的表面——類似新聞的事件和情節,更敏感甚至神經質地沉浸到人物在生活里的細節——內部及其褶皺,貼切而完美地抓取俗世中一代人、一群人、一個人的隱秘。沒有錯,“隱秘”,就是小說家的樂事,是他們在人間擁有和行使著的藝術與技術——唯有這種技藝,讓生活不再是時間和記憶的殘碎存在,反之成為時間和記憶的主體,忠誠地或者忠言逆耳地提醒你人性的優美跟斑斑劣跡。
池上的小說就是這樣一種藝術與技術,她顯然捉摸到了小說的本質的光環,并且樸素而顯出幾分拙意地在養成自己關于小說/生活的理解。
《桃花渡》(2014)、《在長樂鎮》(2014)、《春風里》(2015)、《這半生》(2015)以及更早些的《胎記》(2010),是我對池上中短篇小說的有限閱讀。它們是現實主義的,甚至很少夸張和變形。
池上早期(2008年之前)的小說訓練卻不是這樣的。“我當時模仿殘雪那種文字,華麗又冷酷,還用它營造出一種情緒、一種氛圍,比如2007年的小說《夜》”,“一開始是很奇麗的,我覺得是抓住奇麗的,很炫,炫技嘛。想要每一個字都讓你覺得好厲害、好驚世駭俗。每個字都用力過猛。比如說《犄角》”。殘雪式的先鋒小說、語言乃至結構的“奇麗”、技巧的變化,依舊是“85后”的池上學習和進入文學(文壇)的基本途徑。這些訓練自然有其必要,但揚棄更為重要。“2008年開始,我的小說中斷了幾年。停寫的那幾年,我沒那么絕望了,心境變化,寫的東西也就變化。2010年夏天我從寧波回杭,在火車上,我突然決定要重新開始寫小說,而且不再想寫先鋒的,更想寫點現實主義的東西。我的語言變得不那么陰冷,也不追求華麗了。我現在追求的語言是一種妥帖的感覺。”(池上、李璐,《訪談池上:我追求一種妥帖的語言》)此后,無論小說還是創作談,我感覺池上都回歸到極其樸實的基調,這讓我懷疑并大抵確信,她早期的小說學習階段的“奇麗”“炫技”,多半出自文藝青年的“通病”和走上“純文學”之途時的共振。跟純粹的形式相比,準確理解人物和他們在環境中的存在感受,學習在旁觀(俯瞰)中進入人物的心靈世界并體驗(憫愛)其掙扎和卑微的喜樂更為重要;最好的形式是人物自己的生命形式。
在池上小說的閱讀中,逐漸習慣了她用女性的視角看待生活和男性。換言之,池上提供的是她目前的小說習慣,寫女性且用女性寫。女性的心靈和眼睛成為池上小說觀察生命環境的窗口,男性居于篇幅的次要位置——不過池上在某個意義上又強化了男性的象征意味,即一種現實生活的邏輯中、一種池上的兩性觀中的“男性統治”。
性和社會角色,無處不在的統治權力是池上小說貌似溫婉散淡的敘述腔調里深深含有的基本結構。仿佛城市的水管電力互聯網,我們時常忘記它們的不可或缺,然而一切都市生活規則以及夢幻泡影都架構在它們之上。
《春風里》是一個典型,也是我閱讀之后印象深刻的一篇。林安娜從鄉入城、人近中年,因為漂亮,運命將她推上了脫穎而出的位置,其實是將她推到了男權統治結構的風口浪尖。她的戀愛、婚姻、外遇、事故分別歸屬于身邊不同的男人,一環又一環,沒有盡頭,她完全鑲嵌在了性權力和社會權力的男性中心背景之中,溢出自己這樣的一個女性、一群女性、一代女性被時代現實和社會文化劫持的疲憊的軌跡、掙扎的軌跡、貌似成功而實則凄惶的軌跡。
女性在強悍的男權中心結構中,除了被動的接受、順從自己的角色,做弱勢的自怨自艾和隱忍的自我說服外,學習和模仿男性的生活方式、社會角色就成了另一種選擇,即一種異化了的女性。《桃花渡》是池上提供的這一意味的堅硬苦澀的文本。越劇名家阮依琴在緊張的單位關系和事業更上層樓的轉折點上發現甲狀腺上有個邊界模糊的結節,醫院要求她盡快做切除手術。在小說的開端,池上頗有效率地把死亡搬出來做臨界感的推進,逼迫人物面對生死有新的領悟。而阮依琴“對著那些梧桐落葉說,我不能手術的”,第二段,池上便迅速地揭曉了一層謎底:“阮依琴是怕死的,可阮依琴更怕自己不能唱戲”;十余個段落之后,她的丈夫馬凱揭曉了謎底之下的謎底:“馬凱把那張協議書扔了出去,阮依琴,這么多年,你什么時候在乎過這個婚姻?也對,它只有妨礙到你唱那些狗屁戲,當狗屁團長了,才是重要的。”——離越劇團團長一步之遙的職位迷戀,取代熱愛唱戲的理由成為他人眼中阮依琴的主要性格特征和價值取向,之后的小說中這一點越來越突出,一番身體的無可奈何與社會關系的炎涼常態之后,當讀者同情于阮依琴過往的生活故事以為她終得心志獲得解脫時,權力卻再一次降臨,她則依舊選擇了權力。對于藝術(唱戲)和職位(團長)的雙重追求,尤其是后者,成為他人(即便是丈夫)也不能理解她的原因。阮依琴這個人物,包括她周邊工作環境中的成功者團長柳玥、另一名競爭者副團長黃云伶,共同指向女人入世的硬冷卑寒和男性立法的社會規則本身的弱肉強食。
女性被侮辱與損害還可以有哪些形式,這形成了池上冷靜的社會學式的注意力和思想力。《這半生》就是這樣一個持續推進上述觀察與思考的文本。小說開端再次成為一把鑰匙,正如薩義德花費整整一部大書闡述和研究的,開端決定了此后書寫的意圖與方法(《開端:意圖與方法》,愛德華·W·薩義德),池上在此說:“云惠年輕時受過一次傷。”當我們讀完整個“半生”的故事回頭概括,這小說的鎖心就是開頭第一句,這就是一篇較長的女性“傷痕文學”。如果說張愛玲式的“半生緣”與這里的“半生”還有些文字上直觀的聯想以至于比對的可能,那么池上真正的借鑒卻是《金鎖記》的曹七巧,三代人的互為隔膜和互為限制、互為傷害成了小說最觸目的部分,到善良軟弱的云惠最后轉變為兒子阿寶幸福生活的破壞者時,這觸目也就驚心了。不過,池上專門談到過張愛玲及其《金鎖記》:“張愛玲我覺得骨子里就特別特別的陰冷,她的陰冷是讓人覺得有點難受的。當然我看張愛玲不全,我只看了她的《金鎖記》,其他的我就不太愿意看了,我感覺太陰冷了。”——結果是,《這半生》有意無意地將云惠推到了刻薄母親的境地,使之有了《金鎖記》的一點兒陰冷之影;而興許是池上心中又排斥(恐懼)這樣的陰冷,使得《這半生》究竟無法達到《金鎖記》的獨特和卓爾。
云惠在小說開頭的傷痕,池上“捂”得真真是極好的,一直到小說結尾最后一段才揭開何以在洛陽讀大學時的那段少女情懷釀成了內傷,一輩子無法恢復。我們在謎底之前優先領略的是云惠無法結痂的帶著傷口的兩性生活中,一次次經受的來自男人的故意和非故意的戕害,總之,畢竟是沒有出現能夠治愈她的人,連幫助的心也沒有——現實的婚姻之路實際到無可救藥,誰都不會同情一個心病沉疴的弱女子。
各種男性的隨心所欲和女性的彷徨無依在其他的《在長樂鎮》《胎記》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現,即便這兩篇的女性更多一些自己對生活的選擇、對情欲的渴求,但回饋的反作用力仍然令女性更有壓力、更難消化。所以說,池上是女性更是女性之友,她的動心忍性處都是男權社會下的女性心智與行為,她的小說因此有很好的女性形象塑造出來,像林安娜(《春風里》)、唐小糖(《在長樂鎮》),我以為都是寫得很飽滿、很有生趣的人物——更重要的是,這些小說中的女性素材和心理軌跡非常“接地氣”,如果說這顯示了池上“有生活”,我看毋寧說是池上有注意力(觀察和思考),她讓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及其遭際、發展有了合乎社會學、心理學的依據,是比較扎實的寫法,頗有歐洲19世紀寫實主義小說的風范。
池上小說的男性因此難免有些套式和扁平化。首先是套式問題,池上理解的男性大致有兩種,一種是“溫和陪伴型”,另一種是“花街浪子型”。《桃花渡》里阮依琴生活里的兩個男人都基本屬于前者:丈夫、文化館編縣志的馬凱,越劇團的編舞、追求者潘志文;《在長樂鎮》里唐小糖生活中的兩個男人則分屬一前一后:丈夫、鎮醫院婦科醫生郭一鳴是溫和的,開改裝車修理行、未定性的青年情人阿凱則是同時與兩名女性發生性關系的浪子;《春風里》中林安娜生活里的四個男人復雜一些,一起進城闖蕩的男友沈世民是溫和陪伴型的但更自卑懦弱,早逝的丈夫浩揚是藝術家型的,前后兩任廠長夏宏平、胡國勇欲望纏身(權力與身體的征服者),但夏更男人味、胡更流氓氣;《這半生》中云惠生活里的三個男人兩個(洛陽老板杜江,丈夫、銀行職員沈兆南)是花街浪子,相親遇上的大學歷史系講師林國光是溫和陪伴的。——這些基本有二分的男性角色,拿現在流行的詞匯(當下時代的女性主義視角及其男性命名)來講,就是“暖男”和“渣男”的類型區別。
池上偶爾會盡力細寫一點男性,比如馬凱、潘志文、沈世民、胡國勇,不過總的看是欠缺的;有一個女主人公感情線索以外的男人,《春風里》的下崗工人老伍,卻有些意外的神采,真實、血性、有情有義,不過畢竟是配角,不能改變池上男性理解偏弱的大局。
男權中心下的男性除了強烈的社會性、動物性即權力欲望及其競爭,還有沒有內心的層次可以開辟出來,有沒有特異的、突變的、矛盾重重的心理和靈魂在面對女性和生活歷程后有豐富的變化,這應該值得池上給予注意。
此外,我關注到了池上這些小說中的“性”。性是一種原動力、一種本能,它的釋放與解放始終伴隨著權力斗爭,換言之,性是與權力有關的自然物,看著是我們自己的,但一旦進入兩性尤其是社會之后它就表現出強烈的權力競爭和交換關系。
池上小說中女性的“性”生活很有意思。有一類,是自由選擇,也就是她們身心自由律動的結果。當身體有渴望,心靈為了尋求打破無聊和既定秩序的時候,當代女性有其自由且無論年齡。
《在長樂鎮》里的唐小糖就是青年女性的性愛自由者,模特身坯子和傲嬌氣質的她在平靜無聊的家庭生活中選擇了與樓下經營改裝車鋪子的摩托男阿凱激情來往,修車鋪、錄像廳小包廂,阿凱有力的生機勃勃的青春力量刺激和滿足著年輕少婦唐小糖,“唐小糖擰開水龍頭,從水龍頭里流出白花花的水,漫過了那幾只疊起來的碗,又漫過了不銹鋼水槽。在似乎永無休止的嘩嘩聲中,唐小糖的眼前浮現出那張輪廓分明的臉,赤膊的阿凱像某只雄壯的動物壓在她的上頭。在一次次的交媾中,唐小糖聽到阿凱低沉而有力的吶喊:“我愛你,我愛你……”池上的筆觸生動有鏡頭感地描摹著唐小糖的性生活,呈現出一種美媚結合的快感和美感。
有一個細節確實甚是精彩,唐小糖的第一次偷歡是伴隨著她跟丈夫借口外出買魚達成的。
唐小糖是拎著一條小鯽魚趕回家的。鎮上的菜場收攤收得很早,往往還沒到中午,菜場就變得空蕩蕩了。唐小糖到菜場時,差不多就是那種情形。她看到頭一家賣魚的女人正在往外倒水,魚基本賣光了,只剩下一條手掌大的魚,在水里孤獨地游著。這種魚一看就是被挑剩的,但女人卻說,不要看這條魚小,筋骨是絕對好的,你看看,游得多起勁。魚好像聽懂女人的話似的,又搖擺著兜轉了一圈。唐小糖便把它買了下來,她琢磨著,有總比沒有的好。
還是這條魚,再次出場是在同樣被阿凱始亂終棄、打胎離開的阿麗與唐小糖的最后一番對話中:
阿麗說,唐小糖,我要走了,回自己的老家。你知道嗎?我在這個鎮上沒有親人,所以,當我的腦袋里跳出讓你來陪我做這個手術時,連我自己都覺得可笑。阿麗真的就笑出聲來,唐小糖卻怎么也笑不起來,不知怎的,她想起了家里的那條鯽魚,她從前覺得自己像那條魚,現在,她覺得阿麗也像那條魚。于是,唐小糖對阿麗說,你等我下。唐小糖跑回家,把那條魚裝在裝滿水的塑料袋里,對阿麗說,我沒有什么東西能給你了,這條魚就當作是分手禮吧。阿麗接過那條魚,看了很長很長的時間。阿凱他就是個混蛋,他配不上你的。阿麗最后如是說。
如果說開始小而有筋骨的鯽魚似乎寓意著“魚水之歡”達成后的性事隱秘的話,那么當兩個女性因相同的男人、相同的遭遇互相撫慰時,則可以理解為唐小糖突然覺得阿麗跟她一樣是那條小小的鯽魚:皆若空游無所依。
性事后空空如也。填充無聊感、無根感的性選擇、性自由解決了一時的身心需求,在將男性帶入神經的快感以外,也將女性帶入更多的幻想與感情生活,但最終卻無法解決“無所依”的根本問題,換言之,歸屬和信仰都無法由性快感取代,它們是不同層次的心理樓宇。
另一篇有趣而大膽的性描寫是《胎記》,這次的偷歡者換成了中晚年的賢妻良母盧心慈,介入這個年齡段描寫其最后的性愛訴求真是一次美妙的突破。小說本身懸念相扣,在題材的突破和性愛方式的描寫上可圈可點,不過失之于太過故事化了些。
這一類型的女性性愛表達依舊有很強的社會學、心理學基礎。寂寞、平淡、被丈夫忽略——身心的冒險與性愛美媚的激活——冒險的代價(生活的邏輯)——回歸或小結后的心智反應。性選擇和性自由的合理性,以及兩性問題、人性問題的終極矛盾都在此間浮游。
另一類型的女性性愛是被限制的,是用作權力交換的物化對象。無疑,這是社會生活真實和嚴酷的反映。林安娜的生存技能歸根結底是以性為物,與有權者交換生活資料和表面的風光,那么內在的苦楚會時刻涌泛上來,提醒著她人生的荒涼與茍且。“此刻,胡國勇終于曉得是什么了。是征服所帶來的快感,林安娜身上有一種力量,蠱惑著他去馴服。”是林安娜被男人權力馴化成一架誘惑機器,還是這根本就是男人對于性感的本能意淫?或者二者皆有?這種交易關系步步驚心,其實毫無安全感可言,胡國勇消費著林安娜,卻將她置諸工具的位置,用她的美貌來招待房地產商、招安反抗工人領袖、出賣她成了眾矢之的的騷貨……林安娜的悲苦是深深地陷落于性權力高度物質化深淵的悲苦,若不是她的一只手臂最后被老伍在憤怒中砍掉,她的輪回之苦反沒有盡頭。禍兮福兮,單臂的林安娜舞動在老伍妻子自殺的那口井邊時,路人驚嚇于那森森的鬼氣,而對林安娜來說,何嘗不是了悟悲苦后解脫的一支舞蹈。
同樣的性交易發生在阮依琴身上,年輕時受蛇果般誘惑隨柳玥走上都市繁華競爭路的她,渴望在《追魚》(又是魚)中獲得女主角的機會,結果上了投資商某影視公司趙老板的床,“如果不是長宏影視公司的趙老板,也許阮依琴的人生就這樣了”——在劇團中沉淪下寮;可借助性交換所得的一條路帶她到了何方呢?小說依舊壓抑著悲苦娓娓道破。
對于“性”的認識是池上關于社會關系、時代處境的全面認識的一部分,她找到了其中的關鍵性鏈接,她在某些方面的認識是非常充分的,是有良好準備的作家。
最后,值得一說的是池上這些小說中的城鄉問題。小說中的女性因為來自村鎮,向往都市,而集體呈現著無根、疏離的潛意識,一種情感況味,一種陌生的捍格。林安娜如此,阮依琴如此,唐小糖如此,她們是失去故鄉的人,她們是背鄉而行由欲望和命運交織掌控的人,她們的自由是有限的,甚至連死亡的自由都是如此。她們首先是渴望站穩腳跟,然后是渴望浪漫激情的愛情(阮依琴和唐小糖都有這樣的文字表達),最后是不得不為安全感投入戰斗、交易、競爭,收獲那些失敗的蒼涼和勝利的蒼涼。是什么讓池上敏感到這個層次的細節,我在她的《偏愛一種:〈在長樂鎮〉創作談》中找到了部分答案:
當我走進那所鎮上的中學時,籠罩我的絕非什么優越感,相反的,是一種疏離感,莫名而強烈。我想,我是不可能驕傲了,但我亦不能自卑。
……
果然,杭州于我,是陌生的。街道永遠擁擠,行人永遠面色冷漠,行色匆匆。我的新同學們很快將我歸類為農村來的人,他們無法理解,更確切地說,是沒有興趣去分辨“農場”和“農村”有何不同。我也懶得跟他們解釋。總之,在他們眼里,我理著個杭州姑娘所不屑的蘑菇頭,說杭州話時會夾雜點鄉音,沒有學過地道的英語,尚不知“興趣班”是何物。在之后的日子里,我試著努力適應,以圖融入這座城市。我想我是做到了,至少是裝著做到了,可待夜深人靜時,我再一看,它還在呢。它根本就成了我體內的一份子,哪里還能抹去?
作家幸而有一副上帝的眼睛,可以俯瞰自身、俯瞰生活的軌跡,那么,人的生活也就轉化為了小說的乳與油,讓小說代替生活繼續演繹形形色色的可能性。
池上是一名新手,不過已經找到了自己靠譜的技藝。她的小說踏實的部分讓我心安,我只是等待她的創造與推演。等待好小說同樣是一種好的生活。
(作者單位:杭州師范大學文創學院)
本欄目責任編輯張韻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