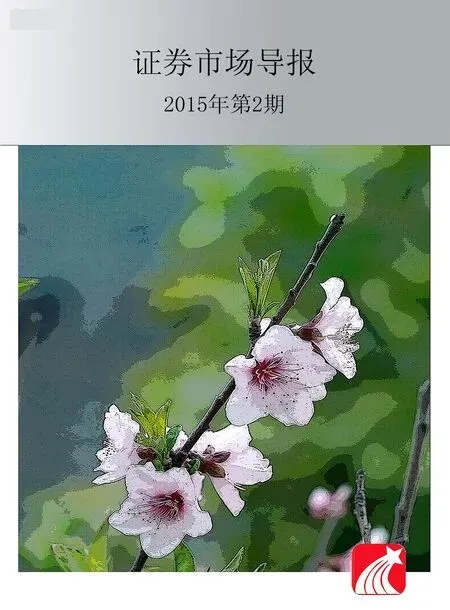高管薪酬激勵對企業價值創造的影響研究
黃志忠 朱琳 張文甲
(南京大學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3)
引言
最近幾年我國上市公司“天價薪酬”和“零薪酬”的問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人們懷疑上市公司CEO的天價薪酬是否合理。與之對應的是,不少公司的董事長或總經理年薪低到不超過2萬元,甚至一些上市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不在公司領取薪酬,這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總之,多少也讓投資者感覺不安:不領取薪酬或領取超低薪酬的管理者是否會為投資者的利益而努力?從投資者利益的角度,到底給管理者薪酬高好還是低好?是直接給予現金好,還是給予股權、期權好?
從現代財務理論和研究成果來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企業存在著經理人利益與股東利益不一致的代理問題,為了減輕二者的利益不一致所導致的經理人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需要對管理者安排激勵機制(Jensen和Meckling, 1976; Jensen和Murphy, 1990)[6][7]。許多學者認為,單純的現金激勵制度不利于經理人關注企業價值的創造(Smith和Watts, 1992)[10],企業經營管理的目標是企業價值最大化,或股東財富最大化,因而應該給管理者安排股權或期權激勵。但是,股權激勵也可能導致管理層操縱公司利潤,進而損害股東的利益。例如,美國安然公司給管理者安排了股權激勵,結果管理者為了自身利益長期操縱公司的利潤,極大地損害了投資者的利益。究竟哪種薪酬安排有利于公司價值創造仍無定論,有待深入研究。
目前已經有不少文獻研究了中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與公司業績的關系,發現上市公司的CEO薪酬與業績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正向相關關系(劉斌等,2003;張俊瑞等,2003;肖繼輝,2005)[14][20][18]。然而,這些研究還不足以說明薪酬激勵的效果,到底是公司的業績好了,發放給高管的薪酬就高了,還是因為薪酬激勵刺激高管更加努力從而使得公司的業績高于其他公司?因此,我們需要根據公司所創造出的價值比較不同薪酬制度的效果,即著力于公司未來剩余收益(即公司的超常收益)的現值來做比較。現有的大量文獻發現,薪酬激勵會導致高管為當前的利益而人為地提高公司業績等短期行為。未來的公司業績能夠更好地避免受這種短期行為的影響,因而更加客觀更加可靠,這是本文的創新點。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代理理論認為,經理人薪酬安排是為了減輕代理問題。如Traichal等(1999)[11]認為相關集團試圖最小化或控制管理者與股東之間代理沖突的方式可以歸結為三個基本類型:市場規制、薪酬結構和監管機制。第一種方式是通過各種市場對經理的行為加以規范,這類市場包括經理人勞務市場(Fama, 1980)[2]、產品市場(Hart,1983)[3]、公司控制權市場(Jensen和Ruback, 1983)[8]。第二種方式是將經理人的薪酬直接與公司的業績掛鉤。Traichal等(1999)[11]認為信息不對稱導致事無巨細的監管成本太高,而將經理人薪酬與公司業績聯系起來是將代理人的利益與委托人的利益聯系在一起的重要一環。陳效東和周嘉南(2014)[12]、夏蕓和唐清泉(2008)[17]發現,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顯著提高了R&D的支出水平。第三種方式包括對經理人業績的監控或者說由CEO對公司的業績加以擔保。我國的經理人勞務市場還不健全,難以起到規范經理人行為的作用。因此,第二種和第三種方式顯得尤為重要。然而,有經驗證據表明,如果人力資源管理致力于控制、注重效率、限制雇員的自由裁量權,那么高管離職率就會增加,組織績效會變差(Jacobs, 1991; Smith & Watts, 1992)[5][10]。當然,中國的情況怎樣,目前還沒有相關的經驗文獻。
拋開文化和政體的影響,從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目標來講,管理者薪酬激勵的安排應該與企業的目標相一致。根據Ohlson(1995)[9]的權益定價模型,企業的價值由未來超常收益的現值決定,即:

上式中,ABEt=Et-r·Bt-1,它被稱為超常收益(abnormal earnings),或剩余收益(residual income),或經濟附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EVA)。從(1)式中可以分離出三個增加企業價值的途徑:提高本期權益賬面值B0、提高未來各年的利潤Et和降低權益的資本成本r。其中第一個途徑——增加權益賬面值的方法無非兩種:增加留存收益和股東投入。前者由本期公司實現的利潤和向股東發放的紅利所決定,后者通過股票增發、配股來實現。顯然,不向股東發放紅利或少發放紅利、增發配股增加的價值來源于股東,而不是由管理層所創造。第二個途徑受到國內業界、學界和投資者的普遍關注。第三個途徑在早期很少受到關注,國內尤其如此。最近幾年,國資委在中央直屬企業開始實施EVA考核制度,同時關注利潤指標和資本成本,但指標體系過于僵化,在資本成本的確定方面未能考慮企業的總體風險水平。
目前,國內大部分上市公司采用的考核機制是目標責任制,并將管理者薪酬與目標責任制完成情況相掛鉤。目標考核的標準主要包括企業規模增長、銷售增長、利潤增長、總資產利潤率、凈資產利潤率、存貨周轉率和應收賬款周轉率等。現有研究指出,高管薪酬由公司規模、利潤率、所在行業、所在地區、公司治理等因素所決定(見張俊瑞等,2003;黃志忠和郗群,2009;張恩眾和張文彬,2007)[20][13][19],這與上市公司普遍實施目標責任制有關。除了行業、地區、公司治理等非財務因素外,目前影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主要財務指標幾乎都是短期指標。已經有大量文獻證實經理人為了薪酬而進行盈余管理(Healy, 1985; 蘇冬蔚和林大龐,2010;權小鋒等,2010)[4][16][15],這是由以短期業績為基礎的薪酬激勵所導致的(Jacobs, 1991)[5]。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與業績掛鉤,很可能導致操縱利潤等短期行為的發生,從而有害于公司的長期價值。而股權激勵可能會在計劃期和實施期招致高管為了獲得股權(期權)而進行的盈余管理(蘇冬蔚和林大龐,2010;權小鋒等,2010)[16][15],但在股權激勵實施后,高管的財富受公司股價的影響,從而激勵公司高管為了股價上漲創造價值。當然,也有研究指出,那些股權激勵水平高的公司,高管也會通過提高應計項目的方法進行盈余管理(Bergstresser和Philippon, 2006)[1]。本文以公司未來4年超常收益的現值作為管理層創造價值的衡量,一定程度上濾除了管理層短期行為的影響。在這個前提下,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H1:高管的薪酬與企業的未來創值水平正相關;
假設H2:與業績掛鉤的薪酬對企業未來創值的影響強于未安排激勵的薪酬對企業未來創值的影響;
假設H3:權益基礎的高管薪酬對企業未來創值的影響高于前兩種薪酬對企業未來創值的影響。
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說明
本文選擇2007年和2008年的在滬深股市交易的上市公司為初始樣本,并將2007~2012年一共6年的上市公司財務數據、市場數據、公司治理數據按照如下標準進行篩選:(1)由于金融保險行業的資本結構比較特殊,因此剔除金融保險行業的所有公司;(2)剔除沒有披露高管現金薪酬、持股數量等相關數據的公司;(3)計算公司未來創值水平要用到t+1至t+4共4年的財務數據,剔除相關數據缺失的公司;(4)本文要判斷公司是否安排了薪酬激勵,安排了怎樣的激勵機制,首先是通過上市公司披露的年報手工收集上市公司激勵制度的建設情況。許多公司不披露或不明確披露公司是否設置了薪酬激勵制度,一些公司雖然針對薪酬制度作了披露,但只簡單說明公司實施業績考核,是否根據考核給予管理層獎勵并未說明。為了辨別公司是否真正實施了薪酬激勵,我們計算了公司近6年的凈利潤與CEO薪酬的相關系數。若公司明確披露未實施薪酬激勵制度或者CEO薪酬與凈利潤的相關系數低于0.1時,我們都將之界定為未實施薪酬激勵制度。由于計算CEO薪酬與凈利潤相關系數的需要,我們將2008年及之后上市的公司排除在樣本之外。這樣,本文最終獲得了1279個樣本觀測值,其中2007年622個,2008年657個。財務和公司治理數據來自于CCER數據庫。
二、經驗模型
本文的研究與財務領域的高管薪酬激勵與公司價值關系的研究略有不同。財務領域研究薪酬激勵與公司價值的關系主要關注兩個問題:一是企業是否安排了與業績掛鉤的薪酬制度,即公司業績的變化是否帶動薪酬的變化,二是薪酬激勵是否發生了激勵作用,即安排業績基礎或股權基礎的薪酬制度是否帶來公司價值的提升。要達到這兩個目的,研究設計上主要是檢驗時間序列的相關性,這需要較長的時窗,比如說十五年以上。但實際上現有這方面的研究選取的時窗都很短,特別是國內相關的研究均存在不足。而本文則主要關注于不同企業間人力資本合約安排的差異以及這種差異是否導致企業未來價值創造水平在橫截面上分布的差異。
本文用公司未來四年的剩余收益現值作為企業未來創值水平的度量。Ohlson(1995)[9]由預期股利折現模型(PVED)推導出公司股權的價值由凈資產的賬面價值和未來剩余收益的現值構成。Ohlson將剩余收益稱之為超常收益(abnormal earnings),剩余收益的現值即是企業的商譽。超常收益的存在是因為企業獲得了高于公司資本成本的凈資產利潤率。顯然,企業的剩余收益越高,企業的價值越高,剩余收益增加了企業的價值。剩余收益現值為正時,管理層為企業創造了價值。
本文用以下線性模型來檢驗第二部分提出的三個假設:

式中,PVRI代表公司未來4年剩余收益的現值,MPay代表公司前三名高管現金薪酬的自然對數值,PRPay代表與公司業績掛鉤的前三名高管現金薪酬自然對數值,EBPay代表安排股權或期權激勵公司的高管總薪酬的自然對數值,Size代表公司資產規模,Lev代表負債比率,ROE為凈資產收益率,Margin為毛利率,SOE代表最終控制人為國有企業或政府部門的啞變量,BLOCK為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ID為獨立董事占董事會總人數的比例。
三、未來創值水平的估計和變量說明
本文用公司未來4年剩余收益的現值來估計未來創值水平。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Eiτ為公司i第τ年實現的凈利潤,Rj為公司i所在的j行業的凈資產收益率ROE的中值,BVi,τ-1為公司i第τ年初的凈資產額,Assetsit為公司i第t年的期末總資產額。本文用行業ROE的中位數作為樣本公司的資本成本,目的在于消除行業差異,而且所計算的剩余收益能夠真實地反映企業的競爭優勢,這與人力資本管理的目標相一致。另外,企業剩余收益的現值受企業規模的影響。為了消除規模的影響,我們將剩余收益現值通過除以期末總資產進行標準化。
其他變量如表1所述。

表1 相關變量說明
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在所有的1279個樣本公司年度中,只有270個公司年度實施了以業績為基礎的現金薪酬激勵制度,占21.1%;在實施現金薪酬激勵的公司里,前三名高管的薪酬平均值為162.65萬元,遠高于所有樣本的均值111.41萬元。實施股權或期權激勵的只有34個公司年度,僅占2.66%。這些實施了權益激勵的公司的前三名高管總薪酬均值為298.36萬元。這可能與我國上市公司股權多數比較集中有關。因為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比較高時,他們偏向于對管理層實施直接的監管。因篇幅限制,描述性統計表在此略去。
二、回歸結果
在模型中控制了企業未來價值增量的動量因素——毛利率Margin和ROE之后,表2的回歸結果顯示:(1)高管薪酬水平與企業未來創值顯著正相關,表明存在大股東的情況下高薪合約也能對高管起到激勵約束的作用,獲得高薪的高管會有動力去為股東財富最大化而努力,從而促進企業未來價值的提升。假設H1得到支持。(2)在2007年的回歸結果中,EBPay的系數雖為正但不顯著,在2008年的回歸結果中,PRPay的系數也不顯著,表明當股市處于高漲時期,權益基礎薪酬激勵的效果不明顯,當宏觀經濟處于低迷時,現金激勵的效果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在股市處于高漲時,高額的股權回報讓管理層獲得的巨額財富與他們對公司未來價值的創造不相稱;而當宏觀經濟處于低迷時,安排了現金激勵的高管報酬相對較低,但是薪酬激勵仍在發揮效用,使得有現金激勵的公司未來價值的增量超過未安排激勵而薪酬不受影響的公司,這個關系會影響高管的薪酬水平與公司未來創值之間的相關性水平。因此,當兩年合并回歸時,EBPay和PRPay的系數都變得顯著,表明橫截面的比較也需要多年度的數據混合起來做檢驗測試以提高實證效果。(3)當公司為高管安排了現金激勵機制時,PRPay與MPay相等,因此第四列PRPay的系數顯著大于零,表明安排現金激勵的公司未來創值水平對薪酬的敏感度(為0.029+0,002=0.031)顯著地高于未安排薪酬激勵的公司相應的敏感度(0.029)。假設H2得到支持。(4)同樣地,安排了權益激勵的公司高管總薪酬EBPay中的現金部分不僅已經在變量MPay中體現,也在PRPay體現。因此,EBPay的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安排權益激勵的公司未來創值水平對薪酬的敏感度(為0.029+0.002+0.004=0.035)顯著地高于未安排薪酬激勵的公司相應的敏感度(0.029)和僅安排現金激勵的公司相應的敏感度(0.031)。假設H3得到支持。

表2 回歸結果

表3 穩健性檢驗結果
綜合以上結果,實證結果表明,在薪酬管理實務中,安排權益激勵的合約優于安排現金激勵的合約,安排現金激勵的合約優于未安排激勵的合約,高薪的合約優于低薪的合約。
三、穩健性檢驗
薪酬激勵對企業未來價值的影響是否會因所有制性質而不同?高管的薪酬水平也可能會因行業而有差異,比如壟斷行業的薪酬受到管制,但企業的創值水平卻可能比較高,或者反之。另外,上市公司經常更換前三名高管,因為有時候董事長不領取薪酬,有時候又領取薪酬,這會造成混亂。還有,薪酬的增加是否有助于提高企業價值的絕對值,而不是上文表2中的相對值?考慮這些因素后,以上的結論還會成立嗎?為此,我們進行了如下的穩健性測試:用公司未來4年EVA現值的自然對數值作為因變量,用董事長或總經理的現金薪酬、現金激勵薪酬、現金薪酬加股權價值的1%再加期權價值之和作為自變量,控制行業和控股股東股權性質,代替模型(1)的變量,并進行回歸。結果見表3所示。
表3中,全樣本的結果與表2的結果一致,CEOPay、CEOPRPay和CEOEBPay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高薪酬、薪酬激勵和權益激勵都能給上市公司帶來未來價值的提升,假設H1、H2和H3得到支持。然而,當控股股東的所有制性質不同時,薪酬激勵的效果有所差異。對于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在未來創值方面,權益激勵優于現金薪酬激勵,現金薪酬激勵優于無激勵薪酬安排。但對于民營控股的上市公司,現金薪酬激勵對公司未來價值的提升作用要強于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但權益激勵的效果似乎不佳,沒有顯示出激勵的效果。
總結與建議
本文以2008年之前在滬深股市上市的非金融公司為樣本,對現金激勵和股權激勵的作用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1)高管的薪酬水平與企業未來創值顯著正相關,表明在我國普遍存在大股東的環境中,高薪合約也能對高管起到激勵約束的作用,獲得高薪的高管會有動力去為股東創造更多的財富,促進企業未來價值的提升;(2)關于未來創值水平對于薪酬的敏感性,安排現金激勵的公司顯著地高于未安排薪酬激勵的公司,即對高管的現金激勵幅度越大,公司未來的價值增加得越多;(3)關于未來創值水平對薪酬的敏感性,安排股權激勵的公司顯著地高于未安排薪酬激勵的公司和僅安排現金激勵的公司,表明股權激勵的效果要好于現金激勵和無激勵安排。我們還發現,由于股票市場的波動對權益激勵機制下高管的薪酬造成影響以及宏觀經濟波動對現金薪酬激勵制度下高管薪酬造成的影響,在個別年份,高管薪酬與公司未來價值增量的相關性會有所降低。因此,需要多年度的混合數據回歸才能有效降低某些外部因素對回歸結果的噪音性影響。
總體來講,研究結果表明,在薪酬管理實務中,安排股權激勵的合約優于安排現金激勵的合約,安排現金激勵的合約優于未安排激勵的合約,高薪的合約優于低薪的合約。但穩健性測試的結果表明,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權益激勵效果更好,這可能是因為民營控股的上市公司CEO所安排的股權激勵更可能是管理者的自我獎勵,而不是真正面向未來的激勵安排。
目前,一些上市公司的“天價薪酬”和零薪酬現象引起了公眾對上市公司高管是否存在自利行為或過度獎勵行為產生疑慮。本文的研究表明,對高管進行適當的激勵和獎勵是有積極作用的。由于國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受到國資委的監督和管制,薪酬激勵,尤其是股權激勵發揮了較好的激勵效果;反觀民營控股的上市公司,許多CEO是由公司控股股東或終極控制人擔任,他們的行為較少受到約束,從而存在過度自我獎勵的可能性,導致股權激勵的效果不明顯。因此,為了使上市公司為投資者創造更多的價值,建議政府部門廣泛推行股權激勵制度在國有企業中的運用,并予以適當的監管;對于民營上市公司,證券監管機構有必要出臺指導意見,規范股權激勵在這些公司中的運用,對于由控股股東或終極控制人擔任CEO的上市公司,尤其需要監管層對其所實施的股權激勵方案加以審查和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