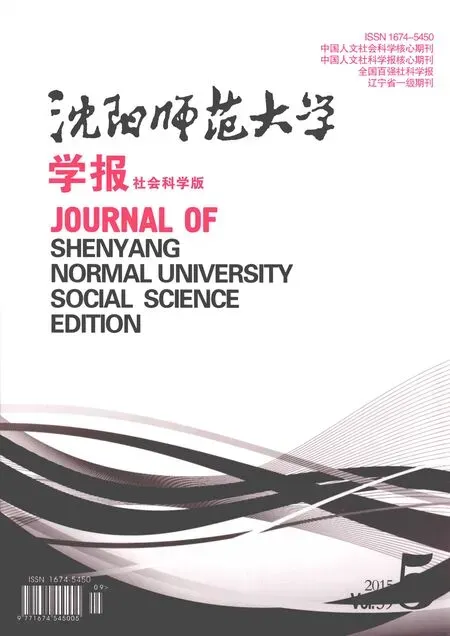上司排斥、組織支持感與員工角色外行為關系
——以綜合性B2C企業為例
何海英
(遼寧大學商學院,遼寧沈陽110036)
上司排斥、組織支持感與員工角色外行為關系
——以綜合性B2C企業為例
何海英
(遼寧大學商學院,遼寧沈陽110036)
以社會交換理論為理論基礎,采用問卷調查法,以綜合性B2C電子商務企業的375名員工為研究對象,使用SPSS20.0研究上司排斥、組織支持感與員工的兩種角色外行為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上司排斥對員工的兩種角色外行為具有負向預測作用,組織支持感在上司排斥與員工的兩種角色外行為中間起部分中介作用。
綜合性B2C;電子商務;上司排斥;組織支持感;幫助行為;進諫行為
良好的領導-部屬關系會對組織的有效運行和發展產生良好的促進作用,已經得到了大量的證實[1][2]。但是由于企業間的競爭壓力不斷加大,轉移給企業領導和員工的壓力也在逐漸增大,領導與員工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隨著壓力的增大也日益增多。但是由于中國企業中規章制度明確嚴格且明顯的報復性行為也為企業所不容,因此,這種矛盾和沖突就轉化為了更為隱蔽的排斥行為。同時,中國企業中權力距離大,下級對上級的排斥行為并不能造成上司的實質性損失,但是上司卻掌握了組織的大量資源,其對下級的排斥會導致下級損失大量的組織資源,并對下級的態度和行為造成巨大影響。因此,本文以上司排斥作為自變量來探討其對員工行為的影響,在具體的行為變量選擇上,本文選擇了員工的角色外行為,因為其對組織的有效運行與發展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并探討組織支持感的中介作用,以期解開上司排斥影響員工行為的“黑箱”。
一、文獻梳理與研究假設
(一)上司排斥與角色外行為
上司排斥是職場排斥行為的一種,指員工遭到來自上司的忽視、漠視和拒絕。角色外行為指的是在職責之外的自發努力,這種努力是一種積極的自愿行為,包括幫助行為和進諫行為。在中國的組織情境下,組織中的政策傳達、資源分配、員工考核大部分都是有直接上司負責的。因此,上司通常被視為組織的代表和象征。同時,上司掌握著相當多的組織資源,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員工在組織中的職位晉升、工資增長、工作資源配給的多寡甚至是個人職業生涯的發展。因此,員工與上司之間的關系質量決定著員工在組織中的發展。
社會交換理論認為,人類的一切行為都受到某種能夠帶來獎勵和報酬的交換活動的支配。因此,人類一切社會活動都可以歸結為一種交換,人們在社會交換中所結成的社會關系也是一種交換關系。因此,從社會交換理論來看,當員工與上司的關系質量高時,即被上司認定為“圈內人”時,上司會利用其組織代理人的身份為員工爭取較多利益,由于上司被認為是組織的代理人,員工會認為這是組織對其的一種認同,會產生強烈的回報動機,在高質量完成本職工作的同時,會做出角色外行為來回應上司的信任,從而使其與組織之間的交換關系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反之,如果遭受上司的排斥與厭惡,會失去大量的組織資源,例如晉升機會、培訓機會等。由于上司充當的是組織代理人的角色,員工往往將其歸因于組織,認為是組織對其的冷漠和忽視。這時員工已經感覺不到組織對其的關心和認同,情感承諾喪失,維持員工與組織的情感紐帶被切斷,則可能由于員工與組織情感關心的破裂而被員工對組織發展和有效運行的漠視所取代。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設:
H1:上司排斥對員工的角色外行為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H1-1:上司排斥對員工的幫助行為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H1-2:上司排斥對員工的進諫行為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二)組織支持感的中介作用
組織支持感用來表示員工感受到的組織對自己的重視程度,并能夠滿足員工的社會、情感需求。根據代理理論,組織的代理人可能是最高層管理者、人力資源部門或直接上司,而直接上司被認為是最關鍵的代理人。[3]因為職場排斥通常表現為對被排斥者的漠不關心,員工在工作場所中所感受到的被其他人忽視或孤立的現象,而來自上司的排斥更會使員工感到其存在的價值得不到組織的認可,其工作表現也得不到組織和上司的重視。
根據馬斯洛需求理論,人的社會、情感需要通常包括自尊需要、歸屬需要、控制需要和有意義的存在,這是人類最基本的需要。排斥會嚴重影響人類的這四種需求,[4]排斥割斷了被排斥員工與他人的社會聯系,從而破壞了員工的歸屬感。同時,上司排斥也傷害了被排斥員工的自尊,因為上司排斥經常是和懲罰相聯系的,它對被排斥員工傳達了你是不被重用的或是低價值的。而且,上司排斥剝奪了被排斥員工在組織中繼續存在的意義,因為遭遇上司的排斥使得被排斥員工在組織的晉升、加薪希望變得非常渺茫,也感覺不到任何組織對其的支持。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H2:上司排斥對組織支持感具有顯著負向影響。
上司排斥使被排斥員工感覺不到組織對自己的重視,并且員工的社會、情感需求也得不到滿足。同時,組織支持理論表明,組織目標的完成依賴于組織如何對待員工,組織的支持滿足了員工的社會情感需求,如果員工感受到組織愿意而且能夠對他們的工作進行回報,員工就會為組織的利益付出更多的努力。[5]但是,上司排斥使員工感覺不到來自組織的任何支持,其與組織的情感聯系被切斷,進而也就失去了為組織做出額外貢獻的動力,員工與組織之間的交換關系破裂。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3:組織支持感在上司排斥與員工的角色外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
根據以上研究假設,構建本文研究的理論模型,如圖1:

二、研究過程
(一)調查方式
本文選取綜合性B2C企業員工作為調查對象。所謂綜合型B2C企業,是指在網站資金實力、網站客流量、轉換率、產品種類和數量、銷售額、網站知名度和消費者熟悉程度上都具備一定規模的自營店鋪或者第三方平臺的網絡店鋪,如天貓商城、京東商城、一號店、卓越亞馬遜、蘇寧易購、國美在線等知名電子商務企業。而不包括專業性的B2C企業,如唯品會、聚美優品、優眾網、麥包包等。因為上司排斥屬于工作場所敏感問題,所以為了最大限度的獲得被調查員工的真實想法,所有調查問卷在發放時均帶有一個已貼好雙面膠的信封,并在問卷顯著位置提示問卷填好后要將其裝入信封并密封。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490份,回收問卷412份,問卷回收率為84.1%。在整理回收問卷時,剔除明顯亂答、錯答及個人信息嚴重不全問卷37份,實際有效回收問卷375份,問卷有效率為91%。有效樣本的人口統計分析如下:從性別上看,男性員工201人,占總樣本的53.6%;女性員工174人,占總樣本的46.4%。從年齡上看,20周歲以下11人,占2.9%;20-25周歲員工103人,占27.5%;26-35周歲員工121人,占32.3%;35-45周歲員工86人,占22.9%;45-55周歲員工31人,占8.3%;55周歲以上員工23人,占6.1%。從學歷上看,高中(中專)及以下13人,占3.5%;大專149人,占39.7%;本科學歷196人,占52.3%;碩士及以上17人,占4.5%。
(二)測量工具
1.上司排斥問卷選取蔣獎等(2011)編制的上司排斥問卷,包括10條題項。利用樣本數據對10條題項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發現,“上司在該介紹我時不介紹我”題項的因子載荷低于0.6,刪除后剩9條題項。經過本研究的樣本檢驗,剩余的九條題目問卷具有較好的信度(α值為0.86)和效度。
2.組織支持感問卷由從Eisenberger等(1986)開發的量表中抽取因子載荷較高的8個題目組成。經過本研究的樣本檢驗,該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α值為0.91)和效度。
3.角色外行為問卷選取Van Dyne和Lepine(1998)編制的量表,包括幫助行為和進諫行為,共13條題目。經過本研究的樣本檢驗,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α值為0.84和0.79)和效度。
所有問卷均采用李克特7點量尺計分,從1到7為7個不同的程度選擇,1表示程度最低,7表示程度最高。
三、假設檢驗過程及結果
(一)假設檢驗
通過相關性分析得出本研究4個變量的相關系數:上司排斥與組織支持感、幫助行為、進諫行為的系數分別為-0.596**、-0.398*、-0.507**;組織支持感與幫助行為、進諫行為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626**、0.239*;幫助行為與進諫行為的相關系數為0.204*。由此得出結果,上司排斥與組織支持感(r=-0.596,P<0.01)負相關,與幫助行為(r=-0.398,P<0.05)和進諫行為(r=0.507,P<0.01)均為顯著負相關。組織支持感與幫助行為(r=0.626,P<0.01)和進諫行為(r=0.239,P<0.05)均顯著正相關。幫助行為與進諫行為(r=0.204,P<0.05)顯著正相關。
Baron和Kenny的研究[6]認為判斷一個變量是否起中介作用時,應該滿足4個條件,以回歸分析為表現形式即為:
1.因變量(兩種角色外行為)對自變量(上司排斥)做回歸,得到結果的回歸系數應顯著不為零;
2.中介變量(組織支持感)對自變量(上司排斥)做回歸,其結果的回歸系數應顯著不為零;
3.因變量(兩種角色外行為)對中介變量(組織支持感)做回歸,其結果的回歸系數應顯著不為零;
4.因變量(兩種角色外行為)同時對自變量(上司排斥)和中介變量(組織支持感)做回歸,中介變量的回歸系數應顯著不為零,自變量的回歸系數應為零,或顯著降低。此時,如果自變量的回歸系數下降到不顯著,則表明中介作用為完全中介;如果自變量的回歸系數有所下降,但還是處于顯著水平,則說明中介作用為部分中介。
因此,根據以上說明,本研究將上司排斥、組織支持感和兩種角色外行為之間的回歸系數進行了匯總,如表1:

表1 組織支持感中介作用回歸分析表
通過表1的匯總分析,得到以下結果:
(1)上司排斥作為自變量,兩種角色外行為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分析表明,上司排斥對兩種角色外行為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267、-0.412,sig均小于0.05,表明判定中介作用條件(1)成立,同時本研究假設1、1-1、1-2成立;
(2)上司排斥作為自變量,中介變量組織支持感作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分析表明,上司排斥對組織支持感的回歸系數為-0.377,sig小于0.05,表明判定中介作用的條件(2)成立,同時本研究假設2成立;
(3)中介變量組織支持感作為自變量,兩種角色外行為作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分析表明,組織支持感對兩種角色外行為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514、0.132,sig均小于0.05,表明中介作用條件(3)成立;
(4)上司排斥和組織支持感同時為自變量,兩種角色外行為分別作為因變量做回歸分析。分析表明,在控制組織支持感這一中介變量以后,上司排斥對兩種角色外行為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61、-0.229,均小于不加入組織支持感作為自變量時的回歸系數-0.267、-0.412,同時sig也均小于0.05,回歸系數下降,但還是處于顯著水平。因此,可以判定組織支持感在上司排斥與兩種角色外行為之間起中介作用,但是為部分中介,表明上司排斥對兩種角色外行為的影響還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同時本研究假設3成立。至此,本研究所有假設均得到驗證,所有假設均被證實。
四、結論、研究不足及展望
(一)結論
本研究以綜合性B2C企業為研究對象,從上司排斥的視角出發研究了其對員工兩種角色外行為的影響,并以社會交換理論為基礎探討上司排斥影響員工兩種角色外行為的作用機制。通過研究得出以下結論:(1)上司排斥負向影響員工的兩種角色外行為。(2)組織支持感在上司排斥影響員工兩種角色外行為方面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二)研究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雖然取得了一些積極的研究成果,但還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在樣本的選取上,本研究的樣本全部來自綜合性B2C企業,雖然能做到有效控制樣本行業類型,但還是存在著一定的同源偏差,并帶有一定的行業特征。后續研究應該在更廣闊的行業背景下進行,來避免本研究所遇到的問題。第二,本研究僅從社會交換的理論視角探討了組織支持感在上司排斥與員工兩種角色外行為的中介作用。但上司排斥對結果變量的作用機制應該不局限于組織支持感。未來的研究應該從其他理論視角出發,去探討職場排斥的作用機理。
[1]李銳,凌文輇,方俐洛.上司支持感知對下屬建言行為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J].中國軟科學,2010(4).
[2]倪倩,儲小平.領導-部屬交換、領導自尊與組織公民行為——來自中國大陸的實證數據[J].經濟管理,2010(1).
[3]Liden.R.C,Bauert.N.The Role of Leader member Exchange in the DynamicRelationshipbetweenEmployerandEmployee:Implications for Employee Socializat ion,Leaders,and the Organizations[M]//COYLE-SHAPIROJ,SHORE L,TAYLOR M S,et al.The Emp loyment Relationship:Examining Psychological andContextualPerspectives,London:OxfordUniversity Press,2004:226-250.
[4]Williams,K.D..Ostracism:The Power of Silence.New York:Guilford Press,2001.
[5]劉維民,何爽.組織支持研究進展綜述[J].社會心理科學,2009(5).
[6]Baron,L.S.&Kenny,D.A.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inSocialPsychologicalResearch:Conceptual,Strategic,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y,1986:1173-1182.
[7]Ferris,D.L.,Brown,D.J.,Berry,J.W.,Lian,H.,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workplace ostracism scale[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8,93(6).
[8]吳隆增,劉軍,許浚.職場排斥與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組織認同與集體主義傾向的作用[J].南開管理評論,2010,3(13).
【責任編輯王鳳娥】
F270
A
1674-5450(2015)05-0061-03
2015-03-13
何海英,男,遼寧北鎮人,遼寧大學企業管理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