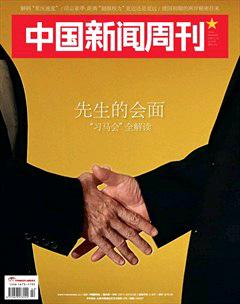重慶的發展善于“無中生有”
劉賢
就重慶經濟發展的路徑和邏輯,《中國新聞周刊》采訪了重慶市人大副主任楊慶育。自上世紀90年代起,楊慶育先后在重慶市政府政策研究室、計劃委員會等部門工作,2006年至2013年期間,他擔任重慶市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主任,參與了該市很多經濟政策的制定。他認為,重慶經濟的快速發展,主要得益于抓住了深化改革、全面開放、創新驅動這三條主線。
“重慶也有經濟下行的壓力”
中國新聞周刊:今年上半年,重慶市以11%的GDP增速領跑全國。你怎么看這個增速?
楊慶育:我始終認為,中國保持了經濟健康增長的基本面沒有變,這一點是很關鍵的。

(資料圖片) 楊慶育。圖/CFP
在這個背景下,重慶不能獨善其身,從2010年到2014年,到2015年上半年,整個經濟也受到經濟下行的壓力,增長速度一路向下,這個趨勢非常明顯。2010年重慶的增長速度是17.1%,2014年到了10.9%,今年上半年基本上和去年持平。一方面大家看到這個速度是全國第一,但如果縱向比較,是一個明顯的下行趨勢,而且比國家的下行速度還要快。
核心問題是什么呢?應該怎么去理解重慶面臨的這種下行壓力,關鍵在于11%是不是健康的,是不是可持續的,背后有什么因素在支撐著它。
中國新聞周刊:那你認為重慶經濟發展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因素支撐?
楊慶育:我認為,重慶在發展的過程當中有很多因素在支撐。比如中央的支持、全國各省市的幫助等,但關鍵有三點:深化改革、全面開放和創新驅動。這也應該是重慶在“十三五”發展規劃中應該遵循的三條基本原則。
深化改革,一般人認為改革是出一些政策,出一些方案。我認為改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要結合本地區的發展,出臺一些重大的改革方案,比如重慶的城鄉統籌改革;二是應該用改革的精神去推動實際的工作。
我舉幾個例,比如重慶的渝東北和渝東南,其資源稟賦決定了它們的發展是以生態環境保護為主的,如果說對這兩個地區不能做出這樣的客觀分析,而非常簡單地要求他們一定要發展經濟,這就違背了客觀現實的規律。在2013年,孫政才書記主政重慶后,從資源稟賦、現實開發強度和發展潛力三個方面確定了五大功能區域發展戰略,包括城市功能核心區、拓展區、城市發展新區、渝東北生態涵養發展區、渝東南生態保護發展區。這就把以前同質化的區域發展,變為差異化的非惡性競爭的發展,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改革的體現。
又如,重慶以前電子信息產業很薄弱。重慶在研究了歐洲和北美等國家對電子信息產品的需求,然后又分析了惠普、宏基等這些整機企業在全球的運作歷程,發現他們的整機廠幾乎布局在中國沿海,但其零部件都分布在全世界各地,這是扁平式的布局。將全球各地的零部件集聚到沿海,又把大量的產成品源源不斷地運離中國,這和改革開放之初的大進大出雷同。如果說把這種扁平式的生產力布局調整為垂直式的生產力布局,就可以把大進大出的物流費用節省下來,從而提升產品的競爭力。
按照這種思路,已經形成了具有重慶特色的電子信息產品基地。我們說服宏基和惠普等整機企業齊聚重慶。他們進入后,其代工企業如富士康也會隨之進入重慶。整機企業和代工企業就會帶動零部件企業蜂擁而至,到目前為止,共有接近千家的電子信息零部件企業,分布在西永微電子園區和重慶保稅區周邊方圓一百平方公里以內,半小時車程,物流非常便利。
吸引整機企業進入重慶的訣竅是什么呢?主要是考慮到加大本地的配套力度。我們分析了重慶的產業結構,認為有條件在整機廠進入的第一年實現本地配套10%,第二年30%,第三年70%,這對整機廠是一個很大的吸引力,因為這樣可以大幅度地降低物流成本,從而提升產品的競爭力。到目前為止,已經實現了這個目標。這就將扁平式的生產力布局變為垂直式,重慶就“無中生有”地打造了一個千億元的產業。
隨后就考慮物流的問題,重慶生產的筆記本電腦大多銷往歐洲,怎樣使物流成本降下來?我們與國家海關、商務部以及鐵道部協商,希望能得到他們的支持,開通重慶經新疆阿拉山口到德國杜伊斯堡的杜塞爾多夫的直通線,并邀請沿途各國的海關在重慶開會,最終實現了多國聯合通關。這樣一來,就把物流的時間從沿海走向的四十余天縮短到十八天。
節約這二十多天有什么意義?電子產品需要很多流動資金,流動資金需要大量的銀行貸款,銀行的利息就是財務成本。重慶的渝新歐線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今年6月份,我去波蘭參加了中波地方發展論壇,介紹了重慶的渝新歐線。第一開辟最早,第二運量最大,第三通達能力最強,第四返運的貨物最多。到目前為止,一共運出了一百多億美元的產品。
2013年,重慶開始考慮另外一個問題。送貨過去放空車回來,物流成本仍然很高。如果能把我們需要的歐洲產品運回來,豈不是兩全其美!后來了解到,要運回歐洲產品,重慶必須要有相應的口岸。所以市政府到了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和海關去爭取整車及相關商品口岸,把歐洲的產品運回來。這樣實現了產品的雙向流通,這個過程實際上是一種改革精神的體現。
現在,重慶形成了三個交通樞紐,即航空樞紐、陸地的鐵路和公路的交通樞紐以及長江上游的水運交通樞紐,三個國家的一類口岸,三個保稅區,這在中國的中西部,內地是唯一具有“三個三”的城市。
產業鏈要集成考慮。一個產品生產出來銷售出去,必然產生結算,結算是在哪里呢?調查發現,都不在重慶,廠商都說中國有規定不能在內陸做結算業務。于是,重慶市政府就到國家外匯管理局匯報,得到了他們的支持。這樣,重慶首開先河,實現了在內陸進行商品出口外匯結算的試點。惠普第一年就有600多億美元在重慶結算,到目前為止,每年有2000多億到3000億美元的結算。
第二個是全面開放。國家在1985年實現沿長江開放戰略,但重慶開放的步伐受多方面條件制約很緩慢。這幾年開放取得了很大進步,在不到五年的時間內,我們利用外資從不到20億美元上升到100億美元;進出口總額在七年的時間,從60多億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近千億美元,增長速度相當驚人。目前在總額上已經位列全國第八。重慶的GDP是1.4萬億元,而進出口是6千億元左右,占GDP的比重接近50%,2015年上半年已經超過50%。
作為一個內陸開放城市,重慶在開放上這幾年做了些什么工作呢?我認為以前我們是研究一個產品或一個企業,后來我們發現,做一個產品應該研究它的前端如原材料,以及后端的研發,即從一個產品上升到產業鏈。后來我們又發現,與某一個產品相關聯的其他產品的集合的綜合開發,就上升到了產業集群。現代化的工業已經不是一個產品產業鏈的概念,而是一個產業集群的概念。
現在看來,前端的研發和后端的市場開發是非常重要的,中間的生產是相對簡單的。我們以前關注中間的生產,不太關注兩端,其實質就是沒有考慮產業集群。我們的開放是指重慶域外的開放,不是僅僅指境外的開放。所以近幾年,重慶非常注意與周邊省份的協作與聯合。同時重慶的企業也非常注意走出境外,這幾年效果明顯,例如重慶力帆汽車已經在俄羅斯、埃及、越南建設了自己的整車工廠。2015年上半年重慶企業走出去的投資達到8億美元,是歷史的最好水平。
第三個是創新驅動。重慶的投資率目前仍然很高,達到接近90%。沿海的投資率一般只有30%左右。但在重慶,投資還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投資上,重慶比較重視創新驅動。這表現為在新引進企業時就注意研發必須要進來,生產銷售及數據處理和結算都要進來,要把一個產業鏈全部引進來。比如說現在惠普的研發中心就放在西永,創新原點在這里。新產品就會在這里不斷的涌現。重慶2014年全市的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不到2%,市委決定在“十三五”末要達到3%,超過全國的平均水平。
在投資的問題上怎么創新?資金來源怎么辦?不能總是靠財政。重慶引入了PPP模式,即政府和社會相結合的融資方式。去年推出了1300億元的項目,今年上半年又推出了1千億元的項目。
中國新聞周刊:你剛才說重慶在做電子信息產業,通過集群布局來推動這個產業的發展,這個過程是發改委最先提出了一個方案,還是市里的領導有這么一個想法,然后讓發改委具體實施?
楊慶育:發改委和經信委都在做這個工作,這是漸進的過程。做出了產業的分析后,就去找整機企業商談,例如惠普問你那里有什么,我們說你需要什么我們就創造什么,重慶是一個綜合性的老工業城市,目前在西永又有一個微電園,旁邊還有一個大學城,有二十幾所大學,可以滿足微電園對高級技術人員和各級技工的需要。園區建了大量的標準廠房。這叫什么呢?這就叫筑巢引鳳。你必須要付出筑巢的成本,才可能引來鳳。這樣,我們說服了惠普,惠普一進來就形成了一種帶動效應,其他整機企業也隨之進來了。
“‘十三五重慶經濟增速保守點是9%”
中國新聞周刊:我們在重慶采訪了一些專家,他們都提到,重慶的很多改革,有向上海學習的地方,特別提到奇帆市長是從上海過來的,這些工作,很多也和他有關。
楊慶育:我認為奇帆市長有上海浦東新區管委會副主任的經歷,根據我們分析,重慶比上海落后十年左右,現在差距在逐漸縮小。一個地方的改革開放的經驗,很難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復制。奇帆市長到重慶已經有十二年了,已經融入到重慶。他在城市經營的理念上很超前,我認為更重要的是他從改革開放的前沿帶來了一種精神,帶來了西部所不具備的東部的開放理念,這個財富非常寶貴。他不是簡單地把浦東新區的經驗復制到重慶,而是帶來先進地區的開放理念,這些理念又武裝了重慶人,就會帶來極大的效應。所以我認為不是重慶復制了上海的經驗,而是上海的經驗武裝了我們。比如說重慶的房產稅和上海就完全不一樣。在設計重慶房地產稅時,就是從重慶的實際情況出發的,并非簡單復制上海。
上海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我常說在長三角,江蘇和浙江的GDP都比上海高,但是都認為上海是老大哥,因為上海站在高端。但是在云貴川渝,大家就不會認為重慶是老大哥。貴州的GDP沒有重慶高,云南和我們差不多,四川的人均GDP比重慶低多了,但他們并不認為你是老大哥,因為你不像上海那樣站得高。
有人說重慶過于重視GDP,在重慶這樣的地方,不說GDP還是不行。
中國新聞周刊:對于“十三五”期間重慶經濟發展,你有怎樣的預期?
楊慶育:現在重慶的增速已經在一個相對比較穩定的位置上了,再往下降,到9%也是可能的。我認為“十三五”重慶的經濟增速保守一點就是9%,也可能到10%,這也算高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