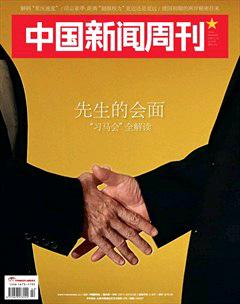快遞實名制:誰為上漲的成本埋單
李騰
雙11來了,在這個快遞員最盼著賺錢的日子,王明卻想著辭職。
天氣轉冷,王明已經穿上了保暖內衣和毛衣。現在他的工作比以前更繁瑣了,因為柳州爆炸事件后,片區里的傳達室和門衛都不代收快件了,擔心有炸彈。“現在又要我們查客戶身份證和快件,以后更累了。”王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每年的11月是快遞業務量最大的時期,大約是平時業務量的2到3倍。國家郵政局數據顯示,2014年11月快遞業務量達到16.5億件,占全年業務量的11.8%。此時也是快遞員掙錢最多的時候。
2015年的11月,快遞的一項新規出臺,從11月1日起,快遞實行實名制,也就是寄送快遞必須出示身份證并且進行相關登記。快遞員們高興不起來了,若新規得以執行,收入必定下降。“因為精力有限,付出同樣多的辛苦,送出的快件卻變少,還要誰收寄、誰負責。”王明說。
而公眾對實名制和查件似乎也有抵觸情緒,擔憂個人信息泄露以及快遞收發速度。有意思的是,如果刨去主觀因素,單說實名制和查件的必要性時,快遞員們對此持支持態度。
在業內人士看來,這是權利和責任不對等的結果,實名制雖是大勢所趨,但必須是在各項配套措施完備的前提下,否則就變成了“方便政府,麻煩群眾”。
有責任,無權利
2015年10月22日,中央綜治辦、公安部、交通運輸部等15個部門聯合決定,從當日起至2016年3月底,開展“危爆物品寄遞物流清理整頓和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專項行動”,提出“收寄驗視、實名收寄、過機安檢”三項措施。2015年11月2日,國家郵政局也下發了《集中開展寄遞渠道清理整頓專項行動實施方案》,要求全面落實上述三項措施,并明確指出,快件達不到100%通過X光機安檢的快遞企業,要被限期整改。
各大快遞公司在給《中國新聞周刊》的回應中都聲稱已有部署。圓通速遞在書面回應中聲稱:已在全網范圍內要求全面實行實名收寄制度,除信件和已有安全保障機制的協議客戶的快件、通過智能快件箱等交寄的快件外,一律要求寄件人出示有效身份證件并進行比對,再將姓名、證件號碼記錄在筆記本;若拒絕提供身份證件,一律拒收。
盡管公司已有要求,但新規正式生效后,各地均曝出“梅長蘇”“流川楓”“咸蛋超人”之類的名字,仍然可以寄件。圓通速遞某站點站長對《中國新聞周刊》坦言,現在收寄還不需要身份證,因為現實條件不允許。“每天上千個快件等著派送,真要挨個查就等著爆倉吧。”
對快遞員來說,實名制也要面對著與客戶的磨合問題,“我們也希望客戶實名寄件,但查身份證是不可能的,90%的客戶不配合,時間耽誤不起。” 快遞員方衛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據方衛介紹,他每天的收單數在40單左右,完全按照新規挨個查客戶身份證外加查件,一個快件耽誤3分鐘,那每天就要多干2個小時。而且,若遇到不好說話的客戶,給他一個差評,他就只能認倒霉了。“公司每年給我們每人30個工作積分,一個差評扣1分,30分扣完年底就沒有獎金了,怎么敢得罪客戶。”方衛說。
與此同時,送貨速度下降也令方衛憂心不已。收貨時間延長,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肯定會造成送貨延遲。而國家郵政局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郵政業消費者申訴中心共受理消費者申訴71.9萬件,同比增長86.2%,其中申訴最多的就是延誤,占比43.4%。緊隨其后的則是投遞服務,占比29.3%。“對于我們來說,速度才是第一位的。誰嚴格執行新規,誰可能就要被淘汰。”方衛有些擔憂。
很多時候,客戶不愿意讓快遞知道包裹里裝的是什么,都是先封好口再遞給快遞。快遞員杜寧說,有一次在收件時,他感覺包裹內的東西與單子上填的書本不符,提出查件。客戶大發雷霆,把快件從他手里奪了過去,沖他吼了句“事兒這么多”,然后一甩手便關上了門。“現在的人比較注重隱私,客戶即便是寄一本書,也不想我們查看。而且,怕我們偷東西。”杜寧說。
說到偷竊,杜寧直搖頭。據他介紹,快遞行業魚龍混雜,大公司管得緊,待遇稍好,偷東西的情況比較少,小公司就難說了。手機和名牌手袋被掉包的事情已經不新鮮了,就連客戶寄十幾個雞蛋,杜寧還親眼見到有快遞員偷偷拿走幾個。“我們公司為了防止快遞員偷東西,都是雙層包裝。”他說。
然而,快遞員最不能接受的是,新規“誰收寄、誰負責”的原則。王明透露,公司要求每個人在收寄快件時,都要自覺擔起檢驗員和政策宣傳員的職責,勸說不配合的客戶;記錄下信息后還要負責保護客戶隱私,一旦發生泄露要追究責任;查件后若出現違禁品,還要負連帶責任。
多位快遞員表示,若客戶真想做違法的事,他們很難查出。“我們頂多是看一眼,不可能把貨物拿出來里里外外搜一遍。”快遞員說。一旦出事,若快遞員按照規定走完全部流程,就要擔重大責任;但如果沒有看身份證和查件,可以推說客戶不配合,只承擔違反操作流程的責任。因此,兩害相權取其輕,快遞員不按新規行事也成為一種自我保護。
信息買賣難以避免
公眾普遍擔心實名制后,個人身份信息會發生泄露,各種騷擾電話和信息紛至沓來,尤其是與身份證綁定的銀行卡會不會被盜刷。多位快遞員認為,身份信息泄露難以避免,因為一部分快遞員為掙外快將客戶個人信息出售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杜寧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快遞員送一個單子提成在1元到1.5元之間,賣客戶信息每單至少可以賺5毛錢。這是除了掉包、偷竊之外,快遞員黑色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
按照公司規定,所有底單都必須拿回公司留存,但這似乎無濟于事。快遞員都是用手機將底單牌照,然后批量發給買家。“微信轉賬、日結、長期合作,很方便。一天賣一百多個單子,一個月就有將近2000元收入。”杜寧說。
杜寧不相信自己從事的這個職業能夠自律。在他看來,同行都是底層的打工者,能有掙外快的機會都會抓住。“送奶的、送洗衣服的、就連銀行的人都在賣,大家都是這么干的,這么一想也就心理平衡了。”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快遞公司對提成政策的調整將對保護個人信息造成不利影響。
方衛對《中國新聞周刊》透露,他們公司近期調整了提成政策,不再按單提成,而是按批提成。比如,原先一次給某公司送10個快件,可以提10塊錢,現在只有1塊錢。為了提高效率,快遞員原來都是盡量一口氣多送少跑,現在一起送反而吃虧,分開送時間又不允許。雖然公司補充規定5公斤以上的快件,1公斤補1塊錢,“但除了整箱水之外,平時快遞的東西能有啥超過5公斤呢?”方衛說。
圓通速遞在給《中國新聞周刊》的書面回復中稱,公司已經建立了個人信息保密制度,會設轉崗專人負責收集和保管寄件人、收件人的個人信息。但圓通某站點站長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公司還沒有對他們提出任何新要求,即便真有要求,效果也有待觀察。“底單回收時間長,經手人多,根本堵不住。”這位站長說。
除了流程問題外,站長坦言,人手問題讓公司很難下決心整治。國家郵政局官網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快遞業務量達到139.6億件,而快遞員只有一百二十多萬人,平均每人每天要送三百多件才能完成任務,現在每天基本只能送一百多件,勞動力缺口很大。上述站長表示,除非所有快遞公司統一行動,否則必然造成員工流失。“以目前國內市場的環境來看,各公司統一行動還是個沒影的事兒。”
快遞行業專家、上海財治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執行總裁趙小敏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現階段我國對大數據的保護嚴重不足,雖然目前出售或者提供個人信息最高可判7年,但對犯罪主體和侵權行為沒有更詳細的規定,缺乏可操作性。而且快遞實名制并不一定要查看身份證,國家一直在推行手機號碼與身份證綁定,“如果國家各個部門之間能夠真正實現數據共享,那么收寄快遞根本沒有必要再查看身份證。”趙小敏說。
價格漲、服務降
值得關注的是,國家郵政局在配合專項整治行動的同時,還要求貫徹落實國務院于2015年10月26日出臺的《國務院關于促進快遞業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為快遞業給出了明確定義:是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動流通方式轉型、促進消費升級的現代化先導產業。
《意見》提出了多個發展目標,被業內人士稱為快遞業的“十三五”規劃,包括到2020年形成覆蓋全國的服務網絡、快遞年業務量達到500億件、年業務收入達到8000億元等。《意見》甚至還提出要制定快遞專用機動車輛系列標準。
然而,在趙小敏看來,雖然《意見》提出包括開放市場、提供小額貸款等多種利好措施,但由誰來牽頭、誰來協調都沒有規定,能夠實施的只剩下實名制、查件、新車輛標準等等增加企業運營成本的內容,服務質量反而會下降。
以制定快遞專用車輛標準為例,快遞三輪車的弊端在于后方視線受阻,容易發生剮蹭事故,但能滿足快遞需要,是市場選擇的結果,國家完全沒有必要插手。趙小敏說,珠三角和南方許多城市已經禁止使用三輪車,現在又要出臺快遞車輛標準,究竟是又允許使用三輪車還是其他城市都淘汰三輪車,令人費解。此外,直接更換車輛需要大量投入,企業負擔不起。
在他看來,2020年快遞年業務量達到500億件的目標或許只是一廂情愿。國家郵政局官網顯示,2010年至2014年4年時間,我國快遞年業務量從23.4億件增長到139.6億件,年均增速達到50%。但業內普遍認為目前經濟下行壓力增大,而且東部發達地區市場已經飽和,不可能維持50%的增速。“先要有消費,然后快遞才能發展,不能用往年的數據來推算。”趙小敏說。
針對民眾關心的送達率和準時率問題,《意見》要求建立覆蓋全國的服務網絡,實現鄉鄉有網點,村村通快遞,重點城市48小時送達。但國家郵政局統計數據表明,2014年我國東部地區快遞業務量占82.8%,而且比重呈上升趨勢,其中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三個重點地區的業務比重就占到全國的7成以上,而中西部地區加一起還不到2成。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很難“向西、向下”發展。此外,過去數年東部地區的72小時準時率也只有70%,西部地區只有50%,5年內實現48小時準時率100%難度更大。
國家郵政局官網顯示,目前經各級郵政管理部門許可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共12428家。趙小敏說,實名制等一系列措施使中小企業難以生存,兼并重組將是必然,快遞價格將持續上漲。“在過去數十年的實踐證明,快遞行業不需要所謂鼓勵發展的政策,需要的是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 趙小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