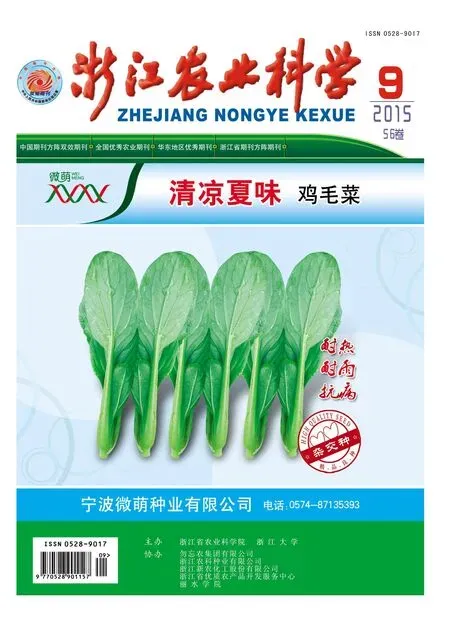農業補貼視角下土地流轉調查與分析
呂悅風
(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江蘇南京 210095)
農業補貼視角下土地流轉調查與分析
呂悅風
(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江蘇南京 210095)
為了探討農業補貼政策對于土地流轉行為的影響,利用山東、浙江295個農戶的農業補貼對土地流轉意愿影響的調查資料,對當前農業補貼政策發放及土地流轉的具體情況進行分析。結果表明,(1)調查地區土地總體流轉比例較高,農戶土地流轉率達50.5%。農戶的土地流轉年限較短,以5年期限以內為主。土地流轉方式主要以熟人之間的自主流轉為主,占90%以上。流轉契約形式以口頭協議為主,合同形式較少。農戶土地流轉面積普遍較小,主要集中在0.07~0.33 hm2,致使實際土地流轉效率偏低,農戶仍以“小農經營”模式為主,這不利于現代農業化發展。(2)浙江嘉興農戶土地流轉比例最高,達77.6%,山東臨沂次之,達62.2%,而山東濟寧、浙江湖州和浙江杭州的流轉率在3成左右。浙江的土地流轉面積占比(平均流轉面積/平均承包面積)明顯高于山東。(3)當前我國農業補貼政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仍存在農業補貼力度偏低、補貼發放錯位等諸多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農村土地的流轉。
土地流轉;農業補貼政策;農戶流轉意愿
文獻著錄格式:呂悅風.農業補貼視角下土地流轉調查與分析[J].浙江農業科學,2015,56(9):1524-1527.
DOI 10.16178/j.issn.0528-9017.20150960
土地是農業的根本,是農民重要的社會保障,也是農村長期穩定的基礎。當前,我國農業生產經營規模普遍較小,土地細碎化現象嚴重,以家庭小農為主的分散經營格局不利于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和機械化發展,大大降低了農業生產效率,阻礙現代農業的發展[1]。因此,土地流轉成為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推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促進農業轉型發展的主要抓手。
事實上,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央政府通過一系列新農地政策,鼓勵和激活農地承包經營權的市場流轉,希望通過流轉促進農地向適度規模經營集中,以期擴大農業經營規模,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改善農民生活水平。然而,現實情況是農地流轉并未廣泛向規模經營集中,農地的小規模、分散經營狀況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我國仍然處于土地利用的初級階段。
近年來,國內大量的研究從理論和實證2方面探討影響農戶土地流轉的影響因素。其中,農地制度、產權、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農戶資源稟賦、社會保障水平和農業生產結構等受到了學者的廣泛重視[2-6],但大多數研究將土地流轉作為單一問題進行探討,忽略了與其他農業政策間的協同影響。同樣為了保障種糧積極性和農民收益,我國于2004年開始實施以糧食直接補貼、農資綜合直接補貼為主要內容的農業補貼政策,這對促進糧食增產、調動種糧積極性、增加農民收入乃至改善基層干群關系等諸多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與此同時,隨著農業稅的取消和農業補貼力度的不斷提高,改變了農民的土地經營預期收益,從而影響了土地經營的策略和方式,對土地流轉產生了影響[7]。鑒于中國的涉農政策已從單一目標取向轉向注重均衡的多元目標取向的趨勢[8]。梳理農業補貼政策對土地流轉的影響,探索農業補貼與土地流轉間的內在關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本研究以來自山東、浙江地區的295份調查問卷資料為樣本,從農業補貼的角度,分析土地流轉的現狀與規模,以期理解農業補貼政策對土地流轉可能產生的潛在影響,為政府決策選擇和政策修訂提供借鑒。
1 數據獲取及樣本情況
本分析研究數據來源于國家大學生創新性實驗計劃項目《農業補貼對農戶土地經營權流轉意愿的調查》(201410307060)。項目組成員于2014—2015年對浙江和山東2省8個縣(市、區)14個鄉鎮進行了農業補貼政策對農戶土地流轉意愿影響的問卷調查。問卷主要從農戶家庭特征、農業補貼政策實施和農戶土地流轉意愿3大方面展開。獲得山東有效問卷144份,浙江有效問卷151份,合計有效問卷295份。
2 農戶土地流轉特點
2.1 流轉年限
對研究區調查發現,農戶土地流轉年限在5年以內的農戶數占多數(最短的為一季),共有82戶,占流轉農戶數的55.0%,而流轉年限超過10年的農戶明顯減少,僅有8戶,占流轉農戶數的5.4%。說明土地流轉仍處于短期化階段,這種短期的土地流轉行為,使經營者不能有長期打算和計劃安排,容易造成耕地的掠奪性經營,不利于耕地質量的培育和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
2.2 流轉方式
據調查結果,目前土地流轉途徑仍以自主流轉為主,土地流轉的方式過于單一,90.0%以上的土地流轉行為發生在親屬或者熟人之間,通過中介機構流轉的比例很小。而且只有6.7%的土地是流向了種糧大戶,很少有大規模的種糧大戶參與流轉。在流動契約方面,74.5%的農戶間流轉只是憑口頭協議,只有23.5%的農戶簽訂了土地流轉合同,可見農村土地流轉的合約與法律意識薄弱。近年來,隨著農業補貼額度的增加,因事先沒有流轉合同的約定而引起土地流轉的糾紛和矛盾持續增加,加之土地流轉規模小而分散的現狀,影響規模化經營的發展。
3 不同地區土地流轉現狀
3.1 土地流轉現狀
長沙市共六區二縣一市,分別為芙蓉區、天心區、岳麓區、開福區、雨花區、望城區、長沙縣、寧鄉縣及瀏陽市,行政面積、人口分布等社會經濟資料來自湖南省統信息網站。
在山東和浙江的295戶被調查農戶中,共有149戶發生土地流轉行為,占樣本總數的50.5%。不同地區土地流轉差異較大,以浙江嘉興土地流轉情況最為活躍,流轉比例達77.5%,山東臨沂緊隨其后,流轉農戶占調查農戶數的62.2%,而山東濟寧、浙江湖州和杭州流轉情況則大體相似,維持在3成左右(表1)。

表1 不同地區土地流轉(流轉和流入)的情況
3.2 土地流轉面積情況
進一步分析發生流轉的149個農戶的流轉面積情況(表2),2省5市8個調查縣(市、區)農戶土地流轉面積呈現出“兩邊低,中間高”的正態分布。流轉面積>0.33 hm2與流轉面積<0.07 hm2的農戶數量相對較少,農戶流轉土地面積主要集中在0.07~0.33 hm2。說明當前土地經營模式仍然以“小農經營”模式為主,土地流轉規模也主要以“小打小鬧”為主,規模經營戶和大面積土地流轉情況出現較少。

表2 不同地區農戶土地流轉面積的情況
3.3 土地流轉面積占比情況
進一步分析不同地區土地流轉面積占比(表3)可知,盡管各縣(市、區)平均承包面積與流轉面積各不相同,但是流轉面積占比(平均流轉面積/平均承包面積)表現出明顯的區域性差異,即浙江地區流轉面積占比明顯高于山東地區,這種情況與表1山東地區流出戶數與流入戶數基本一致,而浙江地區流出戶數明顯多于流入戶數的情況是相吻合的。其原因在于:浙江省經濟發達地區,農民轉投到第二、三產業的機會較多,社會保障體系也較為完善,大多數農戶選擇耕地流出,把耕地流轉給種糧大戶或種糧能手進行規模經營,表現為耕地流出戶數大于流入戶數,流轉面積占比較高。通過這種形式的土地流轉,能有效實現土地集約利用,進而推動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
山東流轉面積占比明顯低于浙江,這與山東省耕地承包面積較大,經濟相對欠發達,農戶有著比較濃厚的戀土情結,不太愿意把土地流轉出去有關,加之土地流轉體系的欠完善,因此表現為流轉面積占比較低,流出戶與流入戶數量相當。盡管山東總體流轉數量和比率較高,但此類小面積自主流轉并未能有效改變當前農村耕地利用的形式,需要在政策制定中加以重視。

表3 不同地區土地流轉面積占比的情況
4 農業補貼政策對農戶土地流轉意愿影響
4.1 農業補貼發放對象分析
毫無疑問,農業補貼的對象是種糧農民,其目的是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促進糧食生產穩定發展。據實地走訪調查結果,當前農業補貼類型主要是以糧食直補與良種補貼為主,農機具補貼的情況較少,說明目前我國農村經營主要還是以小農經營模式為主,大規模機械化的生產方式較少。同時明確,69.2%的農業補貼的實際對象為耕地所有者,而非實際耕種者,這與我國“誰種糧誰收益”的農業補貼政策目標相違背。目前農業補貼中普遍存在“誰的土地誰收益”和“只補流出者,不補流入者”的現象,這種補貼對象的錯位,使得種糧大戶無法享受農業補貼政策的真正實惠,挫傷了實際種糧者的積極性,不利于土地大規模流轉情況下規模經營的形成與發展。
4.2 農業補貼發放力度與土地流轉分析
據調查結果發現,不同地區種糧補貼額度不一樣,濟寧市魚臺縣和金鄉縣種糧補貼額度在225~1 800元·hm-2,臨沂市沂水縣和莒南縣補貼額度為1 500元·hm-2,嘉興市嘉善縣補貼額度在750~2 250元·hm-2,湖州市長興縣補貼為1 500元·hm-2,吳興區則為750~1 020元·hm-2,杭州市蕭山區補貼額度則有1 500元·hm-2與1 800元·hm-22檔。可見不同省市,甚至同一省市的不同地區補貼種類、范圍與金額均不相同。另外,調查中發現,61.4%的農戶認為農業補貼政策對農戶種糧積極性有促進作用,但同時有85.1%的農民認為當前的農業補貼金額仍然偏低,不能很好地滿足農戶期望,當然也不能有效地促進土地流轉與集約利用。研究進一步發現,隨著補貼額度的逐步增加,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農民的“惜地情節”和“惜地意識”,這一方面使得農民不太愿意流出土地,另一方面在流轉雙方協商耕地租金時,往往會把農業補貼作為租金的全部或一部分,其結果抬高了實際種糧者的種糧成本。流轉成本的升高對土地流轉起到抑制作用,從而影響土地資源的高效配置與規模經營,也不利土地流轉的長期穩定發展。
5 小結及政策建議
5.1 小結
本研究通過對源自山東與浙江的295份農業補貼對土地流轉意愿的調查問卷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調查區域總體土地流轉率較高,達50.5%,然而土地實際流轉效率依然偏低。具體表現為農戶土地流轉年限較短,以5年以內短期流轉為主,占55%,而流轉年限超過10年的農戶僅占5.4%;土地流轉途經主要以熟人之間的自主流轉為主,占90.0%以上;土地流轉的規范性有待完善,口頭協議成為主導;土地流轉規模主要以0.07~0.33 hm2的小面積流轉為主。總體而言,目前土地仍以小農經營模式為主,不利于規模經營與現代農業的發展。
比較不同調查地區,從農戶流轉的比例看,浙江嘉興市土地流轉情況最為活躍,農戶流轉比例達77.5%,山東臨沂市緊隨其后,農戶流轉率為62.2%,而山東濟寧市、浙江湖州市和杭州市流轉情況則大體相似,維持在3成左右。從土地流轉面積占比來看,浙江的土地流轉面積占比明顯高于山東。說明浙江土地流轉總體上要好于山東。
當前我國農業補貼政策的實施,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對于農戶種糧起到了激勵作用,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仍存在農業補貼力度偏低、補貼發放錯位等諸多問題。正是由于農業補貼與土地流轉間政策的契合度不強,致使當前農業補貼政策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對農村土地流轉起到了抑制作用。
5.2 建議
為了健全中國特色的土地流轉制度,使得土地流轉的各方達到利益共贏的局面,同時推動我國農村改革,促進農業發展,除了要堅持以市場機制為主要手段,結合相關的扶持政策外,還要進一步健全與之相配套的土地流轉市場體系和農業補貼制度[9]。針對以上情況,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規范土地流轉行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土地作為最基本的不可替代的生產資料理應進入市場,通過市場進行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地方政府應積極完善土地流轉服務體系,建立土地經營權流轉市場與交易平臺,土地流轉信息發布、咨詢、預測、評估等中介組織;規范流轉委托行為,制定流轉價格調節機制,指導簽訂土地流轉合同,并實現土地流轉資料歸檔與備案;建立流轉風險防范機制,制定承租主體準入條件,對進入流轉市場的經營主體進行資格審查和資信評估;進一步完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制度,穩定土地承包關系并長久不變,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高效流轉。
完善農業補貼政策。迫切需要改變當前“誰種糧誰受益”的政策目標與“誰的土地誰受益”政策實踐相背離的情況,使實際耕種者得到補貼利益的保障。各種農業補貼政策中應加大對土地流轉項目的支持,逐步將新增補貼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新型生產經營主體傾斜,這樣不僅能有效解決當前補貼政策增產效應走低問題,還能更有效地推動土地的有序流轉和農業規模經營發展。
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在當前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情況下,就不可能從根本上增強農民離土的安全感,一些農民,特別是二、三產業欠發達地區,仍然把土地作為其生活的最后依靠和保障,這不利于土地的流轉。弱化土地的農民保障功能迫在眉睫,應當將農村的社會保障由依靠承包地轉變為依靠社會保障。同時,要加大對流出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戶的就業培訓和崗位推介,引導規模經營主體優先吸納流出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勞動力,就近從事農業生產。逐步建立農村老齡人口土地經營退出機制,建立“土地換保障”的基本社會保障制度,解決后顧之憂[10]。
積極培育和扶持農業規模經營主體。強大的規模經營主體是促進土地流轉的動力。為此,應當大力培養專業農民,引導有資金、懂技術、會經營的農村各類人才受讓農戶流轉的土地,開展規模經營。支持農業專業大戶、農技推廣人員、村級組織牽頭組建農民專業合作社,擴大生產規模,實行土地規模經營。
[1] 柯福艷,徐紅玳,毛小寶.土地適度規模經營與農戶經營行為特征研究[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5,36(3)374-379.
[2] 何國俊,徐沖.城郊農戶土地流轉意愿分析:基于北京郊區6村的實證研究[J].經濟科學,2007(5):111-124.
[3] 包宗順,徐志明,高珊,等.農村土地流轉的區域差異與影響因素:以江蘇省為例[J].中國農村經濟,2009 (4):23-30,47.
[4] 張夢琳,陳利根.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資源配置效應及政策含義[J].中國土地科學,2008(11):72-75.
[5] 鐘曉蘭,李江濤,馮艷芬,等.農戶認知視角下廣東省農村土地流轉意愿與流轉行為研究[J].資源科學,2013 (10):2082-2093.
[6] 呂悅風,陳會廣.農業補貼政策及其對土地流轉的影響研究[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5(3):362-367.
[7] 陳丹,唐茂華.糧食補貼、土地流轉與農村社會保障:“三農”綜合發展視界下的政策整合研究[J].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11(6):20-27.
[8] 楊博.農業補貼政策對耕地流轉影響的實證分析[D].南昌:江西農業大學,2013.
[9] 馮鋒,杜加,高牟.基于土地流轉市場的農業補貼政策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09(7):22-25.
[10] 王瑞雪.土地換保障制度的邏輯困境與出路[J].中國土地科學,2013(6):42-48.
(責任編輯:吳益偉)
F 301.3
A
0528-9017(2015)09-1524-04
2015-07-23
國家大學生創新性實驗計劃項目(201410307060)
呂悅風(1993-),男,浙江杭州人,本科生,研究方向為土地資源管理。E-mail:lyf9352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