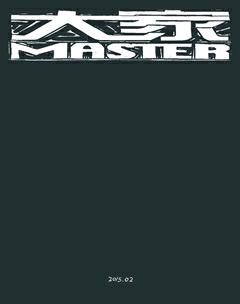電影制作更接近另一種“書寫”
婁燁+張莉
婁燁:1965年3月15日出生于北京,中國內(nèi)地第六代導(dǎo)演領(lǐng)軍人物,1993年畢業(yè)于北京電影學(xué)院導(dǎo)演系。拍攝有《春風(fēng)沉醉的夜晚》《推拿》等影片,獲戛納電影節(jié)最佳劇本獎、第64屆柏林國際電影節(jié)杰出藝術(shù)貢獻(xiàn)銀熊獎及第51屆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等六大獎項。
張莉:河北保定人,文學(xué)批評家。出版學(xué)術(shù)專著:《浮出歷史地表之前:中國現(xiàn)代女性寫作的發(fā)生》《魅力所在: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片論》《姐妹鏡像:21世紀(jì)以來的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
2014年11月18號下午4點(diǎn),在北五環(huán)邊上的婁燁工作室里,我一個人觀看了電影《推拿》,之后和導(dǎo)演婁燁進(jìn)行了三個多小時的對話。四天之后,11月22日晚,在臺北舉行的金馬獎頒獎典禮上,《推拿》獲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內(nèi)的六項金馬獎,這一晚,也被許多媒體喻為婁燁的“推拿之夜”。以下即為當(dāng)天的對談內(nèi)容。
——張莉
《推拿》提供了解決復(fù)雜問題的機(jī)會
張莉:我知道長篇小說《推拿》要改編成電影時是有些擔(dān)心的,因?yàn)殡娪笆强梢暤模な遣豢梢暤模鯓釉谝徊侩娪爸谐尸F(xiàn)“盲”首先是技術(shù)性難題,這個太有挑戰(zhàn)性了。小說沒有男女主角,每個人物的著墨也是平均的,這些應(yīng)該都是拍電影遇到的困難。
婁燁:你說得很對,這是一部關(guān)于不可視的電影,難度一開始就已經(jīng)在那了,又得讓他看到,又得不能讓他看到。還有一點(diǎn),畢飛宇(《推拿》原著作者)也和我說過,這是沒有男女主角的作品,他的小說又是散點(diǎn)透視,所有這些都是違反電影本性的,一切都不直觀。小說作品給人呈現(xiàn)的是不規(guī)則的、貌似很感性的結(jié)構(gòu)。這是很難回溯的,如果畢飛宇不告訴我,沒人會知道。他告訴我他怎樣結(jié)構(gòu)小說,這個結(jié)構(gòu)在閱讀的時候是非常通暢的,也特別能打動人,但實(shí)際上閱讀時你是完全找不到他結(jié)構(gòu)的來源的,隱藏得非常好。這些難度對我有刺激,一個人很難碰到這樣的挑戰(zhàn),它給你提供解決復(fù)雜問題的機(jī)會,這對電影制作者來說非常難得。
張莉:我看電影時,覺得你和畢飛宇是在同一個層面理解問題的,這最有意義,也最有價值。小說是好的小說,電影是好的電影。當(dāng)然,電影并不完全按小說走,也就是說,電影如果要表現(xiàn)小說里的世界,導(dǎo)演得有他自己的方式,他要找他的路徑和解決方案。
婁燁:對,就是解決方案。畢飛宇找到了很好的用文字解決這個事情的方案,而變成電影就要找另外一套系統(tǒng),這套系統(tǒng)應(yīng)該跟小說是對應(yīng)的,但它也不是拷貝,因?yàn)橥耆截愂遣豢赡艿摹_@就是我的創(chuàng)作初衷,必須要找到一個解決方案,來呈現(xiàn)小說已經(jīng)呈現(xiàn)的氣質(zhì),這是屬于電影的難題。
張莉:紀(jì)錄片形式是你尋找到的路徑之一,因?yàn)榧o(jì)錄片的方式更容易讓觀眾相信。這種紀(jì)錄片形式也包括選用盲人演員。當(dāng)然電影后面越來越不一樣,越到后來觀眾越會認(rèn)識到它是有劇情的打動人心的影片。但最初紀(jì)錄的代入感也非常必要。電影中你使用了混雜的敘事風(fēng)格,一種紀(jì)實(shí)和敘事相結(jié)合的方法。這是一開始就打算這么做的?
婁燁:我之前的工作就是從紀(jì)錄片開始,但就像你說的,說到底《推拿》還是一個劇情片,它后面會告訴觀眾,哪些東西其實(shí)是超出記錄感受的。關(guān)于盲人演員,我和畢飛宇聊過,他基本上反對我全部找盲人演員。當(dāng)時想全部用盲人演員也是沖動,后來從沖動回到一個比較正常的狀況,就決定,如果我能在盲人推拿師當(dāng)中找到所有的、特別合適的人物,我就全部用盲人拍,如果找不到,就讓演員加入。現(xiàn)在的電影是最后的結(jié)果,一個混合的陣容。
張莉:我喜歡扮演小孔的張磊,她在電影里真的很美,是那種天然的盲態(tài)的美,那種盲態(tài)是演員表達(dá)不出來的,所以這次金馬獎的新人獎提名給她真是太有眼光的事情。她在電影中呈現(xiàn)的那種羞澀完全是“天然去雕飾”,我看電影會一直看她,哪怕她是在角落里,我也會不由自主去找她。
婁燁:張磊是帶盲態(tài)的美。比如明顯的眼球顫抖,那種眼球的不穩(wěn)定也構(gòu)成了她的魅力。我是在第二周或第三周得到她的視頻錄像的,就是說她很早就被發(fā)現(xiàn)。她的形象已經(jīng)完全進(jìn)入美學(xué)層面了,你會突然發(fā)現(xiàn)她身上是存有一種所謂的美學(xué)意義的。我看過很多視頻錄像,看的時候,通常反應(yīng)就是有些人盲態(tài)特別重,會有不適應(yīng)。但看得多了我就把自己打開了,也不把自己限制在一個美學(xué)范疇內(nèi),然后,你會發(fā)現(xiàn)其實(shí)那一部分也是非常美的。在拍攝過程當(dāng)中,我慢慢體會到,我們的審美是既定的概念性的東西,但也不一定是對的。
張莉:選擇盲人演員很重要。在這個電影里,有一些盲人,比如小孔,我看過介紹,知道她本身就是盲人。但另外一些人,我不知道,比如張一光,感覺他也是挺美的。他是非職業(yè)演員,他也在你說的那個美的系統(tǒng)里面。
婁燁:電影全都用盲人演員來演是可以的,但反過來不行。就是說,如果我們這部電影一個盲人演員都沒有,那是不可能的。現(xiàn)在,我們可以理解所有人認(rèn)為的都紅的美,那是大家所謂的達(dá)成共識的美,這只是一個偶然,不是必然,僅此而已。小說里有這個結(jié)構(gòu),當(dāng)然這個結(jié)構(gòu)放到影片里面會更明確,它也躲不過去,文字一轉(zhuǎn)變成電影,所有的都是挑戰(zhàn)。電影必須直接來面對,如果解決方案是模糊的,就完全不行。
張莉:直接,說得好。一方面,電影本身的表達(dá)和呈現(xiàn)是直接的,而另一方面鏡頭和人之間也是直接的,鏡頭貼得很近,尤其是對身體的呈現(xiàn)。比如電影中王大夫和小孔,那種情人之間的身體交流,在我們所謂的正常人看來動作幅度有點(diǎn)大,會不適應(yīng)。但越看到最后就會越適應(yīng),會覺得他們本來就應(yīng)該是這樣。這個過程,你是用鏡頭推進(jìn)呈現(xiàn)的。鏡頭放大了另外一種美,另外一種肢體表達(dá),慢慢我們會覺得這很自然、很正常。
婁燁:對。更準(zhǔn)確地說,在這電影里,我想表現(xiàn)的是,盲態(tài)不是一個特別的形態(tài)。盲態(tài)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日常狀態(tài)。當(dāng)然,表達(dá)這個看法是需要一些技術(shù)引入的,就像你說的那樣。電影的宗旨就是,當(dāng)我們進(jìn)入這部影片的世界,盲態(tài)就是正常態(tài)。endprint
張莉:這是你整個拍攝美學(xué)里的一部分。這樣的理解出于一種平等意識,這使我們認(rèn)識到,盲態(tài)是和我們生活并存的狀態(tài),只不過被我們忽略了。現(xiàn)在,電影來告訴我們,這就是我們?nèi)粘I钪写嬖谥模褪侨粘#褪浅B(tài)。
婁燁:舉個例子說,有一個地區(qū)皮膚白是美的,那非洲怎么辦呢?這就是一個范疇和系統(tǒng)的差異而已,要上升到意識形態(tài)層面,就非常具有思想性了。這也是畢飛宇小說面對的一些難題,但他解決得非常漂亮。我必須跟隨作者態(tài)度,因?yàn)檫@也是我特別認(rèn)同的態(tài)度。
張莉:就是在共同理解層面上,選擇不同的方式表達(dá)。電影中,你的鏡頭是搖晃的,造成一種盲的感覺的代入感,這是最平等的一種方式,你要把小說中沒有辦法表達(dá)的東西直觀地表達(dá)出來。
婁燁:還比如大量的近景,近景是使你能看到細(xì)部,但看不到太多東西。這種視聽語言就是建立在視聽障礙的基礎(chǔ)上,是有限度的。你會感到這種限度,而聽覺是打開的。你看到的只是局部,沒有全知全能。你沒看到全景的“沙宗琪”,這就是盡量去靠近盲人的一種方式。比如說撫摸,撫摸是從局部開始的,是從局部推移的,它不是我馬上就知道全部。“看”是馬上知道全景,而“撫摸”是,先是門的面兒,然后是門的把手,它是一個逐步的過程。實(shí)際上景別的限制和跟拍,所有的對話、人物、走動,是類似于“撫摸”的。電影就是盡量靠近一種官能的感受,解決悖論問題,讓人感到有一種視覺的障礙,這可以靠近小說里描寫的盲人的感受。
張莉:在展現(xiàn)人物生活和命運(yùn)時,電影鏡頭其實(shí)是講究的,什么時候你的視角是受限的,什么時候是全知的,導(dǎo)演要考慮到。就像小說一樣。《推拿》中,要寫盲人世界時,作家也要閉一下眼,而不能全知全覺。電影中小馬和都紅聊天,沒想到遠(yuǎn)處的沙復(fù)明碰到了風(fēng)鈴,他們才發(fā)現(xiàn)原來他也在場。當(dāng)然那個場景觀眾也沒看到,觀眾也是因?yàn)槟莻€風(fēng)鈴才發(fā)現(xiàn)的,嚇了一跳。
婁燁:對,觀眾跟他們是一樣的,你不知道有一個人在聽,你跟人物當(dāng)時的狀況是一樣的。電影處理的時候,是要分場景的。我們看到小馬表掉在地上,我們超越了他的感知,這是全知,但有時候又要從人物角度出發(fā)。影片困難的地方在于,你什么時候跟他們一樣感知,什么時候你作為一個有眼睛的人,看到一些他們看不到的。這其實(shí)和傳統(tǒng)電影的制作理念實(shí)際上也是吻合的,有時候你是主觀來敘述事情的,什么時候你是高于主觀,知道事情會發(fā)生什么。
張莉:小說中寫泰來做的夢是不會有顏色的,因?yàn)樗窍忍烀と耍瑳]有色彩感;而小馬做的夢一定是有顏色的,因?yàn)樗呛筇烀と恕_@些細(xì)節(jié)創(chuàng)作者要時刻提醒自己。現(xiàn)在電影這樣處理,應(yīng)該叫“戴著鐐銬在跳舞”,時時刻刻記著這個限制。我覺得整部影片呈現(xiàn)的限制特別有意思,看電影的時候雖然有不適感,但也沒覺得那么受限,剛才,等我打開燈從工作室走出來時,我強(qiáng)烈意識到,我剛才是受限的,我經(jīng)歷了限制。影片是從身體感受層面讓人一點(diǎn)點(diǎn)意識到,小說則是通過語言來告訴讀者每個人是有障礙的。
婁燁:看小說的時候,我覺得小說作者想做的事實(shí)際上遠(yuǎn)遠(yuǎn)超出評論者所給予這個作品的理解。我認(rèn)為畢飛宇想做的事情遠(yuǎn)非一個“沙宗琪”可以概括,我們可以看到,這不僅僅是關(guān)于盲人的一部小說。
“電影實(shí)際比文字更感性,更直觀”
張莉:小說中有泰來對金嫣說她“像紅燒肉一樣好看”這個話,所有讀者都會覺得這句話有神奇的吸引力,它能準(zhǔn)確地表達(dá)情人間的愛。可是,這句話在電影里給人的震驚感沒那么強(qiáng),這是小說和電影的不同。電影的沖擊力恐怕還在于那種身體感受。這是兩種藝術(shù)形式的不同。
婁燁:電影實(shí)際比文字更感性、更直觀,我個人認(rèn)為,一部作品起作用的首先不是它的思維邏輯,它的語言首先是作用于肉體的。只有你的語言,不管是文字語言還是視聽語言,必須先到達(dá)肉體層面,然后才能作用于精神層面。跨過去是要出問題的,比如我首先讀小說,它是文字,沒問題,這就是一個生理感覺。它一下子告訴你這些事是什么樣的,這種勁兒,實(shí)際上是一種生理感受,比如現(xiàn)在我隨時能想起小說里的那些段落,那是文字帶來的肉體感受、文字傳達(dá)的生理感受,那種傳達(dá)是特別厲害的。但視聽是另一種,比如“我的血想哭”,實(shí)際上就是電影里小馬自殺出血的部分,但我不能說“我的血想哭”。還比如王大夫之后有警察來的段落,詢問他,他回答,那場戲我們也都拍了,但放到影片里我怎么覺得都不行,用語言的表達(dá)力量不夠。
張莉:你說到電影里的血,我想到小馬的自殺,王大夫那個自殘,以及沙復(fù)明的吐血,都給我非常大的視覺刺激。他們是看不見的,只有我們能看見。他們自己感受不到嚴(yán)重性,那種反差非常奇怪。還有電影最后,一群看不見的人從飯館里跑到街道上,去打車。他們看不到,打車變得很困難,我相信那個鏡頭會讓很多觀眾內(nèi)心感傷。
婁燁:原小說中他一進(jìn)門就吐的亂七八糟的,但他自己不知道。從小說來說,那是一個最實(shí)際的狀況。那天正好是南京的大雪,那是一個困境。
張莉:沙復(fù)明讀的那些詩,是小說里特別迷人的一部分。推拿房是狹窄的,但因?yàn)閷γ赖腻谙牒挖は攵_闊了,但我們也感受到他的障礙。電影里也表達(dá)那種盲人世界的障礙、受限,但用了另外一種方式,摸都紅的臉,“我想知道什么是美”。那個場景更及物,跟電影的語言是最貼的。沙復(fù)明最后朗誦詩的片斷特別有意思。那是誰的詩?我覺得很多意象很熟悉,應(yīng)該也不是好詩,在那個場景里非常恰切。
婁燁:電影里沙復(fù)明念詩,更靠向一種幽默、戲謔的方式。那詩出自網(wǎng)絡(luò)被改編的,可能出自于三毛,和一個歌詞,混在一塊兒的,是一個混雜的文本。因?yàn)橐仙硰?fù)明嘛,沙復(fù)明要是直接朗誦一個“艾略特”那就麻煩了。
張莉:沙復(fù)明相親那個場景,小說里不是這樣。但我覺得改編得挺有意思,那種生活的質(zhì)感出來了,那種啼笑皆非、哭笑不得的東西很有意思。他是典型的偽文青。畢飛宇小說中的幽默感在這個人物身上很好地呈現(xiàn)了出來,這個人很古怪但又很好笑。
婁燁:他就是典型的偽文青,帶有一種向往主流的意思。這種向往主流使電影里的沙復(fù)明成為雙重的人,他向往所謂正常人的世界,向往有錢人的生活。影片當(dāng)中沙復(fù)明必須承擔(dān)畢飛宇小說當(dāng)中幽默的因素。讀小說時,我有這種感受,就是很多人物寫到真實(shí)還原的狀況時你反而認(rèn)為那個不是人物本身了,它會有一個輻射性,沙復(fù)明這樣的人物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很多的。夠又夠不上,你又瞎湊什么呢?其實(shí)就是夠不上主流,也夠不上社會狀況的階層,但他又想扮演。因?yàn)樗J(rèn)為主流價值觀是這樣,被認(rèn)可就是這樣。一旦小說介入到人物內(nèi)部,它就會有一種擴(kuò)張性,原小說有這樣一種力量。這種力量讓你認(rèn)為《推拿》是一部社會小說也可以,這是小說特別有意思的一個部分。endprint
張莉:我喜歡張一光在洗頭房里吹笛子的場景。那個笛子聲真好聽,在這樣的音樂中,我們可以看到更大的一個層面,殘酷的生活以及人的命運(yùn)。那個音樂是特別創(chuàng)作的吧,我想這是你很得意的橋段。
婁燁:笛子聲伴著那個畫外音:“實(shí)際上盲人比健全人更了解什么是命,命是看不見的,盲人也是看不見的,所以更了解。”是我很得意的段落。如果你在電影院看就會更有感覺,因?yàn)槟莻€鏡頭是360度的旋轉(zhuǎn)鏡頭,然后那個笛聲環(huán)繞整個電影院轉(zhuǎn)了一圈,帶著命運(yùn)是看不見的這句話,哪怕是語言修辭,它也是合理的;哪怕事情不是這樣的,但語言上就是這樣的,于是乎你必須接受。
張莉:這是你電影要落的一個點(diǎn),有說服力,也不牽強(qiáng)。它是抒情的片段,也有隱喻性和象征性。
婁燁:那些話來自小說,這些文字是你駁不倒的,“命是看不見的”,很厲害的一句。我讀小說的時候會摘出很多我特別喜歡的句子,這些句子有時候是很難放進(jìn)電影里去的。這個小說的特殊性在于語言方面特別精彩,我要把它完全轉(zhuǎn)化成視聽,必定會丟掉屬于它的氣質(zhì)的東西,這個有些可惜。畫外音,可以讓人知道這是一個關(guān)于聽的電影,聲音優(yōu)先的姿態(tài),同時也希望能保持一些厲害的、準(zhǔn)確的畢飛宇語言,這是我特別希望的。
張莉:演小馬的黃軒很帥氣很明亮,演員選得特別合適,本來小說里小馬就是很可愛的人。他也算是整個電影角色里最閃光的。他的“復(fù)明”,在電影中亦真亦幻,電影最為出色的地方,這個處理小說里不必有,但在電影里應(yīng)該有。
婁燁:所有人都喜歡小馬這個人物。“復(fù)明”這個設(shè)計,是挺困難的悖論,我們很多爭論也與此有關(guān)。你也可以把它理解為小馬的一個夢,在都紅斷指之后你會發(fā)現(xiàn)小馬突然醒了,他去開燈。這些文字都是對復(fù)明段落的一個質(zhì)疑,整個復(fù)明段落是一個虛擬的、假設(shè)的可能性,但通過這個可能性你才能進(jìn)入那個世界的內(nèi)部。我們把這一段叫做“黑暗中行走”,原來叫“復(fù)明段落”,后面覺得這個說法更接近。音樂的宗旨整個就按照“黑暗中行走”設(shè)計,由小馬的可能性把所有人帶入他的世界。那個世界是未知的,我們也不想把它落在實(shí)處,因?yàn)轱@然也不合適。用攝影機(jī)來還原他們頭腦中的世界,是一個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務(wù)。我們只是在可能性層面工作,這個“復(fù)明段落”是可能性范疇,這就是后面為什么要有驚醒,有亦幻亦真。這樣會對整個“看見”“ 看不見”有更廣義的理解,實(shí)際上畢飛宇的小說也正是在說看見和看不見中間的那個世界。他在說交接點(diǎn)上的事,而這個交接點(diǎn)是雙向,是雙刃劍,是對看得見的世界和看不見的世界的雙面評價。
張莉:“黑暗中的行走”照亮了整個電影,我看到這里非常驚喜。這是小說沒有的東西,但又拍這么貼合。看電影到后面,心里開始變得溫暖,哪怕是假的不是真的也沒關(guān)系。包括小馬和小蠻的相見,我甚至認(rèn)為這是主創(chuàng)的一個祝福,是帶著光的、特別感動的一個處理。因?yàn)檫@個處理,我認(rèn)為現(xiàn)在的婁燁和以前的婁燁變得不一樣了。
婁燁:這個可能性段落里有一個必然性,就是停電。電影里停電時,整個電影院將會是黑的,放映的時候觀眾會感覺是不是真出事了,因?yàn)楫嬅婧吐曇粢捕际峭蝗粩嗟摹H绻f前面是可能性,現(xiàn)在的黑就是有眼睛的必然性,因?yàn)橥k姡_實(shí)看不到了,然后鏡頭會再回到他們的世界。可能性和必然性在結(jié)尾實(shí)際上也重復(fù)了一下,但我覺得還是比較樂觀。觀眾理解成光明結(jié)尾也可以,我不排斥。我很同意你說的“祝福”,這樣理解我很認(rèn)同。
張莉:我想說的也不是光明,而是一種很模糊很曖昧的光暈。我認(rèn)為小蠻就是小馬的光暈。在最后,電影給了一些光亮,觀眾的情緒也得到釋放,在這之前我看電影一直是受限的,心里是壓抑的。但從放映室走出來,我的內(nèi)心是有一些溫暖的。我想,從電影院出來,觀眾也會有這樣的心情。這個很好,我覺得小蠻對于小馬具有身體的意義、光的意義。
婁燁:身體的意義,你說得很準(zhǔn)確。所以,為什么要減弱身體陪伴的段落呢?這樣的身體陪伴需要保留,不管是盲人還是健全人,人生都需要一個陪伴。這個陪伴我們可以理解為目光,這是畢飛宇小說里的詞,也可以理解為是身體存在的感受。陪伴的意義要遠(yuǎn)大于看見或者看不見的二元評判。嫂子的身體和小蠻的身體,對于小馬來說,嫂子是“倫理”,小蠻是“道德”。這個電影使你拋開這些,這首先是一個陪伴。這個陪伴是任何人都需要的。
張莉:電影表現(xiàn)了小馬的孤獨(dú),身體的孤獨(dú),它直觀地使用了身體,用身體表達(dá)向往。小說當(dāng)時處理時會考慮道德的層面,電影里顯然也考慮到。小說中小馬是非常純潔的存在,在電影里也是,不管他做什么,觀眾就覺得他很純潔很可愛。這也沖破了很多界限,我們對普通的道德的理解發(fā)生了變化。這個電影的拓展意義也包括這個,可能不是有意,但我覺得你和畢飛宇都共同有這樣認(rèn)識。
婁燁:那段畫外音“故事是假的,假的好玩,小蠻根本不管這些”很有意思。我們應(yīng)該重新理解我們所處世界的規(guī)則,因?yàn)榭措娪埃銜肋@個規(guī)則在“沙宗琪”是會變的,這是我和畢飛宇共同要提醒的。因?yàn)槲覀冇H身親歷了這個變化,所以不要覺得規(guī)則是可以貫穿到每個角落的,只是到了一個小小的推拿中心,有些規(guī)則就已經(jīng)完全崩潰。
張莉: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小馬和小蠻激情戲之后,我們看到綠色的樹葉,看到雨滴。觀眾感受到身體所帶來的歡愉,生命本身的美好。一方面是身體感受,另一方面是生命感受,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樣的,包括樹、烏龜、綠葉啊,我喜歡那些鏡頭,很美。
婁燁:小馬重新沐浴陽光了。那一切對小馬來說就是驚喜,生命的驚喜。我們看到了烏龜,看到了游來游去的魚,可烏龜能看多遠(yuǎn),魚又沒有視力,但這又怎么樣?它就是意義,生命的意義。
張莉:這樣的鏡頭太婁燁了。這是今天的藝術(shù)家,在今天這個時代和這個社會真該有的理解力。小說《推拿》本身也是關(guān)于身體的小說,它可以提供我們理解世界的很多角度,我們從這小說里感受到身體,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整個人類。
婁燁:對!有人說這是一個有社會意義的《推拿》,我認(rèn)為這句話對小說和電影的闡釋沒意義,這意義只對評論者有用。你看到社會意義,但它和生命意義是平等的,不存在高低,我相信畢飛宇也同意這個判斷。endprint
張莉:雨是這部電影很重要的意象。小說里沒有,但你用了,人的情緒、生活狀態(tài)、憂傷,所有那些東西全部在雨這個意象中呈現(xiàn)出來了。兩個盲姑娘小孔和金嫣的擁抱的也是有雨的。是你到了南京決定這么做的嗎,還是即興的?你以前也愛用雨。我覺得有寫意的感覺,算是一種烘托,觀眾能感覺到電影要傳達(dá)的東西。
婁燁:很多人說我的每部片子都要有雨,這也是我的喜好吧。但每部片子的雨是不一樣的含義,這部片子中,雨更多的是聲音和身體的感受。雨只有落在盲人身上,才能感受到,才能聽見,這是一種特別直觀的癥候。雨可以體現(xiàn)出小馬的欲望,但更多的,還是接近于書法、中國畫的那種情境,也類似于留白,很空,卻是說不清。
張莉:我覺得雨是大自然一部分,包括雨滴滴在樹葉上,是渾然天成的。雨與萬物生長有關(guān),是一種對待生命的態(tài)度。結(jié)尾處,我們聽到了那首歌,這首歌我以前沒聽過,很好聽,歌詞也好。我還聽到了“我們坐在高高的谷堆旁邊”那個音樂,很抒情,又是你很喜歡很得意的處理。
婁燁:對,雨是對生命的肯定態(tài)度。小蠻和小馬做愛了,這是樂觀的生命態(tài)度。那個歌曲我很得意的。這首歌是堯十三的,他是很年輕的民謠歌手,這首歌叫《他媽的》,結(jié)尾就用了那個旋律,我特別喜歡,歌詞也很有意思,關(guān)于吃眼睛的故事,他說我愛的姑娘在一點(diǎn)一點(diǎn)吃掉我的眼睛,那種意象非常適合這個影片,我就用了。
“拍《推拿》之前和《推拿》之后的我是完全不一樣的”
張莉:表現(xiàn)盲人身體的障礙相對容易,但觸及到盲人精神上障礙則是困難,這是電影最重要的點(diǎn)。當(dāng)你在敘述障礙時,你主要表現(xiàn)精神上的窘迫。電影傳遞給我們盲人在精神生活時所遇到的窘迫。
婁燁:現(xiàn)實(shí)生活里我們做過調(diào)查,在推拿中心工作的盲人比較熟悉工作環(huán)境,這是一個真實(shí)情況。所謂他生活的障礙,其實(shí)也是在他熟悉的生活范疇之外的障礙,比如出門、比如打車、比如到另一個陌生空間。其實(shí)你從更高的理解層面上來說,這和我們也沒什么區(qū)別,抽象講是完全一樣的。所以盲的概念就被改變了:你看不見東西你不知道,但你看見東西又能知道多少呢?這是在讀小說時我就產(chǎn)生的問題,尤其往后讀,因?yàn)榍懊嫠堰@些問題都解決了,你已經(jīng)進(jìn)入這個“沙宗琪”世界了,于是你不會去問毛巾在哪、牙刷在哪,這是漸進(jìn)的過程,在電影里全都存在,同時拍攝過程更詳細(xì)。比如早上上廁所怎么排隊、怎么敲門,男的到女的房間怎么走,所有的都必須建立起來。電影是截取,兩小時你不可能展示全部的生活,但截取片斷必須來自完整的生活過程。整個過程都記錄,再截取,電影才會有真實(shí)感。
張莉:我看到小孔和小馬初次見面那種夸張的動作時,很震驚,小馬那種行為在正常人看來是非常過分了,小孔男朋友就在旁邊,可又是看不到的。看這種畫面,會更深刻理解什么是障礙。電影給的這個真是直觀。
婁燁:我是按照小說來做的,讀小說我能想象出這些畫面,小說變成畫面,差不多就是這樣。這是很有挑戰(zhàn)性的,你可以理解成“猥褻”,但這不是,這恰恰是很有意思的。還比如說小孔和王大夫的戲,它會挑戰(zhàn)一些既常的規(guī)則,但在他們的世界里也是順理成章的。他們有充分的理由,因?yàn)樗麄兛床灰姟Q過來,我們那么做就不行。這個對應(yīng)關(guān)系就很有意思,從社會學(xué)上說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課題。我們怎么解釋這個優(yōu)劣、上下,或者所謂的道德邊界在哪里?畢飛宇最重要的是呈現(xiàn)了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是要改寫你的頭腦的,如果你能接受這個小說、這個電影,你可能也會接受類似的事情。《推拿》不僅是關(guān)于盲人推拿師生活的一個小說。
張莉:看過電影或小說《推拿》的人,看世界的角度是不一樣的。看小說之前和看小說之后,對世界的理解也是不一樣的。畢飛宇在一次接受訪問的時候也說,自從他開始寫盲人,他看到了更多的盲人、盲道和殘疾人設(shè)施等等,他發(fā)現(xiàn)自己打開了認(rèn)知世界的方法。
婁燁:寫《推拿》,作者是第一個受益者,第一個感受變化的就是作者本身。借用你剛才的句式,我們可以說,寫過《推拿》和沒寫過《推拿》的畢飛宇是不一樣的。我也一樣,拍《推拿》之前和拍《推拿》之后的我也是完全不一樣的。很多做過《推拿》的工作人員受益匪淺的,收獲了比拍一部電影要多得多的東西。拍完《推拿》,我和寫完《推拿》的畢飛宇的感受是一樣的。
張莉:電影中,小孔對高唯說“這個世界上,眼睛是有分工的,一部分眼睛負(fù)責(zé)看到光,一部分眼睛負(fù)責(zé)看到黑”,也是小說的主題。畢飛宇在談話中,也不斷提到這個,電影把它移植進(jìn)來很好。
婁燁:黑暗能阻止所有有眼睛的人,絕對阻止不了盲人,你可以理解這個話是帶有象征意義的。畢飛宇的文字上有很多通感的東西,你會發(fā)現(xiàn)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在這里比比皆是;但也不是,他把情調(diào)的東西刪了,直接就是荷塘,直接就是荷葉。因?yàn)楫咃w宇是今天的作者,他不可能和今天沒有關(guān)系,他的小說寫法就是延續(xù)過去和傳統(tǒng)的一個做法,用這樣的做法,呈現(xiàn)今天和當(dāng)下。我也希望有這樣的一種對應(yīng),我要講述的是今天的和當(dāng)下的,而不是幾十年前的。
張莉:電影和小說的共同特點(diǎn),就是有一種抵達(dá)本質(zhì)的能力,能撥開云山霧罩。要在這個層面上理解《推拿》。當(dāng)有人說這是一個溫暖的小說、一個溫暖的電影時,這是一個文藝腔的表達(dá),這是先入為主的表達(dá),是需要商榷的表達(dá)。小說和電影的不凡是完全沒有那種偽飾,它看到生活的殘酷,同時也能看到精神上的東西,看到黑暗也看到光明,看到暖也看到冷,這是藝術(shù)家應(yīng)該有的對生活的理解。
婁燁:正是這個原因,使我沒法用一個廣播電臺的播音員來讀這個對白。這也是一種態(tài)度,一種對生活的理解。
張莉:從最初發(fā)表到現(xiàn)在,我發(fā)現(xiàn)人們對《推拿》的理解,也包括畢飛宇自己,有一個不斷深入的過程,他自己也在不斷思考。在最初,他強(qiáng)調(diào)平等和尊嚴(yán),其實(shí)對限度的理解早已經(jīng)在小說中了,但當(dāng)時他是不談的,后來在茅盾文學(xué)獎獲獎詞里,他提到了。小說剛出版時,我們也能感受到它的隱喻性和象征性,但畢飛宇拒絕使用象征或隱喻的說法,他說他不想利用他的寫作對象。endprint
婁燁:我非常理解,他當(dāng)時是不能談的。這是一部關(guān)于障礙的小說,這樣的話在寫作最初是不允許出現(xiàn)在他的頭腦里的。也就是說,所謂象征主義是不允許象征的,隱喻是不允許用隱喻的,就是這樣一種互為的關(guān)系。他的拒絕我也完全認(rèn)可,而且我認(rèn)為他這樣做特別優(yōu)秀。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專門為象征或隱喻工作的作品是沒什么價值的。
張莉:2008年大地震時,我們身邊多了很多殘障人士,當(dāng)時電視臺對待殘障人士的方式,畢飛宇很不滿。在一個采訪里,他解釋說,看過《推拿》的人都會很敏感這一點(diǎn),更何況他是作者,一定會自然地站在都紅的視角去想問題。
婁燁:只有他寫過,他才會說出類似于“我們跟盲人是平等的,但同時就是不平等的”,這些話只有作者才能說出來。比如“盲人是平等的,不需要過度同情,但盲人是需要幫助的”,只有他處理過這種格局的、帶有未知邊界的那種題材之后,他才能得到類似很多這樣的信息。我很認(rèn)同這種態(tài)度,也很尊敬這種態(tài)度。
張莉:作為讀者和觀眾,《推拿》的小說和電影的合作在我眼里是棋逢對手、旗鼓相當(dāng),就像一個種籽里長出兩個兩棵并肩的大樹,互有不同,但又緊密相關(guān)。
婁燁:對,改編就是兩個作者的對話。最重要的不是留取小說什么部分,重要的是你是否和小說作者在同一層面上對話。如果在一個層面,就會很有趣;如果岔開,就很困難。
“沒有櫻桃的蛋糕是不漂亮的”
張莉:我發(fā)現(xiàn)你講電影時,會很自然講到那些傳統(tǒng)的東西,你是想把這樣的東西融進(jìn)去。
婁燁:《推拿》整個創(chuàng)作過程靠近中國傳統(tǒng),就是特別根上的傳統(tǒng),這是我的感覺。它不是太在乎邏輯性的結(jié)構(gòu),它是從一個局部到另一個局部,從一個桌子到另一個桌子,從一個人到另一個人,這種方式你可以說是一種盲的方式,“摸象”的方式,但具體的象是什么樣他有興趣。這實(shí)際上反而充實(shí)了很多東西,恰恰在這些細(xì)節(jié)運(yùn)行的過程中你得到的細(xì)節(jié)更多,想象更本質(zhì)。這是小說給我們帶來的。
張莉:我為什么一看完電影就告訴你,電影中有身體感呢,我覺得,《推拿》就是使用鏡頭對人身體和感官進(jìn)行的“推拿”,電影在幫助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的時候使用了身體。你剛才說水墨啊、山水啊、寫意啊,大的角度講,它們和推拿是同一類的詞,與古代中國有關(guān)。
婁燁:理解方式也是一樣的,經(jīng)絡(luò)、脈絡(luò)、穴位,這些更接近于中國繪畫和文學(xué)。電影整個節(jié)奏更靠近于寫意節(jié)奏,而不是一種故事邏輯節(jié)奏。原作也是這樣,小說是一個長卷式的書寫,整個影片的剪接也是按這樣一種方式進(jìn)行的,這樣的剪接是可以修改的。筆墨落下就不能改,如果你要改就要圈一個,類似于顏真卿的《祭侄稿》,它有修改和涂改,因?yàn)樗窃试S涂改的。實(shí)際上后期剪輯的時候就像攤開《祭侄稿》,那么你看,這是可以修改的。就像書寫一樣,單個字是往左偏的,另一個字必然向右找平衡,這是逐步尋找和校正的過程。
張莉:最初看電影的時候,會以為你要拍成紀(jì)錄片,但最后發(fā)現(xiàn)不是,但又覺得前面的部分是必須的。一開始要有生活的質(zhì)感,讓觀眾確信所有一切都是真的,要用紀(jì)錄的方式;然后慢慢進(jìn)入,整個電影看起來也沒有戲劇性,仿佛是反戲劇性的,但它其實(shí)是戲劇。這些都是你要追求的東西吧?
婁燁:這實(shí)際上就是我閱讀原小說的感受。它有很大的戲劇性,也有很多紀(jì)實(shí)的。關(guān)于盲人生活,比如王大夫一進(jìn)門一定會先拉一下那個床,看看那個床是不是被固定上的,這是細(xì)枝末節(jié),我們真的把那個床釘上了。細(xì)枝末節(jié)有非常寫實(shí)的部分,也有非常寫意的部分,是直白的寫意,以一個真實(shí)人物說出來的寫意的話,這在閱讀中居然成立,這是一個特別大的驚喜,但你挑出來用在電影里是不可能成立的。你在閱讀那個段落的時候你會覺得特別感動,這就是畢飛宇語言的力量,他的語言隨時可以離開寫實(shí)層面,這個實(shí)際上是很不容易做的,也很難在電影里對應(yīng),必須找到另一個系統(tǒng)。如果說“我的血想哭”是小說中間對白的寫意,那么手拉手實(shí)際上是行為的寫意。
張莉:我認(rèn)為《推拿》是你拍攝生涯中水到渠成或者命中注定的一個電影。你先前對電影的各種嘗試非常成熟地用在這里,你的思考,你對身體的理解,你對攝影技術(shù)的運(yùn)用,你對人類限度的理解,全部都放在這里,而且是如此貼合。如果你沒遇到以前的那些電影,如果沒有以前的嘗試,拍《推拿》時也不一定能這樣呈現(xiàn)。我聽到你要拍這個電影時我覺得婁燁真的很厲害,他居然要選擇這樣一個很中國的、很寫實(shí)、很當(dāng)下的,跟你之前那種很先鋒很實(shí)驗(yàn)的不太一樣。看了電影又覺得,這個電影還是“婁燁”的,很實(shí)驗(yàn),很先鋒。
婁燁:對,這個電影對于我來說就是很先鋒的。我讀到《推拿》的時候特別吃驚,小說居然都寫到這份兒了,它非常先鋒、非常實(shí)驗(yàn)。所以要感謝畢飛宇,我遇到了這個小說。這是反電影的一個電影。這個反電影是由畢飛宇決定的,如果它變成電影,一定是反電影的電影。
張莉:柏林電影節(jié)給《推拿》頒發(fā)的杰出藝術(shù)貢獻(xiàn)獎是實(shí)至名歸,放在世界范圍內(nèi),也是非常先鋒和實(shí)驗(yàn)特色的。
婁燁:這個電影是個挑戰(zhàn),使你必須選擇一個解決方案。當(dāng)然,這個解決方案和地域有關(guān),跟具體作者有關(guān),這是沒辦法的。所以實(shí)際上從這個角度理解,這個解決方案是比較靠近中國化的。它是在這塊土地上的一個故事,解決方案肯定得從身邊找,不可能找一個19世紀(jì)教堂什么的。
張莉:這部小說的主題有一種普遍性,這有利于二度創(chuàng)作。去年我去臺灣訪問,九歌出版社的總編告訴我們,《推拿》比《平原》《玉米》更受歡迎,雖然后者寫得也很棒。一般小說賣1000冊就很不錯了,《推拿》在臺灣已經(jīng)賣出了5000冊,是非常了不起的數(shù)字。我們問為什么?她說是小說的魅力,因?yàn)樾≌f對人的理解,對人的限度的理解,這些話題是沒有地域、沒有語言、沒有語境障礙的。
婁燁:對人的理解、平等啊這些,是人類共同關(guān)注的,但我覺得整體上這部片子或這部小說更適合中國語境或亞洲語境。從小說的語言到電影的語言,我覺得《推拿》更適合亞洲的語境。這就是我認(rèn)為為什么有些語言是不可以翻譯的。有些語言系統(tǒng)你是很難使用的,在一些區(qū)域。比如在好萊塢的語境并不適合中國的狀況,比如新浪潮的語境也不一定適應(yīng)中國的狀況。恰恰相反,日本社會派電影和小說,反而更適合中國的語境。endprint
張莉:我看前幾天中國電影資料館舉辦了“婁燁電影展”,有許多朋友排隊買票,隊伍很長。其實(shí)你是中國導(dǎo)演界特殊的導(dǎo)演,你沒有那么多的票房紀(jì)錄,但資深影迷和粉絲眾多。畢飛宇有一次跟我說:“即使其他導(dǎo)演把蛋糕分完了,老天爺一定會把蛋糕上的櫻桃留給婁燁。”說得很好。“蛋糕”現(xiàn)在對你有困擾嗎?
婁燁:應(yīng)該說,沒有櫻桃的蛋糕是不漂亮的,我們先不說去分吧,蛋糕上一定要有一個或幾個櫻桃存在。我很幸運(yùn),我只拍了3部影片,在內(nèi)地上映,通過影檢,我拍了將近9部片子。大概有6部是誰都不認(rèn)的,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我擔(dān)心就此為止了,沒人給你投資。做《春風(fēng)沉醉的夜晚》緩過來,雖然還能繼續(xù)拍電影,還能回來拍電影,還能有《浮城迷事》。這個行業(yè)的體系更新是特別快的。沒想到我依然能活著,我覺得很幸運(yùn)。
“電影是一種身體感受”
張莉:我覺得你的鏡頭使用和之前的第五代導(dǎo)演特別不一樣。我們能明顯感覺到他們對燈光的使用,是很唯美的,但在你的電影里是相反的,它是很蕪雜的。你的鏡頭里包含的東西特別多,甚至是矛盾的東西,包括你說過的錯誤的東西,也有。這是你對世界的看法嗎?
婁燁:從電影史來說,60年法國新浪潮之后,已經(jīng)沒有所謂錯誤的語言了。整個世界電影史特別短,它已經(jīng)犯了所有的錯。新浪潮后它把所有的錯融到新的語言里,所謂焦點(diǎn)不實(shí),機(jī)器晃動,手持?jǐn)z影機(jī)的不穩(wěn)定性,所有這些在之前都被認(rèn)為是錯誤的,在之后成為一種通常的語言。從這方面說,電影語言是快速發(fā)展的語言,它快速容納了很多綜合因素,它在不斷地反,反自身。這個演進(jìn)過程非常快,因?yàn)槎嘈畔⒘康耐ǖ溃娪暗目赡苄宰兊脦缀螖?shù)字地往外走,加一點(diǎn)聲音它的含義就不一樣。它的語言的不穩(wěn)定性越來越擴(kuò)散,你很難用固定的美學(xué),比如光線,這是非常困難的。如果和技術(shù)性、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系發(fā)生耦合,就更難斷定了。西方電影的光線是特別好的,比如巴黎、柏林會有這些調(diào)子,但在印度就很難實(shí)現(xiàn)。如果你要用這樣的光線做一部印度電影,那就可笑了。
張莉:你的電影語言有極強(qiáng)的識別性,很多評論提到法國新浪潮電影對你的影響。你是有意識地把這種電影美學(xué)移植到中國來的嗎?
婁燁:從電影史角度,60年代的法國的新浪潮實(shí)際上來自于對20年代的美國黑色B級片的學(xué)習(xí),而后來80年代美國的“新好萊塢電影”又是對60年代法國新浪潮電影的學(xué)習(xí),這很有意思。每一次學(xué)習(xí)都會在不同的地方形成新的電影方式,比如日本、韓國等等,但前提是解決方案需要自己來找,無論是法國新浪潮、歐洲作者電影,還是美國黑色類型片,其實(shí)都幫不了中國電影,我們需要從自己的生活中找到解決方案。
張莉:80年代中國文學(xué)中出現(xiàn)了“先鋒文學(xué)”,畢飛宇是在其后出現(xiàn)的,但他強(qiáng)調(diào)他受到了先鋒文學(xué)的影響。我想,如果你是一位小說家,你的小說會與先鋒文學(xué)的敘事風(fēng)格會極為相近的。你電影里的先鋒性和實(shí)驗(yàn)性是全部源自法國新浪潮嗎,會不會也與中國的先鋒文學(xué)有關(guān)?
婁燁:我不是特別了解“先鋒文學(xué)”,我倒是跟畢飛宇討論過“翻譯問題”,就是很多當(dāng)時的小說語言像是翻譯語,這是當(dāng)時中國作者大量閱讀西方翻譯作品的結(jié)果,以至于自己的寫作也像受到翻譯語的影響,而那個“翻譯”本身可能就已經(jīng)有誤了,我們當(dāng)時討論的是這樣會對整個中國文學(xué)有什么樣的影響。其實(shí)不光是文學(xué),美術(shù)、電影都是,其中最落后的是電影,到今天仍然在使用西方的過去的語言方式在拍今天中國的故事。
張莉:我是這樣理解的,你在尋找你的方法,你通過這種搖鏡頭、省略一般意義上的敘事時間,不按一般意義上的邏輯進(jìn)行敘述,建立了你自己對世界的理解,或者,你可能想傳達(dá)的是,這就是你理解的人或者事件。這樣的人和事件并不一定像其他藝術(shù)家理解得那么完整、那么邏輯嚴(yán)密。你有一句話叫“我的攝影機(jī)不撒謊”,你怎么理解這句話?
婁燁:最關(guān)鍵的是搖鏡頭、省略等等這些語言方式如果在半個世紀(jì)以前還是一種個人方式的話,在今天其實(shí)已經(jīng)不是什么“個人方式”了,而是“眾人方式”。試想一下你拿起手機(jī)想拍下一些你感興趣的東西的時候大概情況就是這樣吧,而且你也不可能完全排除鏡頭的晃動,所以這實(shí)際上是一個今天隨時發(fā)生的“視覺語言”。這種語言的方式是以記錄并且保存某種“真實(shí)證明”為前提的,你好像在說,你看我沒有騙你,這是攝影機(jī)的不撒謊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攝影者其實(shí)有權(quán)力事先決定它所“截取的真實(shí)”,就是他可以選擇怎樣來拍攝這個真實(shí),這就是攝影者的撒謊的一方面,因?yàn)閿z影機(jī)是有人操縱的,所以影像本身從一開始就是有一種悖論在那里。所以說攝影機(jī)可以客觀真實(shí)記錄現(xiàn)實(shí)并不準(zhǔn)確,如果能夠做到是因?yàn)閿z影機(jī)背后的人的作用。
張莉:很同意你說的,所謂完全客觀的真實(shí)是不存在的。但鏡頭的使用是不是跟一個人對生活的理解有關(guān)系?它表現(xiàn)的是創(chuàng)作者怎樣去看去理解他所在的生活,跟小說家的語言是一個道理。
婁燁:鏡頭怎么記錄,機(jī)器怎么來拍,每個導(dǎo)演都不一樣。這可能跟一個人的審美有關(guān),可以這么說。比如我認(rèn)為女孩沒事不用化妝,這部片子里盲人更不可能化妝,更不可能有很復(fù)雜的發(fā)型,一切都要從這個出發(fā)。現(xiàn)在,我看上去特別漂亮的東西,別人一看嚇一跳。我有時特別著迷他們那種盲態(tài),真的很美。比那些整過容的表情要好看好多。
張莉:同為第六代導(dǎo)演中的代表人物,你和賈樟柯的不同在于,你并不關(guān)注那些我們都看到的社會變動,而是關(guān)注人與人之間親密關(guān)系的變化,確切地說,是人的欲望和情愛。我認(rèn)為你所有的電影都在試圖表達(dá)你對人的欲望和情愛的理解。當(dāng)然,這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封閉的角度,你用不同處境的人來表達(dá)你的理解,很深入,很有力,也別開路徑。比如余虹的愛情,那是大時代政治在一個青年身上打下的深刻烙印。比如《春風(fēng)沉醉的夜晚》中的愛情,那是同性之間的吸引。《浮城謎事》里則是金錢化時代人際倫理的一種變形。還比如《推拿》中黑暗中的愛和欲。愛情和欲望,在你電影里,不只是關(guān)于單純意義的欲望,還有事件時代政治的變形和折射。我覺得,把你所有的電影作品放在一起,是你關(guān)于對愛情和欲望的一個長篇小說,或者長篇敘事詩。“欲望和情愛”是你一直關(guān)注的嗎?
婁燁:欲望和情愛實(shí)際上是一種身體感受,我確實(shí)認(rèn)為這樣的來自于身體的感受是很難騙人的,它有一種真實(shí)性在那里。比如你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時候,首先出現(xiàn)的是一種人的身體反應(yīng),憤怒、委屈、想哭等等,所以,從某種角度說,自由、民主、公平、公正實(shí)際上首先是一種身體反應(yīng),而不是一開始就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選擇。否認(rèn)或阻斷這些人的本能的身體反應(yīng)實(shí)際上是非常困難的,方法不是很多,比如說謊言(極權(quán)時代的欺騙),比如說用另外某種更強(qiáng)烈的身體感受去掩蓋(納粹的美學(xué)方式),而另一方面對頭腦和思想的限制也首先會從身體限制開始,比如說監(jiān)獄。這也就是為什么說政治實(shí)際上是一種身體感受,而有意思的是碰巧的,電影也是一種身體感受。
張莉:前面談拍《推拿》的藝術(shù)處理時,你提到顏真卿的《祭侄稿》,我也由此想到你電影中的那些嘗試,比如在電影畫面上刻印郁達(dá)夫小說的文句、朱自清的散文等,可以想見你對中國文學(xué)的熟悉,這使你的電影有一種深厚的文人氣息。你是特別少有的有文學(xué)氣質(zhì)的中國導(dǎo)演,非常寶貴。
婁燁:電影是一種多通道傳達(dá)的媒體,這一點(diǎn)從一開始就決定了電影與多種藝術(shù)門類的聯(lián)系,有人說過,真正的電影是在電影以外,大概也就是這個意思吧。另一方面,電影看似來源于一個“西方”系統(tǒng),但其實(shí)很多方面更接近中國傳統(tǒng)對藝術(shù)以及語言的理解。比如電影實(shí)際上是一個時間優(yōu)先的系統(tǒng),這一點(diǎn)就很接近中國傳統(tǒng)繪畫和書法,因?yàn)楣P墨就是有時間性的,它強(qiáng)調(diào)一氣呵成,強(qiáng)調(diào)時間順序的推演,強(qiáng)調(diào)目的模糊性和變化等等。從這個角度看,電影的制作更接近一種“書寫”,而這其實(shí)與顏真卿寫《祭侄稿》、郁達(dá)夫?qū)憽洞猴L(fēng)沉醉的夜晚》以及畢飛宇寫《推拿》是一樣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