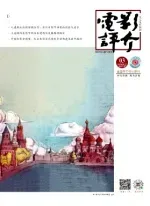西方電影中的“上海印象”
潘紅英

電影《面紗》劇照
中國,作為一個蓬勃向上的新興發展中國家,其經濟、文化開始向全世界輻射,特別在經歷了2008年奧運會的輝煌、2009年順利度過金融危機、2010年成功舉辦世博會以后,中國頂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光環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國際眼光。隨著中國電影票房進人百億時代,國際社會對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方文化愈發感興趣,一大批以中國元素為主題的影視作品紛紛亮相,甚至不少西方電影拍攝都把取景地瞄向了中國上海。
一、“十里洋場”的誘惑
上海和中國電影的誕生發展有著不解之緣。自從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園內“又一村”第一次放映西洋影戲以來,上海便成為了中國電影的發源地。19世紀末開始,美國、法國等西方國家意識到中國這片還未開墾的電影市場處女地,他們通過拍攝影片、特許放映、投資影院、創立公司等途徑,逐漸擴大西方電影在中國的勢力。他們除了將放映地從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延伸到中小城鎮之外,還將拍攝點瞄準了中國的大城市,尤其是當時被譽為“十里洋場”的上海。
從拍片的時間和拍片的國別上來看,歐美等國在中國拍攝電影基本集中在1910年之前的十多年間。國外公司在這一時期紛紛來上海拍攝影片,主要基于三大原因。一是清末民國初期的上海的動蕩社會和光怪陸離的景象給了西方電影制作人無限的想象空間和取材靈感。上海是鴉片戰爭后第一批被迫開放的港口之一,相對于北京、天津和廣州等大中城市,西方社會更早更多地接觸到上海。那段時期的上海,一方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沼中掙扎著,另一方面又在科舉制度被廢除、新文化運動中吸收著民主與科學的思想;一方面是外國列強占地為租界的強取豪奪導致的民不聊生,另一方面是民族資本主義和有志之士救亡圖存的努力。由此反射出的社會萬象自然成了西方人眼中神奇有趣的題材,歐美的攝影師把鏡頭對準了那些愚昧、怪誕、凄苦但又神秘、耀眼的場景,盡管其中不乏扭曲現實、歪曲事實的影像,但可以看到,上海最有希望成為歐美電影公司來華拍攝的集散地。二是國際性和現代性的初顯帶動了上海娛樂業的蓬勃發展,為電影開辟了更大的市場。清末民國初期的上海已經逐步顯現出國際大都市的跡象,人們不再滿足于吃飽穿暖,精神生活和文化娛樂成了上海人民追逐時尚的風向標。而電影作為一種興起的娛樂,正滲透到市民的社會生活中去。20世紀初的上海,已經發展成為中國最大、最重要的工商業城市,也培育為中國最大的消費城市。電影是消費品,消費品就需要龐大的市場。上海的消費特質和消費能力與電影的消費本質相吻合,上海為電影消費提供了大量的消費者,而與此同時,電影消費也進一步刺激了上海的對外交流。上海成為歐美電影公司在中國以至于在亞洲最賺錢的市場。三是本土化的影像迎合了人們的娛樂心理。由于近代上海特殊的發展道路與環境,使得上海擁有大量的外來移民,人口結構變得紛繁復雜。在這樣的結構背景下,盡管上海缺乏精英階層和高級知識分子階層,但是大量的中小市民階級成為了看電影的主要群體。他們文化程度不高,收入很低,更喜歡通俗的事物。這也是為何早期外國電影公司在華拍攝的都是自然風光和人們日常生活狀態的實錄,那些公司通過上海市民熟悉的場景來推銷他們的電影,做到電影的本土化,以此吸引更多人涌入影院。但是到了20世紀20年代,上海的民營電影公司例如明星、聯華和天一相繼崛起,其中涌現了大批的電影人士,他們在十幾二十年間以上海為背景,拍攝了相當多的優秀電影,有的還打造了當年電影市場的高票房,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歐美電影公司對于中國電影市場的浸透,也使得歐美電影公司非常少將拍攝場地選擇在中國。
二、“東方之珠”的魅力
21世紀初,中國電影完成了從蕭條到繁榮的跨越。國內票房從2000年的10億左右上升到2010年的百億元突破,中國電影市場正以其快速的增長和無限的潛力成為爭奪的焦點,而上海作為中國最發達的城市,不僅因其巨大的市場動力吸引著各方電影投資者,同時它的神秘和繁華也成為了不少外國導演青睞之地。
假如100年之前的外國電影公司在上海取景是為了搶占國內市場,那100年之后的國外導演選擇上海為拍攝地又是出于哪些考慮呢?第一,在中國拍片成本低廉。這是外國影片赴華拍攝的最重要原因。盡管以好萊塢為首的電影比起其他國家的影視制作更容易獲得大筆資金的支持,但是在通貨膨脹壓力日益嚴重、勞動力成本與日俱增、投資金額越炒越大的21世紀,很多“省錢”至上的制作人不得不把拍攝地轉移到租金更便宜、薪水更低的地方,亞洲,尤其是幅員遼闊、風景秀麗的中國自然成了西方電影人眼中的香悖悖。而上海這座將中西方文化完美融合的國際大都市,將懷舊和時尚展示得淋漓盡致,再加上相對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健全的法律機制、方便的生活設施,為制作方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例如電影《面紗》,集合了愛德華·諾頓、娜奧米、黃秋生等明星,制作成本卻只有3400萬美元左右,這在美國只能拍一個靠賣錄像帶收回投資的小成本電影,但如果在中國拍攝,卻足以拍一部大片。另一方面,通過中國大片《英雄》《十面埋伏》和日益受到關注的《無極》等電影在服裝、攝像和特技方面給海外公司留下的印象,越來越多的海外公司開始選擇價格便宜但是能力不俗的中國制片部門合作。第二,海派文化中的兼容并蓄、神秘以及歷史文化背景也是吸引外國導演的原因之一。作為中國的第一大都市,上海擔負著“世界人民了解中國的一扇窗口”的特殊使命。上海所獨有的“海派文化”是一種受西方文化影響較早、較多的復雜地域文化,它根植于中華傳統文化基礎,融會吳越文化等中國其他地域文化的精華,吸納、消化一些外因的文化元素,逐漸形成富有上海地方特色、為世人所共知的具有獨特個性的文化模式。其開創性、創造性、揚棄性和多元性給予了電影拍攝的精神土壤。上海豐富多彩的歷史和人文又給電影創作增添了既復古又摩登的元素。19世紀40年代開埠以來,上海就一直在書寫著屬于她的傳說。從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冒險家的樂園”,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后的日新月異,再到21世紀躋身國際金融中心行列,上海有著太多的故事讓電影人樂此不疲地追尋。《面紗》《伯爵夫人》和《黃石的孩子》等影片都再現了上個世紀30年代老上海的景象,《紅美麗》《碟中諜3》和《環形使者》等影片則是對現代上海的重新演繹。然而,無論是充滿傳奇色彩的上海灘,還是時尚發達的新上海,無不體現了一些外國導演對于東方文明的喜愛和對于海派文化的推崇。第三,上海擁有電影市場理想的經濟環境。對電影市場而言,經濟環境的好壞往往意味著電影消費者的消費實力的強弱和電影市場走勢的強弱。上海是中國最大的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也是中國經濟的“心臟”,其財政收人占全國的1/8,口岸進出口商品總額占全國的1/4,港口貨物吞吐量占全國的1/10,強勁的經濟動力讓上海成為全國最大的消費市場之一。上海移民眾多,海納百川,上海人民相比其他城市的人更能接受各種各樣的文化和新鮮事物,再加上上海一直是中國電影市場票房的巨大貢獻者之一,都是吸引國外電影制作方的原因。
三、電影宣傳與城市營銷
西方電影制作人選擇到中國城市取景,體現了電影宣傳與城市營銷之間的博弈。從電影宣傳角度上,來華拍攝不僅能夠節省成本,更是向電影上映的潛在市場進行一場低成本的宣傳。在電影市場日趨火爆的21世紀,當每月二三十部新片上映已成常態,當24小時之內數部電影同時上檔已不稀奇,當電影宣傳費用增速逐年超過CPI,當明星緋聞、激情戲等老手段不再吊起受眾胃口,電影宣傳需要新的血液注入,來抓住消費者目不暇接的眼球。在中外電影交流不斷頻繁和深入的當下,上海無疑是外國影片迫切想占領的市場。用“上海影像”這一概念可以引起上海受眾的興趣,可能還會有助于票房的提升。就像《面紗》的廣告宣傳語“好萊塢電影史上第一部全景在中國境內完成的影片”,《碟中諜3》在上海上映前反復強調戲中高潮部分的拍攝地是上海,而《變形金剛2》雖然沒有到上海取實景,但是其在中國宣傳時所稱有東方明珠電視塔的戲份也吸引了不少影迷特別關注那一鏡頭。這些都是海外影片制作方推廣電影的一種手段,目的就是讓本土的觀眾產生好奇心,從而走進電影院。另一方面,上海可以借助外國公司來滬取景進行城市營銷。“城市營銷”已經是全世界都認可的一種營銷理念,營銷市場包括本地市場、國內市場、海外市場,甚至是網絡之類的虛擬市場,它的概念最早來源于西方的“國家營銷”一說。
中國電影制作早期,人們并未意識到電影元素對于城市營銷的巨大作用,影片拍攝初期也并未將城市植入營銷作為創作時必須考慮的初衷之一。但是改革開放之后,隨著中國各大中城市相繼增加與外界的交流,城市營銷的概念就體現在了電影里。例如張瑜和郭凱敏當年主演的《廬山戀》,不但大大提升了廬山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使得“游廬山,看《廬山戀》”成為當地旅游一個必不可少的項目,該片也被譽為中國目前播放次數最多,播放時間最長的影片。時至今日,還有無數游客慕名《廬山戀》去廬山游玩,帶動了當地的旅游業發展。無獨有偶,馮小剛導演的《非誠勿擾1》和《非誠勿擾2》不僅在賀歲片票房上賺得盆滿缽滿,而且分別帶動了杭州西溪濕地和海南三亞熱帶雨林公園的旅游業,使得這兩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景點游客絡繹不絕。

電影《面紗》海報
綜上所述,西方電影中有著中國的影像對于中國形象的宣傳和中國電影的發展都很有利。城市影像與電影的融合,讓電影力量與城市魅力組合起來,希望把我們的城市文化與中華文化推廣到西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