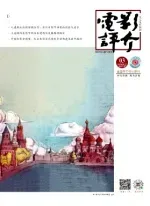阿蘭·羅伯-格里耶小說電影的美學特征
李 瑩

電影《去年在馬里安巴》劇照
20世紀60年代,阿蘭·羅伯-格里耶的小說電影是法國“新小說”派在電影領域的新探索。在《未來小說的道路》一文中,他認為小說改編的電影為他提供了一種思維方式。電影通過精選場景,將小說字句的意義直接呈現在觀眾面前。“而在原著的小說里,構成故事機體的物件和姿態卻完全消失了,只剩下它們的意義。”[1]而電影卻在其畫面呈現中恢復了物件的現實性。因此,阿蘭·羅伯-格里耶創作的小說電影,是恢復故事機體原貌的一種呈現方式。關注物件的呈現不是目的,關注真實性,關注人類生存環境的真實世界,從傳統的功能意義的世界中掙脫出來,達到真正的創作自由才是其目標。
阿蘭·羅伯-格里耶編劇和阿侖·雷乃導演電影小說《去年在馬里安巴》(1961年,第26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不朽的女人》(1963年)、《橫跨歐洲的特別快車》(1967年)被視為法國“左岸派”電影的代表作品。20世紀50年代,在存在主義和結構主義哲學思潮的影響下,法國文藝界掀起了一股反傳統的潮流。在文學界以“新小說”派為代表,在戲劇界是荒誕派,在電影界與之相呼應的則是“左岸派”的作品,“左岸派”是法國新浪潮電影運動的一個分支。法國新浪潮電影運動是繼歐洲先鋒主義、意大利新現實主義以后的第三次具有世界影響的電影運動。這一運動的本質是一次要求以現代主義精神來徹底改造電影藝術的運動,它的出現將西歐的現代主義電影運動推向了高潮。這一運動有兩個分支,一是作者電影,即“新浪潮”;另一是作家電影,即“左岸派”。
可以歸入“左岸派”的編導有阿侖·雷乃、阿涅斯·瓦爾達、克利斯·馬爾凱、阿蘭·羅伯-格里耶、瑪格麗特·杜拉斯、讓·凱羅爾和亨利·科爾皮,因他們都住在巴黎塞納河左岸,故有“左岸派”之稱。他們大都是作家出身,所以人們又常把他們拍攝的影片稱為“作家電影”。[2]
阿蘭·羅伯-格里耶作為“新小說”派的領袖,將他宣揚的“新小說”理論運用到電影劇本的寫作和拍攝,用“新小說”的語言元素加入到了電影創作,在小說和電影這兩種載體之間尋找到了一個很好的結合點,從而使小說電影成為一種依賴語言符號敘述的特殊文學形式。通過對小說電影的經典作品《去年在馬里安巴》的文本解讀,探討阿蘭·羅伯—格里耶小說電影的美學特征。
一、瓦解敘事
阿蘭·羅伯-格里耶的小說電影如同他的新小說,在作品中瓦解了傳統意義上的故事敘事。小說和電影雖然屬于不同的藝術門類,但都是敘事藝術。小說的第一要素是語言,小說用語言來塑造人物,展現情節事件、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以及人物的思維過程。電影則是以影像組合的鏡頭作為媒介。媒介的差異導致二者使用不同的藝術符號:小說使用文字符號系統,電影使用視聽符號系統。文字符號系統具有所指和能指結合的隱晦性和不確定性,而試聽符號系統則直接訴諸于觀眾,具有直觀性和現實性。基于這樣的差異,小說在敘事手段上主要采用敘述、描寫、理論和抒情,而電影的敘述手段是鏡頭并列、連綴的蒙太奇手法。小說和電影雖然敘述手段不同,但為敘事藝術都是要在作品中講述一個符合邏輯的故事。很多小說被改變成電影搬上銀幕,或者很多電影在放映成功后又被改變成小說出版。能夠實現小說和電影作品之間互相改編的前提就是其敘事性。閱讀故事也是讀者的一個傳統習慣。但是阿蘭·羅伯-格里耶卻在他的小說和電影中瓦解了敘事。
有學者聲稱阿蘭·羅伯-格里耶與阿侖·雷乃合作編導的小說電影《去年在馬里安巴》是“迄今以來最難以理解的一部影片”。這與電影的文學風格是分不開的。阿蘭·羅伯-格里耶將他的新小說的寫作手法運用到電影劇本的寫作之中。電影劇本為電影拍攝提供了場景設置、人物外形、鏡頭的遠近和組合,并進行了具體的文字指導。電影場景朦朧而虛幻,故事沒有遠景,只有近景,是一個自在的封閉的世界。似乎是一個放在歐洲的任何地方都說得通的旅館。電影人物主要有三個,女主角A,丈夫M和陌生男子X。人物形象是平面化的,對人物的描寫只停留在表面的模糊印象。A是一個離群的女人,25歲到30歲,美貌,身材修長;丈夫M是個50歲黑白頭發的男子;陌生男子X只有衣冠楚楚的總體印象。作者介紹人物的語氣是“我們用字母A來代表她”。[3]“我們稱他為M吧”。[4]作者意在表明他所描寫的人物,并不是獨特的“這一個”,而是抽象普遍的“某一個”。人物沒有獨特的個性和形象,名字只是一個代碼。電影沒有采用傳統的線形結構,而是多個事件的無序拼貼,但主要的情節可以概括為:陌生男子X告訴女主角A他們去年在馬里安巴相戀,約好一年后的今天在這里相聚,一起私奔。A感到詫異,確定自己不認識X,但在X對過去的反復講述中產生了懷疑,被X降服,最后跟隨X私奔。
M是什么身份,X是一個真誠的追求者還是誘奸者,是否真的有馬里安巴這個地方,A和X是否真的在這里相戀相約,還是僅僅出自于X的謊言。A真的回想起了他們相識的記憶還是被X的謊言所迷惑。電影敘述的故事充滿了不確定性,敘述者之一X更是一個不可信的敘述者。電影在敘述故事的同時瓦解了敘述的真實性和可信性,敘述充滿了謊言和不確定性。阿蘭·羅伯-格里耶在電影《不朽的女人》中,人物設置為L、M、N,故事撲朔迷離,前后敘述的故事充滿了矛盾和自我否定的成分。在羅布·羅伯-格里耶看來,電影是呈現視覺感受的最好形式。他預設觀看他的電影會出現兩類截然相反的觀眾:一類觀眾想恢復“笛卡爾”格局,搞清楚故事的來龍去脈,使之合情合理,就會覺得這是一部非常難懂的電影。而另一類觀眾隨遇而安,任憑感受地進入電影,就會認為這部電影很好懂。以阿蘭·羅伯-格里耶為代表的“左岸派”電影人,追求把電影拍攝成為以藝術家自己的形式表現生活的藝術品。藝術電影的模糊性、多義性、不確定性為他們展現后現代生活的豐富性提供了想象空間。
二、瓦解傳統的時空觀念
阿蘭·羅伯-格里耶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和胡塞爾的現象學影響,在小說電影中運用了閃回、蒙太奇等手法,把人物的幻想與現實、過去與現在、表象與內在交互混雜,著力表現人物的潛意識。在他的小說電影中,對時空觀念作了有力的挑戰。傳統的敘事作品,時間往往是直線式行進的。而阿蘭·羅伯-格里耶在小說電影中也嘗試了時間的非直線式敘述。按照嚴格的時空觀念講述的男女主人公經歷,應該既有過去時的,也有現在時的,同時還隱含著未來時的。但阿蘭·羅伯-格里耶卻將男女主人公的過去和未來的表達隱藏在了現在的時空范圍中。最為典型的例子是X對A講述的關于去年在馬里安巴的故事。X在旅館客廳里找到正在看書的A,為了證明他們曾經相識,向她講述他們去年的一個對話的場景。
“請回憶一下,當時在弗雷德里克巴花園里……您當時離群一個人站著,稍稍側著身子,靠在一個欄桿上,手搭在上面,彎著手臂。”[5]X對A的姿勢的描述,正在引導她與自己的一些慣用的姿勢形成平行對比,獲得體驗。對發生在過去時間的情景進行再現式的描述:“為了找話題,我談論起這個雕像。我對您說男子想阻止年輕的女子再往前走……”[6]然后鏡頭轉換,A與X再次出現,A穿著另外一套衣服和X靠在石欄桿前繼續談話。當X要求帶領A到更遠的地方觀看雕像時,說:“請跟我來。”[7]但鏡頭再次轉換,A與X又出現在旅館客廳,A卻穿著在花園那個場面的連衣裙,化妝也相同。鏡頭就這樣循環轉換幾次。人物的精神面貌和著裝在兩個交替的場面中出現混亂。從清晰的時空轉換和鏡頭切換到時空交錯,人物形象進行了互換。使用“現在”“也許”,“那么在別處,在科爾斯塔,在馬里安巴,或在巴頓薩沙——或干脆就在這兒,在這個客廳里”。[8]這些模糊的時間概念和隨處皆可的空間意義,打破了過去與現在的時間界限,此處和別處的空間界限,將A在X的講述下產生的幻覺、潛意識和夢境表現得淋漓盡致。復雜的時空觀念給我們理解A提供了廣闊的猜想空間:一是X利用時空交錯為A營造了一個迷失的回憶,引誘A相信了他的謊言,跟他私奔。二是X的講述喚起了A對未來的憧憬,他們心靈相通,共同奔向向往的未來。三是A原本就是一個不安分,向往自由的女性,與其說是X引誘了A,還不如說是A早就在等待這樣一個機會或一個人帶她走出現在的生活。
三、寫物風格的延續與轉變
小說電影也延續了阿蘭·羅伯-格里耶早期小說的“寫物”風格,并表現出敘述者對場景呈現的非人格化態度。但與早期小說的以寫物為中心相比,他的中期作品顯然出現了一定的轉變,A不是被強大的物控制的弱者,而是具有強烈的生命力和自由精神的人。作家安排了幾個場景向觀眾展示了同時出現在她面前的兩個男性。
紙牌游戲室的多米諾骨牌游戲是敘述者多次敘述的場景之一。這個場景主要展示了丈夫M與A之間的關系現狀。X和M經常在同一個桌上競技,M是游戲場上的強者,很多人敗在他的手下。X出現之后,經常是最后一個和他較量的對手。敘述者不厭其煩的為我們敘述游戲過程:“M先撿去單獨的火柴,X從三根一排中拿起一根,M從五根一排中撿一根,X再從三根一排中拿一根;M從七根一排中撿兩根,X拿起三根一排的最后一根……”[9]多米諾骨牌游戲在電影中是男性人物的專利,似乎暗示了名利場上搏斗與廝殺。而M在這場游戲中,憑借非凡的理性和機智,總能掌握全局,獲取勝利。M對A也像對待物(多米諾骨牌游戲)一樣具有強大的控制力。但A不能忍受他的控制和冷漠,最終決定離開他。
X對石雕群像的講述是電影重點敘述的一個場景。在雕像前,X對A訴說著曾在弗雷德里克巴花園為她解釋過雕像姿態:“您問我這些人是誰,我回答說不知道,您做了好幾種猜想,我是也可能是您和我。”[10]“我對您說男子想阻止年輕女子再往前走,他覺察到什么——肯定有危險——,于是用手擋住了他的女伴。您回答我說,興許他覺察到了什么,但相反他們發現一件妙不可言的東西出現在他們眼前,她正伸手指著呢。”[11]這個場景提供了A選擇跟隨X私奔的內因。與其說是A相信了X在她面前一邊說、一邊杜撰的謊言或者過去發生的事情,還不如說A可以將它設想為未來和X度過的生活,充滿了浪漫和冒險。這是A逃離現在,奔向未來根本原因。
總之,阿蘭·羅伯-格里耶認為電影這種綜合藝術形式是最能充分體現“視覺派”小說家的形式探索和藝術革新。他在電影領域為新小說所強調的視覺呈現性找到了最好的媒介。在他的小說電影代表作《去年在馬里安巴》中,他通過瓦解敘事、瓦解傳統的時空觀念和寫物風格的延續與轉變,造成了這部藝術電影的模糊性、多義性、不確定性,為展現后現代生活的豐富性提供了想象空間。
[1]柳鳴九.新小說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63.
[2]韓君倩.塞納河左岸的獨語——談“左岸派”對電影藝術的獨到探索[J].當代電影,1994(1):68-72.
[3][4][5][6][7][8][9][10][11](法)阿蘭·羅伯-格里耶.去年在馬里安巴[M].沈志明,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28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