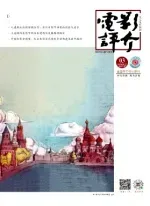解讀《西游記之大圣歸來》中的英雄涅槃
丁祥倩
2015年7月,電影《西游記之大圣歸來》僅上映20天累計票房便已突破7億元大關,打破了《功夫熊貓》在2011年創造的票房紀錄,奪得內地動畫電影冠軍,被影迷譽為“國漫的良心之作”。專家普遍認為,《大圣歸來》在國產動畫電影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中國文藝評論協會會長仲呈祥說:“‘歸來的大圣’是個符號,歸來的是中國精神、中國風格、中國優秀傳統。”①電影《西游記之大圣歸來》研討會,中國電影資料館,2015年8月4日。
眾所周知,中國古典名著《西游記》以其富有傳奇色彩的故事內容及跌宕起伏的情節鋪排,在影視界一直倍受青睞,近年來,以其為藍本更是翻拍出了不少精彩作品。而經典之所以不朽,更重要的是源于其背后所提倡的普世價值觀。貫穿于《西游記》的勇敢與正義精神,便是其長盛不衰的凝聚力。電影《大圣歸來》采用公路片結構,以孫悟空從五行山下走出后在拯救他人與拯救自我一明一暗兩條路徑中完成了一次英雄涅槃,彰顯了中國風尚與品格。本文從榮格分析心理學出發,具體探討孫悟空完成英雄蛻變的前后形象與內心成長歷程,進一步發掘電影蘊含的精神內核所具有的當代價值。
一、自然天性之放誕不羈
在從五行山走出之前,對齊天大圣孫悟空而言,他一直都是自己心目中的蓋世英雄,無論世俗是否承認,他從未言敗,即使身體被佛祖壓在山底下,精神卻始終高昂著頭顱,孤傲地審視著世事滄桑。
電影一開始便是大鬧天宮的場景,這似乎是齊天大圣的生命巔峰,各路天兵天將無力戰勝這只無所不能的仙猴,紛紛落敗,無奈只有如來佛祖現身處理這蔑視天庭的舉動,才使事態得以平息。而同時,孫悟空再也不是曾經的齊天大圣,封印束身的他,只是“一只普通的臭猴子而已”,于五行山下,一壓便是五百年。

電影《西游記之大圣歸來》海報
從石頭縫里蹦出來的孫悟空,其稟性天然,熱愛自由。分析心理學家榮格認為,“自我”是指一種復合的東西:“首先你對自己的身體、自身存在的一般意識,其次是你的記憶材料,你對已有的一連串記憶的某種觀念”,這便是最初無意識中的自我,而“自我只有存在于無意識狀態中,才是自然的、天性的,也才能生活得無憂無慮”。[1]同樣,大鬧天宮時的孫悟空,正處于這種自我無意識狀態中,也即本我階段,追求的是無拘無束,在他的內心中,自己具備高超法力,不服從禮教制度的管約,一旦稍有不滿,便會利用手中的各項本領,任意釋放天性中的無政府主義,以致四大天王等被打得落花流水,上演了大鬧天宮的一幕。這里,孫悟空的自我在這種狀態中得以無障礙生存,其千變萬化的法術加之不可一世的個性讓天庭眾神談猴色變,無形中縱容了他本來就狂妄的自我無意識,加之其武藝高強,眾神難以媲美,使得他幾乎可以為所欲為。至此,孫悟空自命不凡的自我無意識已經膨脹至極,而如來佛祖將其關于五行山下,正是對他狂放心理的壓制,對他心性的磨練。
二、法印束縛之信念崩塌
影片中,當江流兒為躲避山妖偶然走進了關閉孫悟空的山洞,又偶然地觸碰了孤冷的冰殼時,那滴從受傷的手中流出的鮮血卻必然地打開了束縛的枷鎖,齊天大圣從堆積如山的石塊中重新站起。這一場景的設置頗有深意,一滴血融化的不僅是那具冰衣,更是其背后唐僧一世的江流兒內心善良正義的力量對孫悟空個人信念的再次喚醒,同時為片末的大圣歸來作出鋪墊。
從五行山走出后,孫悟空本想回花果山過逍遙自在的日子,但在自覺與不自覺之中,走上了送江流兒與傻姑娘回長安城的路。應當承認,在孫悟空的內心仍然存在愛與正義,在山妖橫行的情況下,實際上他是自愿保護江流兒兩人的,這是他內心的另一個無意識自我,雖然他有蠻橫霸道的一面,但本性善良,這是他對自己的另一個心理期待——俠者仁心。
然而,滄海桑田,物是人非,此時的孫悟空已不是當年戰無不勝的齊天大圣,他雖已從五行山下解脫出來,但法印尚未解除,功力大不如從前,就連一個由石塊組成的山神都阻擋不了。當山妖沖進客棧奪走幼女時,他因自己無能救人而變得十分沮喪與失落,“我管不了,管不了”,每每看到手腕上的鐵鏈,他都再一次意識到自己早已不是“從前的我”,心中的信念陡然崩塌。這里,孫悟空之所以會產生如此巨大的心理落差,正是因為在他的內心中,潛藏著一種“無意識”,這種“無意識”來源于五百年前大鬧天宮時自己的無所不能,也來源于他的俠肝義膽,但當這些期待受到外界的撞擊時,“意識”這種非自然產物就會被激發出來。榮格認為,“有意識的狀態會使你感到倦怠,會使你感到精疲力竭”[2],此時的孫悟空深感自己所處的境況之窘迫,痛苦也便隨之而來,齊天大圣風光不再。
雖然孫悟空內心充滿正義與果敢,但“你不過是一只普通的臭猴子而已”,這種意識讓他的心理防線漸漸崩潰,使他無法跨過自己心中的那座“五行山”。直到他在懸崖邊上發力想要解開鏈索無果,暈厥過去后墜入海中,他曾經的自信剛強陡然消失,他已被徹底擊潰,不僅是在與山妖的打斗上,更是在與自己內心世界的博弈上。
三、自我救贖之英雄重生
電影前段,江流兒的父親就曾對他說過,“齊天大圣是不會死的”,而這句話也像一個符號貫穿了影片始終。當孫悟空沉入海底時,幻覺中,他看到江流兒手中的那個大圣玩偶,耳畔響起的也是描述他的戲文,“齊天大圣孫悟空,身如玄鐵,火眼金睛,長生不老還有七十二變”。此時,影片又將他大鬧天宮時的場景作為回憶重現熒幕,加之岸上豬八戒的那句“別忘了,你可是齊天大圣啊”,這“一連串記憶的某種觀念”讓他幡然醒悟,心中那象征著正義與勇敢的火炬再次燃燒起來。
從榮格分析心理學的角度講,此刻孫悟空的自我無意識與意識發生了激烈碰撞,產生了“力比多”,即心理能量。江流兒對他的崇拜信任,以及義無反顧幫助傻丫頭回家的那份善良,加之山妖的為非作歹,喚起了孫悟空體內最初的無意識,他再次樹立了自信,準確地說,喚起的是他勇于擔當、匡扶正義的責任感,即使明白自己不如當年,卻毅然與山妖一戰到底,此時齊天大圣的英雄主義富有浪漫色彩,天生的反叛精神已幻化為主持正道的大義凜然,于是,豬八戒隨行,兩人共赴戰場。
影片中的山妖頭目混沌欲借童男童女之精華,煉制長生不老的仙藥,傻丫頭也在其中,孫悟空為救出這些孩子,便來到了混沌準備祭祀的地方。幾個回合下來,雖然孫悟空并不占上風,但卻依然堅持斗爭,“力比多”幫助他逐漸擺脫了意識的束縛,重新強大起來。劇情繼續發展,而結尾也是整部電影的高潮,使其所要頌揚的核心精神得以升華。江流兒見大圣被混沌用巨石卡在了山洞洞口旁,便主動幫忙,不拋棄不放棄,那一句“跟你說好了,要一起走的”的樸實溫情,何嘗不是一種大愛,而這份愛的力量又進一步增加了孫悟空的“力比多”,隨即他溫柔地說道:“傻瓜,你忘了,我是齊天大圣,我是不會死的。”我們暫且可以理解為這是勸戒江流兒迅速離開的托詞,但從大圣個人角度講,或許,這也是他心理能量的再一次壯大,只有自己首先相信自己,才能讓別人放心依靠。
最后,當孫悟空徒手扒開石堆,看到了江流兒稚嫩的小手只揮動了一下便無力地懸在了半空時,他在極度悲哀與絕望中,在無意識與意識的極端沖突下,迸發出了強大的“力比多”。榮格認為,對立的兩極間壓力越大,產生的能量越大。此時,孫悟空騰空而起,點化山石為鋼盔鐵甲,從耳洞中提出金箍棒,心懷正義與愛的力量,一回合便置山妖混沌于萬劫之地,真正的大圣歸來了,光芒耀眼。
《西游記》原著中,遇到孫悟空的唐僧已是自己的第十世,而那句“師父,等等我”也被孫悟空常常掛在嘴邊,這里,電影借鑒原著人物設置,塑造了唐僧一世江流兒的形象,而“大圣,你們快點兒”也呼應了唐僧與孫悟空的師徒關系,應該說,孫悟空的英雄回歸來是內外兩方面的條件造就的,其中,外因是江流兒身上愛的力量對他的感召,幫他在意識產生后喚醒了其除惡行善的本性,重新找到了無意識的天然自我,并促使他在無意識與意識的激烈碰撞中產生了“力比多”。而更重要的是助他完成英雄重生的內因,當白龍飛上天的時候,孫悟空抬頭望天自語道:“有一天,你要是夠堅強,夠勇敢,你就能駕馭它們。”實際上,在他心中一直對自己抱有正義與勇敢化身的期待,只是當這種無意識遭到破壞后,意識充斥著他的精神世界,使他曾短暫的一蹶不振,但當看到江流兒對身邊的人不離不棄的情感,以及勇敢斗爭的行為,他被感化了,這種感化隨即化作內心一股向上的力量,即“力比多”,讓蘊藏在他心底里的能量得以重新燃起,也正是因為他本性中正義的存在,才使他能夠在最后得以爆發,真正回歸到五百年前的齊天大圣,完成了自我救贖的精神涅槃。
結語
任何一個時代,都并不真正缺少英雄,只是有著不同的人格形態,但無論何種類型的英雄,也無論我們身處哪個時代,社會對“英雄”的定義都不會離開“愛與正義”這個評判標準,電影《大圣歸來》便是對這一價值觀的集中頌揚。當今世界,因為政治意識形態的不同,不同國家或地區存在著多元的價值觀,然而愛與正義卻是全人類永恒追求的理想精神世界。可以說,對這一普世價值觀的彰顯,是《大圣歸來》得以成功的關鍵,也是其票房魅力所在。
該片通過8年醞釀和3年制作,將動畫形象孫悟空重新搬上銀幕,在影片題材多樣、價值觀模糊的電影市場,《大圣歸來》不僅在技術上達到了世界級水準,在情節敘述與主題營造上也贏得了同行與觀眾的認可,同時凸顯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精神。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賈磊磊認為,該片在對中國傳統文化資源進行現代性的開采上,作了成功嘗試。①電影《西游記之大圣歸來》研討會,中國電影資料館,2015年8月4日。應該承認,《大圣歸來》對《西游記》靈感的吸收,在向經典表示敬意的同時,也在觀眾面前呈現了中國精神煥然一新的一面。
通過這樣一部動畫電影,我們也跟隨英雄孫悟空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中完成了一次內心世界的涅槃重生,感悟中國傳統精神品格的魅力所在,這種靈魂洗禮,在當下人格多元的社會體系中,正如一面旗幟,無論世事如何變遷,它都不會倒下,反而歷久彌堅。在《老人與海》中,海明威寫下一句箴言——“人并不是生來要給打敗的,你盡可以消滅他,但就是打不敗他。”[3]的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齊天大圣已成為英雄的代名詞,而英雄就是要憑借一顆勇敢正義的心,在偶爾失去自我的路上,永不言敗,找回那個“從前的我”,千帆過盡,勿忘初心。
[1][2]榮格.分析心理學的理論與實踐[M].成窮,王作虹,譯.北京:三聯書店,1991:7-8,7.
[3]海明威.老人與海[M].孫志禮,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