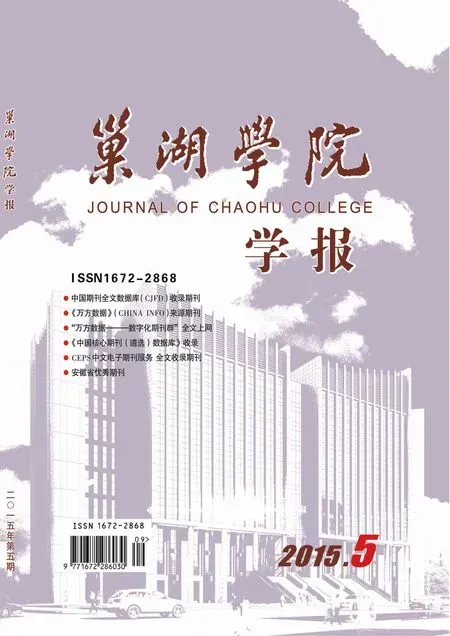試論孔孟孝道體現的“經”與“權”
張婷婷
(安徽大學研究生院,安徽 合肥 230039)
試論孔孟孝道體現的“經”與“權”
張婷婷
(安徽大學研究生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孝是儒家重要的倫理道德,而經權觀是儒家重要的方法論。孔孟皆重孝,二者孝又各有所長。總體來說,作為儒學的開創者,孔子的孝更多的是循規蹈矩,符合禮制的孝,也就是說,孔子的孝偏于執經;而孟子在發展孝道的同時,結合社會現狀和具體事例,對孝的遵循古禮的同時,有著因時因事權變的色彩,可以說,孟子的孝是守經達權的孝。
孝;經權;孔子;孟子
孔子重孝,孟子曾云,“乃所愿,則學孔子也”,因此,對于“孝”,孟子也極為重視。然而經過比較不難發現,孔孟所談之孝各具特色,即孔子提倡克己復禮,他的孝更體現出奉禮守經的一面,而孟子在發展孔子孝道的同時還帶有權變色彩。
首先看孔子。孔子認為孝悌是“仁之本”。對于有人問他奚不為政,孔子回答:“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這與他的政治思想“為政以德”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可見,孝作為“德”之一類,在孔子心中有著極高的地位,于家于國都有著重要作用,推崇孝悌就是在施行仁政。
1 孔子之孝

孝之一詞,不在于人的學識多寡,而在于德行的有無,它不是體現在口舌之利上,而是在于是否付諸于具體的行動。孔子論孝的行為可以根據時期不同而劃分為兩類,一類是父母在世的時候圍繞著奉養父母而展開的,另一類是在父母過世后圍繞著如何喪葬而行動的。
圍繞著怎么事父母,論語中零零散散提到了許多細節,比如,父母在世,由于要侍奉父母,孝子就應該“不遠游,游必有方”;為了贍養父母,他必須有理想有目標,最主要的表現是要有一份事業來謀生,所以孔子提出“父在,觀其志”;子女侍奉父母的態度要恭順,但在父母有過錯時,不能視而不見也不能直言不諱,而是要“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體現出對父母的敬重和對親情的維護;子女要牢記父母的年齡,當他們年歲漸高,一方面為他們高壽而喜,另一方面也為他們壽高而懼,等等。
當父母亡故,孔子強調通過“觀其行”來辨別是否做到了孝,具體就是孝子要慎重地辦理喪事,讓他們有尊嚴地離去;為父母守孝三年,表達對父母的哀思;三年內不改父之道,以示對父輩決策的尊重。
除此之外,《論語》還有幾句被認為帶有守身侍親的色彩,譬如 “父母唯其疾之憂”、“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可見孔子孝的核心是“愛人”,不僅在于愛父母,也同時要求關愛自己,不損害他人。至于后世愈演愈烈的埋兒奉母等“孝行”,連始作俑者都深惡痛絕的孔子,無疑是不會提倡這種過分的孝道的。
以上幾點都側重從行動方面來闡釋孝的具體內涵,所以說孔子在論孝方面,不是只空談,而是重篤行。

《左傳》里有這么一句話很好地寫出了經、權、禮、道之間的關系——“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也;權者,道之變也。”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合乎“禮”的孝,就是守經的“孝”。
關于孔子的孝,且看《論語》記載的一件事例: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谷既沒,新谷既升,鉆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
這里宰我拿禮崩樂壞做擋箭牌來逃避三年之喪,孔子對他這種行為嚴厲譴責的,因為他不僅違背了情,也違背了禮。
于情,父母含辛茹苦地把孩子養大,孩子為其守孝是對這種養育之恩的回報,是舐犢之情與孺慕之情的世代更替、交融,烏鳥尚能反哺,更何況是人呢?血濃于水的親情在孔子看來是任何其他的感情都無法比擬的,《論語·子張第十九》有“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這么一句,能讓十分注重儀表形態的孔子有如此感概,足以證明在他心中的孝是真性情的流露,是無法用理性克制束縛的。
于禮,父母做到了教養子女的責任,子女也該盡到奉養父母的義務,這樣從 “父慈子孝”到“父父子子”,將從情而生的孝上升到了倫理綱常層面,從而達到了禮的范疇。人人皆懂禮,社會安定和諧,可以促使仁政更好地施行,反之仁政的施行也將會社會道德更加穩固,這樣相互作用良性循環也正是孔子的最終理想。
總體來看,孔子論孝,無論是談及的行為還是所舉的事例,均并沒有超出禮約束的范圍。孔子提倡恭敬謹慎地事父母,但也不曾宣揚損己奉親;宰我之例中孔子批評他守孝不滿三年,但也不曾推崇延長孝期,過分喪葬。孔子行事中規中矩,他談孝也帶有過猶不及的思想,表現出嚴于守經,不偏不倚的特點。

權變思想在孔子孝道中體現的并不明顯,有兩處隱約帶有“權”的色彩。之所以說是隱約,因為禮也沒有明確規定必須要這么做或不那么做。
一處便是之前有提到的,孔子感慨人在面對至親的離去時,感情是最難自持,這也正如他所說的,“喪,與其易也,寧戚”。也就是說,孔子不反對子女在父母喪事上過分地痛哭。按照習俗,父母喪事,子女是要哭喪的,人們通常只會指責沒有表現出哀痛的子女,對于過分哀痛的,反而會稱贊他們孝順。
另一處是孔子在“父母在,不遠游”后面加上了一句“游必有方”。之所以有那么一句,個人之見是孔子自身游歷各國宣講政治主張,深感不遠游在當時各諸侯王不行仁政,百姓顛沛流離的社會是不容易被實現的。一般百姓為了謀生要遠游,而孔子心懷天下,為志奔走,也要遠游。更進一步分析,這里的“不遠游”,不是要強人所難,它僅代表孔子內心中希望每個子女都能承歡膝下,每對父母能夠更好地頤養天年這樣一個美好的愿望。
綜上所述,孔子之孝,從本質上并沒有背離常道,因此認為它是以守經的為主的孝。
孟子的孝道繼承了孔子,但由于時代的變遷,當時禮崩樂壞的現象更為嚴重,加之孟子性格更加圓滑世故,他對孝的理解又有其獨特的發展。
2 孟子之孝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中提到當時社會險惡的現象,即“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面對如此亂象,孟子對父子綱常更加注重,他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禽獸代表已經脫離了人的范疇,可見孟子是在用十分犀利的筆墨來批判墨家的兼愛無父對社會造成的惡劣影響。父子綱常的重申和他多次向君王提出通過“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來維護統治的政治主張是相輔相成的,孟子也是希望孝悌能夠肅清不良風氣,輔佐仁政順利施行。
《論語》記載有曾子的一句話“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可見曾子對后事與祭祖的重視。作為他的老師,孔子對逝者和奔喪之人的敬重也是眾所周知的,但在孝這方面,他并沒有說偏向于事親與送喪二者間的任何一個,往往是把這兩件事按父母生前父母逝后的時間順序先后并提。而孟子明確提出“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孟子·離婁章句下》)孔子只曾批判“今之孝者,是謂能養”的淺陋孝道,他認為“養生”遠不及“事親”,單純養生與養活牲畜沒什么區別,孟子在這里認為養生遠不及送死,可見二者都一致認為養生在“孝”地位中比較低。
此外,孟子在孔子孝的基礎上,還創造性地提出了不孝的幾種表現。比如說:
“不孝有三,無后為大”。
“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之前說到,孟子認為送死大于養生,但提到不孝,從他對五種不孝的列舉可以看出,卻全是圍繞著“父母之養”來寫。進一步推理可得知,孟子把養生作為孝的最低層面,把它拿來判斷孝與不孝,高于養生的是送死,而大孝就是舜,舜因其“終身慕父母①“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見之矣。”(出自《孟子·萬章章句上》)”、“以天下養②“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出自《孟子·離婁章句上》)”被孟子作為大孝、至孝的典范。
此外,在提到遇到父母有過錯時,比起孔子只要求兒女單方面的小心翼翼不抵觸父母,孟子則明確表示,要適度適當地“怨”,否則導致父子間“愈疏”、“不可磯”,反而會變成不孝。
以上體現的孟子孝道可以視為其對孔子孝道基本內涵的發展,有深化,無背離,是在禮崩樂壞更為嚴重時的“反經”。

孟子孝道的“權”從三個特殊的事例可見一斑。
2.2.1 一是舜不告而娶。從記載來看舜的父母不慈,弟不恭,不僅如此且有殘害舜的行為。但如果嚴格按照禮制,縱使他們不對在先,舜繞過父母直接娶妻也是不爭的事實。對于舜的行為,孟子解釋是由于“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他認為在人倫大義下的不告相當于告,結合之前所說“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來看,這里的不告可以理解成看似不孝,實為孝的舉措。在《孟子·離婁下》里也有一句“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因此,在孟子看來,舜是個十分通曉一般事物的道理和人類常情的人,他的所作所為不僅不是在違背禮與孝,而是沖破俠義的仁義限制,最終成全了人之大倫。而從舜之后的行為可以看出,盡管父不父,但舜依舊堅守著為人子的操守,勞而不怨地以天下侍親,如果這樣還要被指責,對這位孝子來說未免太過不公。孟子一向推崇舜的仁義,對于他的拳拳之心感同身受,這正是孔子所說“他人之心,予忖度之”的表現,批評舜不告而娶的人,卻未必能做到舜的程度。
2.2.1 二是與匡章游。齊國人都認為章子不孝,孟子卻不以為他不孝,并與之交游。之前所說的“不孝者五”就是孟子為匡章做的辯護。匡章的父親殺死匡章的母親,匡章選擇了遵從父親的意愿不為母親遷墓,這在父權社會并沒有受到責難,后來還得到了君王的稱贊和信賴,但他由于父子責善而決裂,造成了父子相離為人詬病。孟子深知匡章的苦楚,認為他通過趕走妻兒自我懲戒的舉動足以證明他是個正直的人。匡章的這種行為,近似于俄狄浦斯在得知自己殺父娶母后的自我放逐,俄狄浦斯是好人受磨難的代表,從匡章對父親的規勸來看,他也是好人,只是沒有處理好父子關系。因此,孟子能力排眾議,順從自己的判斷,與匡章相處,是難能可貴的。
2.2.1 三是厚葬孟母。孟子給孟母所作的棺槨過于華美,后喪踰前喪,面對他人提出的質疑,孟子解釋這是由于前后“貧富不同”,他認為現在的自己既有財力又有使用上等木材的地位,此番作為是無可非議的,并且孟子還補充道在體現孝心的時候,“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聯系之前他對舜不告而娶的解釋,孟子的行為也可以解釋為“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孟母用心良苦培養孟子成才的故事婦孺皆知,在孟子心中她不僅僅是啟蒙老師,更是有著生育、哺喂、撫養之恩的母親,孟子對母親的這份感情是遠比常人想象的要深厚,因此在力所能及而又沒違背禮的情況下厚葬孟母,實際也是對他深厚感情的慰藉,對人倫大義的尊重。
此外,孟子曾表示不可將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相比較。可見,他心中有秤,去衡量孰輕孰重,挾太山以超北海可不為,為長者折枝不可不為。他的權變并不是寬于律己嚴于待人,而是體現了對于特殊情形下的通達,究其本質依舊是“仁者愛人”,更人性化,更順應時代的發展。
3 當代環境下對孔孟孝道的取舍
盡管孔孟孝道各有側重,但二者可以說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春秋末期,為了利益弒君弒父等亂象就已經頻頻發生,孔子個性寬厚溫和,他更多地是從束己的角度提出相應的孝道,以圖匡正綱常,而在當時無疑是失敗的。孟子時期統治階級的內部和諸侯國之間的斗爭都更加激烈,所要面對的社會現象更為復雜,守經已經無法解決實際問題,因此孟子針對不同問題具體分析,采取經權結合的方法闡述孝道。
《孟子》中匡章的例子在今天依舊是個典型。比如2015年河南高考作文就是取材于一件真實案例,即女兒舉報開車打電話的父親。這個題目一出來就引發了眾人的爭論。若以孔子的思想評價,女兒這種公然舉報父親的做法無疑是不孝的,倘若依據孟子的觀點,女兒此舉則并不在不孝的范疇里。而從長遠來看,這種“大義滅親”的舉動不僅維護了社會治安,還有益于父親自身的生命安全,所以現今的主流觀念對女兒也是贊揚的。
在當代環境下,社會和家庭都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傳統孝道中的一些內容已經落后于這個時代,需要進行揚棄。孔子守經的孝趨于理想化,可以作為孝的范本進行參考。而孟子的孝在沒有背離孝的本質的前提下,以“權”給孝帶來了發展的空間,因此更加適應當今的需要。
[1]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8.
[2]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8.
[3](宋)朱熹,撰.孟子集注[M].濟南:齊魯書社,1992.
[4]楊海文.有一種人生智慧叫權變——孟子經權之辨的生存哲學闡釋[J].現代哲學,2008,(1):117-123.
[5]楊海文.激進權智與溫和權慧:孟子經權觀新論[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4):114-137.
A STUDY ON THE“RULES”AND“RIGHTS”EMBODIED IN THE FILIAL PIETY OF CONFUCIUS AND MENCIUS
ZHANG Ting-ting
(Graduate School,Anhui University,Hefei Anhui 230039)
Filial piety is an important moral concept of Confucian ideas,while“rules”and“rights”is also a crucial methodology of Confucian ideas.Though both Confucius and Mencius would think highly on filial piety in their theory,they could pay attention on different points.Generally,Confucius,as the originator of Confucian ideas,would emphasize more on rites.That is to say,obeying rites within society moral standard could be quite important in achieving Confucius filial piety.However,Mencius might consider more on weighting and changing during his developing of filial piety theory.According to social status and specific examples,Mencius is aiming at achieving a filial piety which could not only obey behavior rules,but also adapt to the various changing social situation.
filial piety;rules and rights;Confucius;Mencius
B222
A
1672-2868(2015)05-0016-04
2015-08-15
張婷婷(1992-),女,安徽蚌埠人。安徽大學哲學系,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哲學。
責任編輯:陳澍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