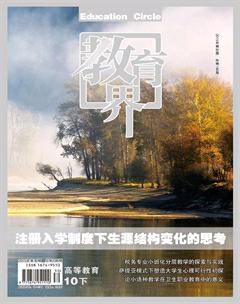淺談資本—帝國主義侵略對中國民主進程的阻斷
鐘聲
【摘 要】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造成了近代中國的貧弱,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難,這是中國人民的共識,對于各侵略國來說,這也是無法否認,不可掩蓋的罪行。本文擬以《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教學為基礎,淺談資本—帝國主義侵略對中國民主進程的阻斷。
【關鍵詞】《中國近現代史綱要》 ? ? 資本—帝國主義 ? ?侵略 ? ?中國民主進程
近代百年是中國的黑暗史,是國人的屈辱史,這一切都源于西方的殖民侵略,他們的軍事侵略使得中國國土淪喪,政治控制使得中國主權喪失,經濟掠奪使得中國國衰民貧,文化滲透阻礙中華文明的進程。正如馬克思評價不列顛對印度的殖民侵略,“印度失掉了它的舊世界而沒有獲得一個新世界”一樣,資本—帝國主義國家“打破了中國的舊世界卻并沒有給中國一個新世界”。
公元前475年到1912年,中國的政治體制都是封建專制制度,在如此漫長的時間維度里,中國政治體制有過多次的變動,各個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都在不斷地變革。公元前221年,秦吞二周而亡諸侯,中國的政治體制趨于成型,我們姑且稱為“秦政”。秦政經過無數皇帝專權者的改進,逐步完善,造就了古代中國的輝煌,使中國一度成為世界的中心,成為西方人、東方人向往的地方,而自己也逐漸成為“溫水中的青蛙”,沉醉于天朝上國的迷夢中。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誠如梁啟超所言:“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臺灣,償二百兆以后始也。”國人終于驚蟄,在多方探索挽救國家民族危亡道路之后,終于將目光投射到政治制度上。
政治之核心在于限制人的私欲,“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所以先進的政治制度是以憲法為中心,實行權力的制衡。而中國施行兩千多年的秦政,則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專制制度。社會國家的發展沒有任何制度的保障,社會國家的進程受個人喜好左右。相比較而言,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先進的,君主立憲或者民主共和。是時的國人已經認識到了民主制度的確立對于國家發展的重要性。清廷也被迫實行新政,在社會上更是產生了一場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大辯論。這場大辯論的主要對象是關于中國的政治改革,戰場卻是以《中興日報》《南洋總匯報》為核心的海外華文報。我們說民主的核心是自由,中國政論的這種格局,一則說明當時中國的言論沒有自由或曰自由度有限,一則說明持憲政觀點者力量薄弱,無法與清廷直接交鋒,只能退而取其次,外圍包抄,“農村包圍城市”。以《中興日報》作為陣地的孫黨和以《南洋總匯報》為陣營的康黨,唇槍舌劍,筆槍墨彈,在無硝煙的戰場上戰斗得異常激烈,即使如此,他們卻有一個共識,即: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秦政應該退出歷史舞臺,中國應該實施憲政。他們的分歧在于實施憲政的方式,孫黨希望采用民主共和,而康黨則堅持君主立憲。
如果說康黨和孫黨與清廷的博弈是中國憲政的濫觴。那么隨后的辛亥革命則是憲政在中國實踐的開端。辛亥革命雖然是一場革命(相對于改良而言是武裝起義),但是最后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建立卻體現了民主的精神。中華民國資產階級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建立是一種和談的結果,是各方力量相制衡的結果,從這個角度來講,也是對民主制度的實踐與嘗試。當時的中國主要有三大政治力量,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派,以張謇為代表的立憲派,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武昌起義時,三派力量相當,誰也強不過誰許多,大家的力量都有限,但是三者又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推翻帝制。在這樣一個共同目標下,在大家力量都差不多的背景下,三方坐下來談,以期用和平的方式來實現共同的目標。這樣的一個過程極為短暫,這樣的一個細節微不足道,但卻是中國由帝國到民國的轉型中,極為光輝而燦爛的一刻,雖然是轉瞬即逝,曇花一現,但在那一刻,中華民族竟然不是暴力者說了算,不是以暴力邏輯來決定,不是由湯武式的暴力革命來說話。可惜的是,這種平衡狀態很快被打破。勝出者是袁世凱集團,袁世凱集團之所以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積蓄起強大的力量,離不開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這股強力助袁世凱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中國本就先天不足的憲政之路至此受到重創。袁世凱上臺之后,毀法造法,解散國會,實行軍人極權統治,隨著宋教仁的被刺,中國的民主之夢也就灰飛煙滅。不僅如此,袁世凱甚至開起了歷史的倒車,與日本簽訂出賣中國主權的“二十一條”,登極稱帝,恢復帝制專政。
由以上分析不難看出,中國并非沒有民主議會的因素,這顆民主之花就像那無比絢麗短暫的煙火,瞬間凋零,甚至國人還來不及意識到它的存在,更談不上欣賞它的美麗。而在中國的這場民主發展的進程中,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充當了劊子手的角色,將中國的民主扼殺在搖籃里。其實這也符合近代資本—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本意與目的。他們只是希望瓜分瓦解中國,將中國變成他們的商品傾銷地和原材料供應地,而并不是要將中國發展成一個真正進步文明的資本主義國家。
在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武力干涉下,民主之夢對于中國人,借用海涅的“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來形容再恰當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