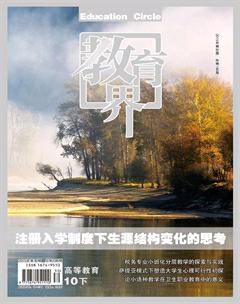“陽儒陽法”論
杜杰
【摘 要】“陽儒陰法”是一個誤論,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陽儒陽法。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都是被公開作為專制統治的思想工具,成為封建意識形態。
【關鍵詞】陽儒陽法 ? ?陽儒陰法 ? ? 封建意識形態
這個題目表達了一個新的觀點,可以說等于是對于傳統的“陽儒陰法”論的駁論。在理論界,“陽儒陰法”論是一個通識,認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公開倡導儒家思想而又暗里使用法家謀略,是陽柔陰剛合體的政治文化。這個說法是需要檢討的。從中國歷史的實際看來,法家思想從來都不是暗里使用的,而也是公開使用的。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都是被作為了專制統治的工具,所以說,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是被使用的,使用一詞,通俗而達意。整個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可以稱之為“陽儒陽法”。
這第一個問題,是要說說所謂的封建意識形態,是指封建社會欽定的封建思想理論,而與之對應的則是民間的觀念和思想,兩者當然是有相當的交集內容的,但不是等同的,有必要區別開來。陽儒陽法,就是封建意識形態。什么是封建社會,現在也仍然有著爭議,且大有反轉傳統成說之勢。傳統成說認為封建社會是從戰國后期到清朝終結的兩千余年的中國社會,基本上就是皇權社會。反對的觀點一直認為封建乃封邦建國之意,其典型時代是在西周,周朝才真正是封建社會,而周朝之后則恰恰不再是封建社會。本文則特別以為,所謂封建社會,可以指稱從西周開始的封邦建國一直到秦始皇后的皇權一統社會直到清朝終結。
這個觀點的實質是認為,秦始皇秦朝開始的新制度,從社會結構的本質看,并沒有中斷封邦建國的國家體系國家機制。郡縣制是官吏取代邦國制的貴族來管理郡縣,雖然官位不世襲,但依然是一世的土皇帝,跟邦國的貴族一樣是土皇帝。而以前的邦國制,也可以看作是古代的自治州。所以,整個國家結構依然是一個皇帝與大大小小的土皇帝的關聯,是一個權力分肥的體系。作為同樣的土皇帝,郡縣官吏跟皇帝的政治關系也依然是如同貴族一般的朝覲、進貢、勤王,其間的差別主要是“技術性”的不同。例如,秦始皇秦朝之前,就有諸侯國實行郡縣制,主要由于交通信息等技術限制而未能發展。故而,秦始皇秦朝開始的新制度,就是首先著意解決了交通信息等技術性問題,“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可以說,郡縣制的大一統新制度,就是在技術性基礎上建立完成起來的。而從《禮經》記載的內容看,封邦建國的周朝,天子對于諸侯國的統治,也是以王畿為軸心,越遠越疏于管理,最遠的地方只是象征性統治罷了。何哉?交通信息所局限也。在技術條件許可下,新制度的郡縣跟舊制度的邦國都同樣是對天子皇帝朝覲、進貢、勤王,基本關系是同質的、同構的。郡縣制與封建制的差別,與其說是制度上的,毋寧說是技術上的。因而,所謂封建意識形態,乃是指的從西周開始的封邦建國一直到秦始皇后的皇權一統直到清朝終結的長時期的官方的封建統治思想理論。
這第二層意思,來簡要說明儒法一體構造了中國傳統意識形態。首先說明的是,儒家和法家的思想淵源都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的禮(德)與刑。就基本思想而言,儒家講求禮(德)治,法家講求刑(法)治,可以說是各取其半,這就為后來的儒法一體奠定了坯模。學者們早有指出,在孔子及早期儒家思想和文化氣質方面,與周代文化有著一脈相承的聯結關系。孔子感嘆“吾不復夢見周公”,荀子更直言周公為第一代大儒。另一面,也如學人所指明的,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韓非,就主要表現了對于傳統刑罰的承繼。可以說,歷史上儒家與法家是同源異流,而儒法一體構造專制意識形態正是在漢代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之后的時期。實際上,也早有研究者指出,所謂“罷黜百家”并沒有真正落實,尤其沒有那么狹隘的,法家、道家、陰陽家、縱橫家、兵家依然在傳學。最主要的是,這個皇帝制度本質上就離不開刑治,離不開霸道與陰謀,離不開法家思想。而且,法家思想也從來都最為直接地、公開地體現在帝王統治之中,是最要害的帝王思想和統治術。
進一步說,儒法一體的傳統意識形態核心思想就是“三綱五常”。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就源出于法家韓非,后被附會儒學的董仲舒承襲。當然,《詩經》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可以看作更早的思想源頭。這里要著重提出來說明觀點的是,中國傳統專制主義思想的核心支撐正是法家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這個問題當另文專論。仁義禮智信的“五常”,是儒家的核心德目核心思想,不過法家也同樣講究這些德目,只是內涵理解大有不同。比如韓非,就直接把仁義之德納入帝王利益、帝王意志,利于帝王利益、帝王意志才是仁義。仔細看來,中國歷史上的法家才正是集專制主義思想之大成,儒家則更主要是塑造了中國傳統的社會心理。順便一說,儒家文化塑造中國傳統社會心理的最根本的一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這一條也可以說是中國民粹主義思想之源。
就封建社會的思想統治而言,可以說是“法家為體,儒家為用”。實際的中國社會就是一個以王權為軸心的家國體制,說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倫理社會,實在是誤解。也就是說,專制統治是以明白的王法作支撐的,儒家倫理的實際內容與專制統治有許多不相容的方面,倒是法家思想與王權統治一致合拍。實際上,在王法、家法一體同構的傳統社會里,民間社會治理也絕非主要以儒家倫理來維持,而自有同構于王法的家法。國家專制同構著家族專制,都是制度化的權力統治。儒家倫理以道德為核心,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所謂法“先王”。儒家沒有建構傳統的家族體系,而只是認同這種體系并維持這一體系的倫理關系,從而達到一種等級和諧。
接著就要說說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批孔”之失了,這是一個必須認真反思、重新認識的大問題。從由果求因的方法論來看,這個新文化運動恰恰沒有擊中中國傳統專制意識形態的要害:皇權意志和法家思想。中國現代文化之專制主義批判的一個怪現象是:只批孔子而少批秦始皇,儒學變成了專制的法器而不是王權帝制。從“五四”的反傳統到當代新批判主義莫不如此。那么,儒學與王法究竟哪一個更具有專制力及實際控制力呢?顯然,從中國傳統社會進程看,是王法帝制架構著整個社會體制和社會秩序。實際上,儒學并沒有形成為體制和組織,它從來都是依附性地存在,雖然歷經磨合而多有合流,但儒學在其社會功能上相對于王權的依附地位始終未變。秦始皇建立帝制,王法治國,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專制主義遂成為中國社會的根本制度和意識形態,這才是中國大一統文化的內在本質。單純地批判儒家,甚至使得法家思想展開得更加猖狂。可以說,儒法一體的傳統意識形態,儒家是附會于法家而成為專制思想理論的;而且,在儒法一體的傳統意識形態中,儒家既輔助法家,又在一定程度上有限地限制了法家的文化專制和政治專制。所以,我們看到的,歷史上那些極端專制的帝王,總是流露出來對于儒學的反感,甚至直接貶毀孔子孟子。而對于法家思想和權謀,專制帝王總能得心應手地習之用之,根本沒有像儒學那樣開館學習的必要。整個社會也莫不如是,把王法套在儒學頭上就可以經世致用了。如此,儒生與官吏總還是兩張皮的,盡管是“學而優則仕”,儒學更主要的還是一種文化傳承。
自然,上面這樣說,并不否定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的時代進步意義,而只是否定其片面性的同時更堅定地打倒法家思想理論;現實越來越表明,這個缺失可以說是災難性的。歷史的事實是,王法專制制度本身對人的壓制力遠遠甚于儒家說教的力量,批孔批儒的文化批判只是找了個虛靶子,帝制王法反而逃脫了文化批判的直接攻擊而始終未被清算。當然,我們不能苛求于前人,并且,我們只能仰視五四運動所達到的最高成就:愛國主義就是要建設一個民主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