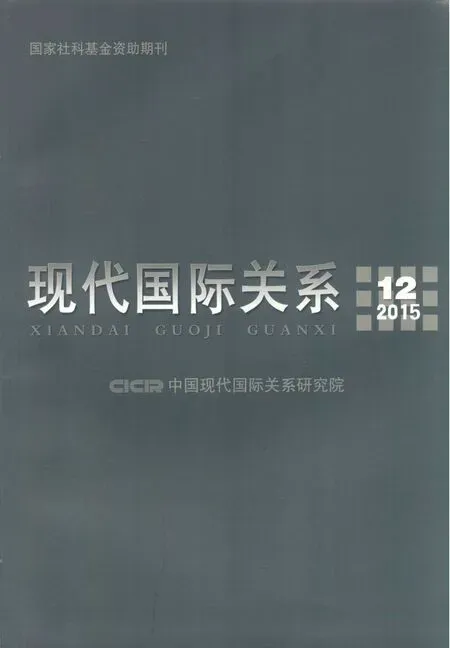中伊關系:核協議簽署帶來新機遇
田文林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東所副研究員)
中國是具有全球性影響的地區大國,伊朗則是日漸崛起的中東大國,因此中伊關系對雙方乃至全球都有重要影響。中伊深化合作既有強大推動力,也有不小障礙與阻力。尤其2003年以來,伊核危機升溫直接妨礙了中伊深度合作。2015年7月14日伊朗與六國簽署全面核協議,不僅使持續十多年的伊核危機“軟著陸”,也為中伊深化合作帶來機遇期。
首先,阻礙中伊深化合作的“第三方干擾”明顯減弱。“美國因素”一直是妨礙中國與伊朗深化合作的主要障礙。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美國將伊朗視為死敵,并想方設法進行遏制和削弱。2003年伊核問題曝光后,美國以炒作“伊朗核威脅”為抓手,對伊朗進行外交孤立、軍事威懾、經濟制裁,并日漸將國際社會拉攏到自己一邊,聯手圍堵伊朗。在這種情勢下,美國顯然不愿中伊關系走得太近。因美國對伊朗直接影響有限,所以不斷對中國施壓,一面勸說中國減少與伊朗合作,鼓勵除伊朗以外的其他能源生產國(如沙特)增加對華石油出口,改變中國對伊朗的相對依賴;一面頻頻加大對中國涉伊企業的制裁。中伊經貿合作本來潛力巨大,但由于美國“第三方因素”干擾,中伊經貿合作明顯受到抑制。尤其2012年美歐強化對伊制裁后,中伊貿易額從2011年的450億美元降至2012年的365億美元。
而2015年7月14日伊朗與六國達成全面核協議,使歷時漫長的伊核問題最終實現“軟著陸”。伊核協議內容長達上百頁,但核心思想只有一個,即“伊朗限制核能力,換取外部解除制裁”。可以預期的是,如果伊朗遵守協議承諾,并獲得國際原子能機構認可,歐盟有望停止對伊朗的經濟、能源及銀行制裁;美國也將取消或減輕行政制裁(包括金融制裁及能源制裁),并暫停國會制裁法案;聯合國制裁也將逐步取消。中長期看,伊核協議落實過程仍將不斷“扯皮”,制裁解除不會一帆風順,但對伊制裁松動是大勢所趨。
新形勢下,世界各國紛紛加大對伊朗關注和投入力度,進一步加快了對伊制裁體系的動搖與瓦解。歐盟對重返伊朗態度最為積極。歐盟曾是伊朗最大貿易伙伴,2012年歐盟啟動對伊朗金融和能源制裁,導致伊朗經濟受損明顯,但歐盟并未從中獲得好處。相反,歐盟追隨美國制裁伊朗,使自身利益受損。近些年,由于利比亞戰亂導致北非能源供應中斷,烏克蘭危機使俄羅斯能源供應出現問題。因此歐盟非常渴望重返伊朗市場。7月14日全面核協議后,歐洲代表團紛紛赴伊朗尋找商機。7月,德國、瑞士、法國等外長級團組訪伊尋找商機;8月,意大利等國相繼組團訪伊;8月23日,英國與伊朗重新互相開放使館,英國外長哈蒙德率領石油、采礦和工程等商界領袖訪伊探尋商機。《華爾街日報》預測,隨著伊朗石油禁令解除,伊朗在未來十年將成為歐盟最主要天然氣供給國。俄羅斯也加大與伊朗經貿合作力度。2015年7月伊核協議達成后,俄羅斯公開稱,俄今后將不會批準任何一項針對伊朗的制裁決議,并誓言將兩國貿易額增加10倍。2015年11月23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繼2007年之后再次訪伊,雙方簽署7項經濟合作協議,顯然有搶灘伊朗市場之意。
中國同樣面臨難得契機。中伊合作程度與伊核危機緩解程度呈正比例關系。2013年美伊開啟核談判后,中伊經貿額重新回升,2014年中伊貿易額升到520億美元,中國在伊能源和基礎設施領域投資增長近30%。2015年伊核協議達成,意味著阻礙中伊深化經貿合作的主要障礙正被清除。
其次,伊朗戰略重要性日趨凸顯,但中伊合作水平相對滯后。伊朗本來就是中東屈指可數的地區大國,無論資源、人口還是領土面積都相當可觀。近十年來,中東接連發生“政治地震”,伊朗每次都從中獲益匪淺。一是美國分別在2001年和2003年打掉塔利班和薩達姆政權,客觀上幫助伊朗擺脫了兩面受夾擊處境,并隱然出現了“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真主黨”的“什葉派新月帶”。一名伊朗議員放言:“貝魯特、大馬士革、巴格達這三個阿拉伯國家首都已落入伊朗囊中。”二是2011年中東劇變,導致埃及等親美政權垮臺,沙特等海灣國家成驚弓之鳥,土耳其外交“先贏后輸”,唯有伊朗政權穩固,地區影響力增加,即便敘利亞爆發危機后,伊朗通過強有力的資金和人員支持,使巴沙爾政權至今仍屹立不倒。三是2014年“伊斯蘭國”的興起,使中東主要矛盾由“防擴散”轉向“反恐”,由此使伊朗由重點防范對象變成了倚重對象。美國總統奧巴馬、國務卿克里都曾寫信或暗示,希望伊朗在打擊“伊斯蘭國”中發揮作用。四是2015年伊核全面協議的達成,意味著美國已經沒有能力武力摧毀伊核計劃,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此背景下,中東“反伊聯盟”聲勢銳減,而伊朗的地區影響力則會隨著對伊制裁體系逐步解除進一步增大。伊核協議簽署后,伊朗不僅獲得和平利用核能權利、保留部分核能力,地區影響力也大幅提升。有分析認為,伊朗有可能從制裁解除中獲得更多經濟好處,而且這種新發現的財富將使伊朗既能迅速增強軍事能力,又能更好地支持其在本地區的盟友(包括敘利亞、伊拉克、也門和黎巴嫩),從而在中東地區獲得更大發言權,乃至成為西方與非西方國家競相爭奪的戰略關鍵。可以說,伊朗的地緣環境正處于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最好的歷史時期。對中東十國精英層的一項民調顯示,絕大多數人認為,未來5~10年,伊朗將是中東最具影響力地區大國。
對中國來說,中東是落實“一帶一路”倡議繞不開的重點區域,伊朗又是這一重點區域的重要國家。伊朗油氣豐富,綜合實力強,市場潛力大,對外輻射強,地區影響力日趨擴大,是“一帶一路”合作必不可少的重要伙伴。但截止目前,中伊關系的密切程度和合作水平與伊朗的戰略重要性并不相稱,也與中國與其他中東國家(如埃及、沙特、阿爾及利亞、土耳其等)的關系定位難以相比。在中東形勢正在發生新變化的背景下,中國有必要強化與伊朗的全面合作。
第三,美國戰略東移持續加快,中國與伊朗深化合作緊迫感上升。近年來,美國因實力不濟,早在2012年初就放棄了“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戰略原則,其很難在中東應付伊朗,同時在亞太應對中國。經過反復權衡,奧巴馬最終選擇了“對華圍堵,對伊緩和”的大戰略。美國推行的“戰略再平衡”,實質就是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加大對中國的防范力度。2014年下半年以來,美國國內圍繞對華政策展開激烈辯論:美國對華“接觸”政策是否有效?如何評估中美關系前景?怎樣調整對華政策?總體看,美國對華負面評價日益增多,認為當初確定的對華“接觸”政策的兩大目標(對外開放促成中國政治自由化;中國參與和維護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都未實現。特別是2015年3月美國外交學會發表的《修改美國對華大戰略》,認為中國將是美國最重要的競爭者,因此有必要對中國日益強大的實力作出更加連貫的反應,以平衡中國實力的擴大而不是繼續協助它崛起。由此不難理解,美國為何將60%軍力置于亞太,并不斷加強與亞太盟友的軍事同盟,縱容日本、菲律賓等地區盟友主動挑釁中國。2015年以來,美國在南海地區的軍事挑釁明顯增多。
相反,美國在中東則加緊戰略收縮,其中重點就是盡快解決伊核問題,以促使美國盡快從中東脫身,甚而與伊朗一定程度實現“化敵為友”。2013年以來,美伊實現總統直接通話、外長會晤經常化,據傳兩國外長曾在阿曼秘談達成核協議后恢復外交事宜。2015年7月14日全面核協議的達成,意味著美伊關系由完全敵對,轉為“敵對+接觸”,某種程度實現了歷史性“政治諒解”。《紐約時報》認為,奧巴馬及其繼任者們仍有時間和空間重建美國與伊朗這一“敵意最深的敵手”的關系。中東媒體也認為,核協議可能催生兩國關系正常化進程。對美國戰略規劃者來說,簽署核協議最重要的目標,就是防止伊朗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與歐亞大陸新興經濟體整合到一起。美國認為,如果解除對伊制裁,并實現與西方關系正常化,伊朗將很快退出上合組織。美國甚至幻想使伊朗由反對美國-北約-海合會-以色列霸權的堡壘,變成反對金磚國家-上合組織-歐亞經濟聯盟-新絲綢之路的武器。
在這種新背景下,中國亟需采取對應措施,緩解戰略壓力。長期以來,在安全問題上,中國與中東某種程度是一種此消彼長的“蹺蹺板關系”。中國以往多次面臨外部壓力,但每次都是中東“出事”幫中國解套: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幫中國轉移“六四事件”帶來的制裁和壓力;2001年“9·11事件”,促使美國轉赴中東“反恐”,不再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當前,要想有效化解美國“戰略東移”帶來的安全壓力,仍然離不開中東這一“戰略緩沖器”。伊朗是中東主要地區大國,主張國際關系多極化,奉行獨立自主政策,這本身就是對美國全球霸權的戰略牽制力量。因此,中國唯有加強與伊朗安全合作,強化歐亞大陸國家內部整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和削弱來自美國的威脅和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