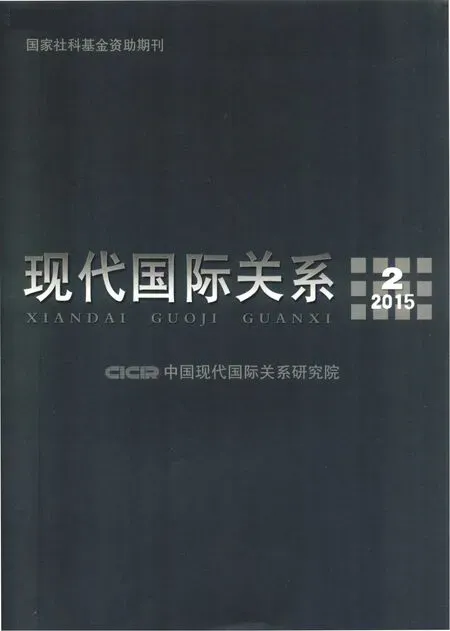2015年世界經濟需關注的幾個“量”
張運成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所所長、研究員)
2014年,全球經濟增長疲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謂之“平庸增長”(3.3%)。整體低迷之下,增長分化的態勢尤為明顯,實力消長悄然演變,預示世界經濟格局正迎來新一輪重塑。
全球經濟在歷經多年低位運行后,2014年增長分化明顯加劇,中美明顯領跑全球經濟增長,發達與新興經濟體之間及兩大陣營內部均出現增長分化。首先,美國、中國作為世界第一、第二大經濟體表現不俗,明顯領跑各國經濟。中國經濟雖然換檔減速,2014年增長7.4%,為25年來最低,但仍屬較高增長;美國經濟則調檔加速,第二、三季度經濟分別增長4.6%、5%,第四季度活力不減,全年增長2.4%,將好過IMF之前預測的2.2%。美、中如此大經濟體量同時在增速上突出是世界經濟少有的新態勢,而世界經濟的“火車頭”與“車廂”的差距漸大是暫時現象還是趨勢性變化,2015年將是一個重要觀察窗口。
其次,發達與新興經濟體之間延續增長分化。2014年發達、新興經濟體分別增長1.8%、4.4%,較2013年分別增加0.5個百分點和減少0.3個百分點。雖然從增速上看,發達國家仍遠不及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但從增速變化看,呈現出發達經濟體增長率總體向2%收斂、新興經濟整體從6%離散的新態勢。
第三,發達經濟體政策、增長均現明顯分化。美國經濟一枝獨秀,增勢明顯;英國、加拿大2014年增長率將分別達到可觀的2.6%、2.4%;歐、日則可能面臨“停滯風險”,歐元區經濟數據經過多次修正后,勉強避免零增長,2014年僅增長0.8%。日本經濟因上調消費稅對經濟造成沉重打擊,“安倍經濟學”推動的增勢正在逆轉,二季度經濟下挫6.8%,2014年僅增0.1%,經濟不振可能延續。美、歐、日經濟走勢上的分化,與各自經濟貨幣政策刺激的時機、幅度、手法不同相關,短期內歐日與美差距或將拉大。
第四,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分化嚴重。大國僅余中、印保持平穩或較高增長,2014年印度增長5.8%。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速分化比發達國家更為明顯。最高的亞洲新興市場可達6.5%,最低的如獨聯體預計僅為0.9%。金磚五國的其他國家,或受大宗商品價格暴跌影響經濟急劇下滑,如巴西經濟增速由2013年的2.5%急降至2014年的0.1%;南非因大宗商品價格下滑致經濟走低,其非洲第一大經濟體地位已被尼日利亞取代;或因石油價格暴跌與地緣政治風險疊加增長受壓制,俄羅斯經濟2014年僅增0.6%,但因盧布快速貶值、美歐制裁,預測2015年俄經濟實際增速將跌至-3%。
對于2015年全球經濟,總體看,各國經濟增長分化進一步加劇,改寫世界經濟版圖的動能也在累積、增大,世界經濟走向的不確定性因而更大,面臨動蕩抑或迎來機遇,沉悶低迷或是創新突破,尤需關注“兩股力量”、“一個變量”和“一大增量”。
“兩股力量”是指中國與美國。中、美對世界經濟穩定與增長將發揮更為重要和決定性作用,但將呈現出不同的影響途徑和方式,兩國之間競爭、合作的趨勢也將同時增強。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測算,2014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約27.8%,是貢獻最大的國家;美國次于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15.3%。美國經濟迅速轉暖甚至重新崛起很可能轉變整個世界的經濟格局;中國則在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區域經濟一體化等領域不斷推出新倡議,從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到“一帶一路”整體推進,從“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到“金磚銀行”,正努力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格局。
2014年,美國通過收縮與后退、中國通過開放與進取對世界經濟產生影響,至少在國際資本市場呈現出這樣的特點。伴隨美國結束量寬,全球資本回流美國,呈現“收水”之勢。如高盛數據顯示,2014年流入美股的外資占比達16%,創有記錄69年來新高。相比之下,2014年,中國基本成為凈資本輸出國,呈現向全球“放水”勢頭。在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上中國大幅超過美國,正是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在促進世界經濟發展上的具體體現。
兩股力量競合態勢明顯。競爭層面,在自貿安排設計、未來規則調整上,美打壓新興經濟體崛起意圖明顯;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力圖通過金磚機制以及區域自貿協定等維護自身利益。合作層面,二十國集團持續推動主要經濟體之間的協調與合作,并致力于改革國際經濟治理體系,中、美仍在共同推動氣候談判和APEC下的區域經濟一體化。
中、美經濟雖然領跑,但還未達到世界各國都將因此受益的程度,特別是美國決策層自行其是還可能產生負作用,而兩國經濟也不是“孤島”,世界經濟整體環境變化以及地緣政治風險,反過來將對中、美經濟增長形成制約。
“一個變量”是指美國加息時機。經濟增速放緩的國家出現金融、債務危機的可能性偏高,而由美元加息引發的資產重新定價和全球資本流動將對新興經濟體產生最大外部沖擊。美國經濟真正開啟繁榮,必然會導致全球資本回流,并引發相關國家出現金融動蕩,上世紀80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日本資產泡沫破滅都和美國貨幣政策的轉向緊密相關。目前美元加息預期正在升溫,新興國家已經出現明顯的資本外流跡象,美聯儲下一步的貨幣政策已成世界各國關注焦點,對業已疲軟的世界經濟構成不可低估的挑戰。誰能預見到,受量寬退出最大沖擊的國家是烏克蘭?如果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2013年12月31日不宣布退市,發行了巨額外債的亞努科維奇政府2月21日可能就不會垮臺。
綜合彭博財經和IMF數據分析,2013年,經常賬戶赤字占GDP比重高的國家是烏克蘭、土耳其、南非、秘魯、巴西、印度尼西亞、哥倫比亞、墨西哥、印度、波蘭、羅馬尼亞和泰國。2013年5月22日,伯南克首次暗示要退出量化寬松,隨即形成對世界經濟的沖擊波。至2014年10月底美正式結束量寬止,上述國家陷入所謂“消減恐慌”,先后出現幾波大規模債券拋售和資本外逃潮。2015年,爭議美聯儲何時加息的“利率騷動”(Rate Ruckus),也會如量寬退出所產生的蝴蝶效應一樣,對全球經濟帶來震動,并對一些國家產生重大沖擊。
據統計,美國正式退出量寬前后,60%的發展中國家出現貨幣貶值,實質就是本國資產重新定價的需要;而美聯儲一旦時隔9年后首次加息,將直接導致全球資產重新定價,進而引發資本流動。據美國外交政策委員國際經濟部主任本·斯泰爾(Benn Steil)預測,較之于2014年,烏克蘭今年經濟情況會有所改善,經常帳戶赤字將從2013年的9.2%消減至2.5%;泰國將扭虧為盈;秘魯、哥倫比亞、印度、波蘭、羅馬尼亞經常賬戶赤字將會增加,而波蘭和羅馬尼亞因美元升值可能受到最大沖擊。歷史經驗表明,一些高度依賴大宗商品和能源出口的國家,反復承受了資本外逃、貨幣貶值、物價高漲等風險,在經濟增長大幅放緩的過程中更是加大了調控難度,可能誘發新的經濟和金融危機。
“一大增量”是指世界科技和產業革命。世界經濟低速增長環境下,各國加快結構性改革步伐,期待新一輪世界科技和產業革命帶來機遇和突圍。世界經濟難覓新增長點,各國普遍面臨結構性改革壓力,“苦日子”可能不會短。主要經濟體為應對危機近年均推出大規模刺激計劃,但未能改變結構性問題。歐洲、日本增長弱化,持續加碼量寬刺激經濟,并無改革良方,僅靠印鈔也難堆出持久繁榮;新興經濟體則面臨維持經濟增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需進行重大結構性改革,實現創新驅動增長。
然而,世界經濟也在累積新力量、新勢能,拐角處或許就會榮景乍到。就在各方評估清潔能源、生物技術、互聯網、智能制造等尚未達到全面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程度之際,一些國家已在為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可能悄然而至做準備,力爭搶占先機和制高點。
美國近年將重振、發展高端制造業作為最優先發展的戰略目標。2010年,總統奧巴馬簽署了《美國制造業促進法案》。2011年,美正式啟動“先進制造伙伴計劃”,旨在加快搶占21世紀先進制造業制高點。2012年,進一步推出“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通過積極政策鼓勵制造企業回歸美國本土。2013年,奧巴馬專門發起成立先進制造業合作委員會,并通過該組織劃出11個技術領域包括傳感、測量和控制過程、材料設計、合成與加工、納米制造、數字制造技術、生物制造等為全國研發的重點。
同樣,就在輿論仍持懷疑態度的情況下,近年來以頁巖油、頁巖氣為主導的新能源革命徹底轉變了美國能源依賴國的地位。國際能源署預測,美國將于2017年超過沙特阿拉伯,成為世界第一大產油國,這標志著美國頁巖革命正轉變著整個世界的能源格局。
制造業最為發達的德國將醞釀中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稱為“工業4.0”,力推實現信息技術與制造業深度融合,促使工業領域的設備、生產與系統以網絡化的形式向互聯網邁進,將制造業向智能化轉型。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必將成為改寫世界經濟內涵、版圖和秩序的新能量,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希望和前景所在。為應對新科技產業革命,爭奪國際產業競爭話語權,中國既不能等,也不能慢,唯有迎頭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