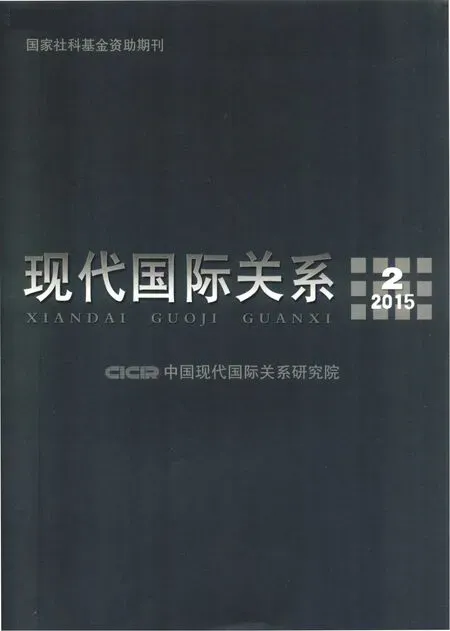國際制度與國家治理——第二屆UIBE國際政治經(jīng)濟高端論壇綜述
熊李力
在全球性的跨國問題此起彼伏、全球治理的相關理論與實踐方興未艾、國家治理面臨的挑戰(zhàn)趨于多元化、大國競合博弈呈現(xiàn)多層次寬領域態(tài)勢之際,國際制度與國家治理到底有何聯(lián)系?國際制度與國際關系之間如何相互影響?中國應如何參與、塑造國際制度?為探討影響國際關系和中國外交走向的這些重大問題,2015年1月17日,對外經(jīng)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主辦了以“國際制度與國家治理”為主題的第二屆對外經(jīng)濟貿易大學(UIBE)國際政治經(jīng)濟高端論壇。來自北京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防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清華大學、外交學院、(臺灣)政治大學、中共中央編譯局、中共中央黨校、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現(xiàn)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國政法大學、對外經(jīng)濟貿易大學等十多所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40多位學者專家參與了論壇,集中研討了國際制度的發(fā)展趨勢、國際制度與國際關系的相互影響、中國對國際制度的參與和塑造等三大議題。
國際制度的完善與發(fā)展涉及國際制度對國家治理有何影響、未來國際制度如何確保影響力的有效性、事關國際制度發(fā)展趨勢的核心要素等。學者們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梳理和闡述。中國政法大學全球化與全球問題研究所蔡拓教授指出,隨著各國間聯(lián)系日趨密切,環(huán)境、氣候變化、公共衛(wèi)生、反腐敗等問題既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國家治理需要解決的難題,也是全人類共同面對的全球性跨國問題,兩者之間的邊界日趨模糊。在這種背景下,國際制度與國家治理的結合將更為緊密,國際制度對國家治理的引領效應趨于強化。國際關系學院趙曉春教授認為,國際制度變遷已進入加速發(fā)展階段,全球性的跨國問題此起彼伏,不斷涌現(xiàn)對國際制度的新需求,但是既有的國際制度遠遠不能滿足這種需求;與此同時,與大國競合博弈相似,國際制度變遷呈現(xiàn)多層次和寬領域的發(fā)展趨勢,不僅體現(xiàn)在全球和區(qū)域等各個層次,而且涉及政治和經(jīng)濟等多個領域。對外經(jīng)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戴長征教授指出,國際制度失效風險的主要誘因在于各國對國際制度的選擇性支持,若要確保未來國際制度影響力的有效性,既需要以全人類共同價值為基礎,代表跨越國界的人類共同利益,也離不開主要大國的主導性參與。
關于國際制度未來發(fā)展趨勢的核心要素,中國現(xiàn)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林利民研究員和外交學院蘇浩教授都認為,體現(xiàn)人類共同性的價值基礎至關重要。林利民研究員指出,應對當前國際關系現(xiàn)實中的種種亂象,無論埃博拉之類的公共衛(wèi)生危機,還是各國頻繁遭遇的恐怖襲擊,都需要進一步推進全球治理。即使如烏克蘭亂局這樣的地緣政治危機,也只有通過全球治理才可能化解。推進全球治理離不開國際制度的物質平臺,而在制度平臺的背后,是體現(xiàn)人類共同性的價值基礎。然而,既有國際制度的價值基礎主要源自西方價值體系。對此,既應有所吸收,又當有所批判,尋找共同價值基礎是未來國際制度發(fā)展的大勢。蘇浩教授將近代以來的世界政治劃分為強權政治、意識形態(tài)政治、威權政治和文明政治等四種形態(tài)。他認為,未來國際制度的核心應該是構建于文明基礎之上的人的精神和人的價值,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一種具有普世意義的精神和價值。
伴隨著國際制度的完善與發(fā)展,國際制度與國際關系的相互影響必然發(fā)生相應的變化。圍繞當前國際關系現(xiàn)實對國際制度運行模式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研究所李少軍研究員比較分析了國際制度運行的“大國警察模式”與“多邊治理模式”。由于通過“大國警察模式”解決國際問題的代價越來越大,在國際制度框架內設置多邊議程解決國際問題的趨勢將更為明顯。鑒于核大國之間爆發(fā)戰(zhàn)爭的后果不堪設想,在阿富汗戰(zhàn)爭和伊拉克戰(zhàn)爭中一度盛行的“大國警察模式”難以重現(xiàn),美國和歐盟將更多地借鑒在烏克蘭問題上的行動模式,在國際制度的運作中側重于“多邊治理模式”,以經(jīng)濟制裁取代大規(guī)模軍事行動。國防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唐永勝教授認為,國際制度能否對國際關系產(chǎn)生更大的正面影響,關鍵在于各國能否實現(xiàn)國家利益與人類共同性之間的平衡。一方面,倘若各國過分強調自身的特殊性與自主性,國際制度、國際關系乃至各國外交都必然失去活力;另一方面,倘若各國完全追隨世界潮流,難免錯過最符合本國具體需求的發(fā)展機遇。國際制度形成和發(fā)展的根本動力來自世界的整體性,而世界的整體性源自各國國家利益的吻合。
對于中美關系在國際制度中發(fā)揮什么作用,學者們相當關注。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牛軍教授指出,回顧1949年以來的中美關系史,因兩國務實的戰(zhàn)略訴求而起的激烈對抗并不多見,中美但凡發(fā)生激烈對抗,基本都源于雙方超出正常的戰(zhàn)略訴求。在中國方面,這種超出正常的戰(zhàn)略訴求就是試圖在東亞地區(qū)秩序中占據(jù)排他性的領導者地位。因此,對今日中國而言,到底需要在東亞地區(qū)構建何種國際制度是值得深思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周琪研究員認為,美國推進“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首要目標是通過影響亞太區(qū)域國際制度的發(fā)展進程維護美國在該地區(qū)的利益,實現(xiàn)這一目標的可行途徑是在制度化框架內積極參與亞太區(qū)域合作。TPP談判既是近年來亞太區(qū)域合作制度化進程中的一大熱點,也是美國“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重要一環(huán)。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zhàn)略、推動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從國際制度層面對美國“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回應。
大多數(shù)中國學者認為,國際關系研究離不開對中國外交理論與實踐的思考。探索國際制度的發(fā)展趨勢、闡釋國際制度與國際關系的相互影響,都需要深入探析中國如何參與和塑造國際制度的問題。學者們對國際制度之于中國外交的重要意義給予了高度肯定,并深入探討了中國參與、塑造國際制度的戰(zhàn)略路徑和潛在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時殷弘教授認為,中國應適度增進“國際制度信仰”,亦即對國家間制度性合作的“信仰”。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外交需要從強調中國國情和中國特色的“防御性態(tài)勢”,轉為既堅持中國的特殊國情和特殊性質,又注重自主訴求與國際社會普遍期望之間愈益增進的共通性;在此基礎上,中國應當更加努力擴大國際共同利益、共同認識,增進國際共同努力。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阮宗澤研究員認為,中國的發(fā)展在過去30年主要體現(xiàn)為增量型成長,未來30年應實現(xiàn)質量型成長,這就涉及參與、塑造國際制度的問題;通過參與和塑造國際制度,中國應該在亞太地區(qū)甚至更廣闊的區(qū)域內形成合作共贏的局面。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金燦榮教授指出,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的一大特色是新倡議特別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帶一路”與“亞太自貿區(qū)”,推動落實這兩項新倡議都需要構建相應的國際制度平臺。中共中央黨校戰(zhàn)略研究所高祖貴教授認為,盡管中國近年來經(jīng)濟增長迅速,但要把經(jīng)濟實力轉化為國際影響力尤其是對國際制度的話語權,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對于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新興國際制度平臺的形成與發(fā)展,中國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今后應避免新興制度平臺與既有制度平臺之間出現(xiàn)競爭關系,著力塑造二者之間的互補關系。清華大學國際戰(zhàn)略與發(fā)展研究所楚樹龍教授認為,國際制度作為國際公共產(chǎn)品的意義不僅體現(xiàn)在物質層面,而且體現(xiàn)在價值層面;無論參與既有國際制度,還是塑造新興國際制度,中國不僅應提供“一帶一路”和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等公共物質產(chǎn)品,而且應注重提供能為各國接受的公共價值產(chǎn)品,這才是一個世界大國對國際制度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