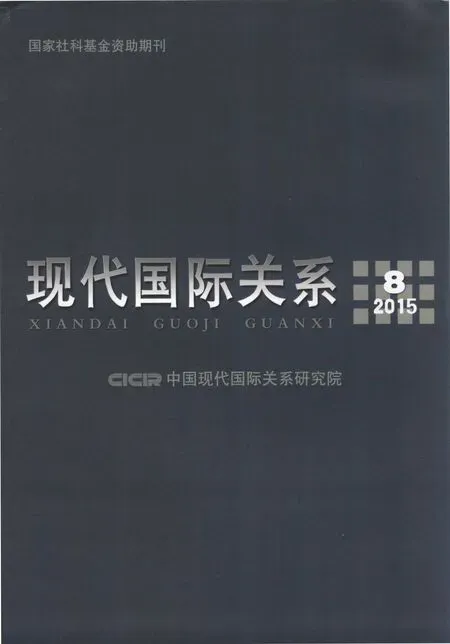從“村山談話”到“安倍談話”:日本在歷史認識上“失去的二十年”*
黃大慧
冷戰結束以后,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發展態勢長期低迷,經歷了經濟上“失去的二十年”。實際上,日本在歷史認識上同樣經歷了“失去的二十年”。從戰后50周年發表正視歷史的“村山談話”,到戰后70周年發表缺乏誠意的“安倍談話”,過去20年日本在歷史認識上呈現出不斷倒退的趨勢。特別是第二屆安倍政權成立以來,日本國內歷史修正主義明顯抬頭,一系列模糊侵略歷史性質、推卸戰爭責任甚至美化侵略戰爭的錯誤言行,引起了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究其原因,日本在錯誤歷史認識的軌道上漸行漸遠,主要源于其國內政治的日益右傾化。本文擬在回顧“村山談話”的基礎上,重點剖析“安倍談話”的主要內容及其實質,并從國內政治右傾化的視角闡釋日本歷史認識不斷倒退的深層原因。
一、正視歷史的“村山談話”
冷戰結束后,東西方之間的對抗淡化,隨之原本受到掩蓋或者壓抑的各種矛盾開始迸發出來。對于日本而言,歷史問題在其對外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如何認識和對待歷史問題成為日本政府的一項重要課題。恰在此時,日本政壇經歷了大變動,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失去政權,作為“國內冷戰”格局的“55年體制”宣告終結。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日本政府發表了正視歷史問題的“村山談話”。“村山談話”是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正式立場,為其后歷屆政府所繼承,并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
(一)“河野談話”與細川的“侵略戰爭”表態。在“村山談話”之前,日本政府發表的關于慰安婦問題的“河野談話”,以及細川護熙首相承認侵略戰爭的表態,也是應予關注和肯定的。
1993年8月4日,時任宮澤內閣官房長官的河野洋平代表日本政府對外發表了《內閣官方長官河野洋平關于慰安婦問題調查結果的談話》(即“河野談話”)①“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關于慰安婦問題調查結果的談話”,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1993danwa.htm.(上網時間:2015年8月1日)。該談話承認“慰安婦”的官方性質和強制性質,證實了被送往戰場的慰安婦原籍(來自朝鮮半島的女性占了很大比重)。日本政府表示要對此道歉和反省,并正視這一歷史教訓,“通過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將這一問題永遠銘刻于心,并再一次表明我們絕不重復同樣錯誤的堅定決心”。①“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關于慰安婦問題調查結果的談話”,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1993danwa.htm.(上網時間:2015年8月1日)“河野談話”是日本政府尊重歷史、承認錯誤的進步行為,得到了國際社會的積極評價。
就在“河野談話”發表次日誕生了以細川護熙為首相的八黨派聯合內閣。細川就任首相后即表示,太平洋戰爭“是侵略戰爭,是錯誤的戰爭”。這是戰后日本政府首次明確承認“侵略戰爭”。但細川迫于國內右翼勢力的壓力而最終將“侵略戰爭”改為“侵略性行為”。接下來,在“8·15”例行的“全國戰歿者追悼儀式”的講話中,細川首次表示“對日亞洲近鄰的犧牲者表示哀悼”。在施政演說中,細川對于“日本的侵略行為和殖民統治等給眾多的人們造成難以忍受的痛苦和悲哀”,表示“深刻的反省和道歉”。細川還在聯合國大會上表示,“我希望再次說明,日本對過去的行動繼續懷有悔恨感,它決心要在實現和平與安全的目標中進一步作出貢獻”。細川護熙因此成為日本戰后第一位誠摯對待歷史問題的首相。
“河野談話”和細川表態顯示了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積極姿態,并為其后“村山談話”的發表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發揮了促進作用。
(二)“村山談話”。1994年6月,以社會黨委員長村山富市為首相的社會黨、自民黨、先驅新黨的聯合政權成立。相較其他政黨,日本社會黨作為“革新陣營”的代表,在歷史問題上向來持有積極的立場。因此,村山上臺伊始即表示,希望能解決“自民黨過去未能解決的戰爭歷史認識等問題”,并將“出臺反省過去戰爭的決議”列入三黨聯合政權的共同協議。然而,日本國內圍繞“不戰決議”卻展開了激烈的政治斗爭。
“不戰決議”全稱《以史為訓重表和平決心的決議》,早于“村山談話”兩個月由日本國會眾議院以不到半數通過,但終因參議院未能按慣例審議通過而導致該決議被擱置。事實上,“不戰決議”只是一個模棱兩可、泛泛而談的“決議”。該決議有意回避以道歉、謝罪的形式承擔日本所應履行的國家責任,而只是談到“認識到我國過去進行過的這種行為及給予他國人民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的痛苦,對之表示深刻的反省”。這份缺少“侵略”、“殖民統治”、“道歉”的所謂“決議”,由于政治勢力的紛爭尤其是自民黨的強烈反對而最終遭遇流產。因此,村山不僅要盡量避免過多地刺激右翼保守勢力,還要對“不戰決議”進行補救,緩和國內正義力量和鄰國的質疑與不滿,維持國內政治這架“天平”的平衡,而發表“村山談話”就成為其合適的選擇。
經過日本國內政治以及國內外的復合博弈,在日本宣告投降50周年的1995年8月15日,村山首相終于正式發表了題為《戰后五十周年之際》的談話,即“村山談話”。“村山談話”可以分為三個部分:日本的戰后建設;對歷史事實的道歉和反省;村山本人的施政誓言。
第一,村山表示戰后日本的建設歷經艱辛,“戰敗后,日本從被戰火燒光的情況開始,克服了許多困難,建立了今天的和平與繁榮。”②“村山富市內閣總理大臣談話”,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1995danwa.htm.(上網時間:2015年8月1日)村山還指出,“今天,日本成為和平、富裕的國家,因此我們動輒忘掉這和平之尊貴與其來之不易。我們應該把戰爭的悲慘傳給年輕一代,以免重演過去的錯誤。并且要同近鄰各國人民攜起手來,進一步鞏固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③“村山富市內閣總理大臣談話”,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1995danwa.htm.(上網時間:2015年8月1日)
第二,村山直面歷史事實,并作出道歉和反省。村山表示:“我國在不久前的一段時期,國策有錯誤,走上了戰爭的道路,使國民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機,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為了避免以后發生錯誤,毫無疑問,我們應謙虛地接受歷史事實,并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時向在這段歷史中受到災難的所有國內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其中,“國策有錯誤”、“殖民統治”、“侵略”等成為“村山談話”直面歷史的明證。村山對之再次表示了“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并向受難者表示“沉痛的哀悼”。村山還表示,“我國應該立足于過去的深刻反省,排除自以為是的國家主義,作為負責任的國際社會成員促進國際合作”。①“村山富市內閣總理大臣談話”,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1995danwa.htm.(上網時間:2015年8月1日)第二部分反映了日本政府清算歷史罪行和承擔戰爭責任的較為明確的立場和堅定的自信,構成談話的核心部分,也形成了“侵略”、“殖民統治”、“道歉”、“反省”等關鍵詞語。
第三,村山引用“杖莫如信”這一古語表達其施政理念:“信義就是我施政的根本”。②“村山富市內閣總理大臣談話”,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1995danwa.htm.(上網時間:2015年8月1日)村山決意用信義指導對政治道義的追求,并以行動來實踐自己的政治理念。
“村山談話”是以內閣決議形式發布的正式文件③內閣決議形式,是由內閣決定整個政府意志的程序。在首相主持召開的內閣會議上,由全體閣僚一致決定是其原則。決定事項包括政府提出的法案、中央省廳干部人事安排等。“首相談話”需要經由內閣會議決定,被定位為政府官方見解。不同于僅由首相決定的“首相的談話”。,因而不僅僅是村山個人的談話,也是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的正式立場。“村山談話”有兩個著名的“第一次”:第一次以“內閣總理大臣”的名義代表政府發表如此完整的文件;第一次認定過去實行了錯誤的國策并明言侵略。“村山談話”的發表反映了當時日本政府對歷史問題最為深刻的反省,是戰后日本政治走到十字路口時發表的一份關鍵談話,④步平:“徹底反省侵略歷史才有光明未來”,《人民日報》,2015年3月23日。也成為了日本21世紀亞洲外交的基本理念。⑤[日]村山富市、[日]佐高信著,陳應和譯:《“村山談話”到底是什么?》,東方出版社,2013年,第009頁。對此,我們要予以肯定。
但是,“村山談話”實際上是政治妥協乃至退讓的產物,在歷史認識上有著鮮明的“現實性”特點。一是村山曾一度考慮以“國會決議”的方式發表這一份談話,但在內閣討論中多數意見認為以“總理大臣”名義代表政府發表更為慎重和嚴肅,但這實際上是歷史認識的一種倒退。二是由社會黨、自民黨和先驅新黨三黨成立的“50年問題工作委員會”在商議如何處理戰后問題時,有人主張使用“侵略戰爭”,也有人主張使用“侵略行為”。最終,村山歸納為“侵略”兩個字,有關“侵略”的性質認知和表述模糊化了。三是在“村山談話”中,把“侵略”和“殖民統治”結合在一起,而拒絕使用“侵略戰爭”的說法,這種曖昧做法實質上是一種退讓。⑥[日]浦野起央:“日本歷史認識問題的幾個層次分析”,《太平洋學報》,2005年,第7期,第86頁。
總體來看,“村山談話”是日本政府就侵略殖民歷史向亞洲受害國人民作出的鄭重表態和承諾,⑦楊依軍、徐棟誠:“外交部:‘村山談話’是日本政府的承諾”,《新華每日電訊》,2013年1月30日。反映了日本政府對政治道義的維護和追求,具有顯著的歷史性意義。該談話也成為日本的國家方針——日本曾經侵略亞洲各國并實施殖民統治是不爭的歷史事實,⑧“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日本侵略亞洲各國是史實”,http://japan.people.com.cn/n/2015/0521/c35469-27037778.html.(上網時間:2015年8月1日)在日本國家政策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村山談話”使得歷史問題有了比較好的結論,日本也因此得以翻開新的一頁。⑨“村山富市:對安保法案有強烈危機感”,http://japan.people.com.cn/n/2015/0730/c35469-27383672.html.(上網時間:2015年7月30日)它奠定了日本此后各屆政府承認戰爭事實和承擔戰爭責任的立場基調,因而也獲得了亞洲各國的尊重和贊同而成為日本歷史觀演變史中的里程碑式講話之一。
二、缺乏誠意的“安倍談話”
2012年12月,下臺3年多的自民黨重新奪回政權,安倍晉三再度登上首相寶座。安倍作為一個歷史修正主義者,上臺伊始就試圖改變“村山談話”等日本政府對歷史問題的正式見解。安倍不愿沿襲此前關于歷史問題的一系列表述,并多次表示要發表自己的“面向未來”的“談話”。
(一)“21世紀構想懇談會”報告。2015年2月19日,為了制定戰后70周年的“安倍談話”,日本政府設立了由16名成員組成的首相私人咨詢機構——“回首20世紀,構想21世紀世界秩序和日本作用有識者懇談會”,簡稱“21世紀構想懇談會”。該懇談會每月舉行一次會議,定于8月份前拿出研討結果,作為起草“安倍談話”的的參考和“藍本”。2月25日,第一次懇談會會議在首相官邸召開,安倍首相也出席會議。安倍為懇談會提出五個討論要點:(1)應從20世紀歷史中汲取的教訓;(2)對戰后日本和平主義、經濟發展、國際貢獻的評價;(3)戰后70年與歐美、澳大利亞等國,特別是與中國、韓國為首的亞洲諸國的和解之路;(4)對21世紀亞洲和世界的遠景暢想與日本的貢獻;(5)舉出戰后70年應該采取哪些具體措施。從這五點建議來看,安倍擺出了強調“面向未來”的姿態。于是,即將發表的“安倍談話”將如何評價日本的戰爭歷史,成為日本內外輿論關注的焦點。
2015年8月6日,“21世紀構想懇談會”經過7次會議認真討論,最終形成報告并提交安倍首相。從報告的內容來看,顯然是以安倍當初提出的“20世紀的教訓”、“戰后日本的歷程”等論點構成全文。不過,該報告最突出的要點還是歷史認識問題,其大部分篇幅也被歷史認識有關內容占據。是否將“前次大戰”視為“侵略”,貫穿整個懇談會會議,并引發委員們尖銳對立。其爭論的結果,一方面在報告中明確寫入“侵略”,另一方面在腳注中寫明部分委員對于使用“侵略”一詞存在不同意見。①在腳注中提出的三個理由是:在國際法上,“侵略”的定義尚未確定;即使從歷史的角度進行考察,將“九一八事變”之后的行動定義為“侵略”也存在不同意見;在其他國家也實施了同樣行動的背景下,不同意僅僅將日本的行為定義為“侵略”。需要說明的是,該報告通篇只有這樣一個腳注。
該報告首先指出,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悲慘戰禍,國際輿論傾向于和平主義,主要國家簽訂了“不戰條約”和“裁軍條約”。在此基礎上,該報告認為,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脫離了戰爭非法化的潮流”,是一種侵略,是破壞國際秩序的開端。報告明確指出,滿洲事變以后的日本,“擴大了對大陸的侵略,誤判了世界大勢,輕率的戰爭給以亞洲國家為主的各國造成了諸多損害”。報告認為,殖民統治從1930年代后半期開始日益嚴酷,并稱“不得不說(導致這些的)日本政府和軍方領導人的責任確實很大”。由此可見,報告不僅明確承認“九一八事變”是“侵略”,而且將戰后50年“村山談話”等談話中表述模糊的侵略時期等歷史認識明確化。也就是說,與“村山談話”中“我國在不久前的一段時期,國策有錯誤……”相比,該報告更加明確地說出了日本應該反省的對象。
此外,該報告稱“日本宣稱為了解放亞洲而戰的國家政策并不正確”,這排除了“圣戰論”,還可以“起到約束政治家講話不守規矩的效果”。②[日]“報告的歷史觀應反映在首相談話中”,《日本經濟新聞》,2015年8月13日。
該報告除了承認“侵略”,還納入了“村山談話”中的“痛切反省”表述。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令人失望的是,“道歉”這一關鍵詞沒有明確出現在這份報告中。實際上報告避談“道歉”,并且認為謝罪不是“單方的努力”。它指出,日本“不能說已經完全實現”與中國、韓國的和解,在強調“加害者秉持真誠的態度補償受害者是大前提”的同時,也敦促受害者一方應抱有“寬容之心”。在懇談會討論中,大多數意見認為“無需謝罪”。
這份報告還對日本在戰后70年的歷程給予肯定評價: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中,在以和平、法治為前提的國際體系中,日本是“忠實地走過來的國家之一”。不過,報告要求日本在安保領域做出更多的國際貢獻。
關于日本與世界各國和解的道路,該報告贊揚日美關系“是少有的獲得成功的雙邊關系”。與此同時,報告稱日中“雙方的想法70年里沒有充分達成一致”,日韓“和解至今未能實現”。其中還將未能很好地與中韓和解的責任,理解為中韓兩國沒有像美國等國家一樣抱著合作和面向未來的態度;指責“中方強化愛國主義教育”、“樸槿惠政權沒有看到與日本理性交往的意義”,導致中韓兩國與日本的和解無法取得進展。而對于真正阻礙和解的“靖國神社”合祀甲級戰犯等日方原因,該報告卻幾乎完全沒有提及。它還聯系中國的軍費增加,要求重新研究日本防衛費被限制在“國民生產總值(GNP)1%以內”的規定。
(二)“安倍談話”的內容及實質。“安倍談話”最終于2015年8月14日正式公開發表。整個“安倍談話”的篇幅超過三千字,囊括了對戰爭的回顧與反思、對日本未來國家走向的寄望以及施政方針等方面的內容。該談話基本上遵循了“村山談話”、“小泉談話”的歷史認識原則和精神,寫入“侵略”、“殖民統治”、“道歉”、“反省”等關鍵詞語,表面上正視了歷史問題,但在實際上卻離人們的普遍期望有很大的距離。
系統的涌現理論為企業跨越實體邊界與價值共創者組成的價值共創體系的整體屬性的評價提供了理論依據,因此,本文從涌現理論出發,針對超競爭環境中企業價值共創體系的運行特點,以是否保持企業價值共創體系的可持續價值創造能力為評價標準,對企業的價值共創體系進行全面評估,建立企業價值共創體系的價值創造能力評價指標體系,為當前復雜環境下的企業價值共創體系評估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從內容上看,“安倍談話”主要包含以下幾個部分。首先是對戰爭的回顧。安倍先是指出日本實現近代化的背景和動力,即19世紀波及到亞洲的西方殖民統治及其給日本帶來的危機感和實現近代化的動力,以及歐美各國推動的區域經濟集團化對日本經濟乃至國策帶來的沉重壓力。可見,安倍一開始便試圖將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置于全球歷史的背景之下。由此,安倍故意忽視了當時國內右翼政治勢力將日本帶上軍國主義統治和對外侵略殖民道路的事實,甚至表示“日本是被迫走上這一道路的,并為此受害深重”,這顛倒了受害和加害的關系。安倍還提到了“日俄戰爭鼓舞了許多處在殖民統治之下的亞洲和非洲的人們”,①“安倍晉三內閣總理大臣談話”,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2015danwa.htm.(上網時間:2015年 8月 15日)不僅否認了日俄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和對中國造成的深重傷害,還以“鼓舞亞非反殖民斗爭”為名美化這場戰爭。安倍表示“人們渴望和平,創立國際聯盟,創造出不戰條約,誕生出使戰爭本身違法化的新的國際社會潮流。”②“安倍晉三內閣總理大臣談話”,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2015danwa.htm.(上網時間:2015年 8月 15日)實際上,日本違背了此點:對中國發動“九一八事變”,退出國際聯盟,并對中國進行武裝入侵和殖民統治。作為對戰爭回顧的總結,安倍表示“日本戰敗了”。③“安倍晉三內閣總理大臣談話”,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2015danwa.htm.(上網時間:2015年 8月 15日)安倍在此省略了日本進行侵略戰爭和殖民統治的過程,并沒有直觀地認識這段歷史。
其次是對戰爭的“反思”。在這一部分中,安倍對戰爭進行了反思,也是“安倍談話”的核心內容。安倍表達了對死難者的痛惜和哀悼之意,“正當戰后七十周年之際,我在國內外所有死遇者面前,深深地鞠躬,并表示痛惜,表達永久的哀悼之意。”④“安倍晉三內閣總理大臣談話”,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2015danwa.htm.(上網時間:2015年8月 15日)安倍指出,“在如此重大損失之上,才有現在的和平。這就是戰后日本的出發點。”⑤“安倍晉三內閣總理大臣談話”,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2015danwa.htm.(上網時間:2015年8月 15日)安倍表示今后將繼續貫徹和平國家道路這一方針,堅持歷代內閣在歷史問題上的立場。對此,我們也要看到安倍轉移問題焦點、淡化戰爭責任的企圖和行為。安倍還提到許多無辜平民的受苦和遇難是由于“戰斗”和“糧食不足”,從而回避了日軍進行大屠殺的事實,間接地否認了日軍屠殺平民的殘暴行徑。該談話也始終沒有正視“慰安婦”問題,只是提到“在戰場背后被嚴重傷害名譽與尊嚴的女性們的存在”。⑥“安倍晉三內閣總理大臣談話”,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2015danwa.htm.(上網時間:2015年8月 15日)。而且,在第三部分中,安倍也保持了類似的表述。⑦即“我們繼續將在二十世紀的戰爭期間眾多女性的尊嚴與名譽遭受嚴重傷害的過去銘刻在心。”
關于“侵略”和“殖民統治”,安倍只是使用了“事變、侵略、戰爭”和“應該永遠跟殖民統治告別”⑧“安倍晉三內閣總理大臣談話”,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2015danwa.htm.(上網時間:2015年 8月 15日)這樣的表述,對日本侵略和殖民行為的表述故意抽象化、模糊化,繼續其一貫的“侵略未定”論調。關于“道歉”和“反省”,安倍表示“我國對在那場戰爭中的行為多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⑨“安倍晉三內閣總理大臣談話”,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2015danwa.htm.(上網時間:2015年 8月 15日)安倍所談的是“我國”而非他自己和此屆內閣。安倍以回顧歷屆日本歷史認識立場的方式表達了“反省”和“道歉”,他也沒有具體指出向誰道歉、為何道歉,“那場戰爭中的行為”亦不知所云。
值得注意的還有,安倍強調“我們將印尼、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以及臺灣、韓國、中國等亞洲鄰居人民走過的苦難歷史銘刻在心”。[10]“安倍晉三內閣總理大臣談話”,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2015danwa.htm.(上網時間:2015年 8月 15日)其中,安倍不僅將中國放在最后進行表述,更為重要的是將臺灣與中國并列提出,這違背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日本政府關于臺灣問題的承諾。
再次是日本未來的國家走向。安倍在這一部分中指出,“將歷史的教訓深深地銘刻在心,開拓更加美好的未來,為亞洲及世界的和平與繁榮而盡力”,①“安倍晉三內閣總理大臣談話”,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2015danwa.htm.(上網時間:2015年 8月 15日)具體包括“以實力打開僵局”、“慰安婦”問題、“挑戰國際秩序”等方面的內容。
安倍首先強調“值此戰后七十年之際,我國向致力于和解的所有國家、所有人士表示由衷的感謝”。在表示感謝的同時,代表戰爭施害者的安倍內閣添加了“感謝”條件——“致力于和解”,其意旨在對中韓等國進行差別化對待,借以逃避戰爭責任。安倍也企圖擺脫戰后體制,破除“自虐史觀”,認為戰后世代人數已經超過總人口的80%,日本不能陷入繼續道歉的宿命。
安倍還在談話中間接表達了牽制中國的意圖,將中國視為“國際秩序挑戰者”,②“安倍晉三內閣總理大臣談話”,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bunken_2015danwa.htm.(上網時間:2015年 8月 15日)并予以不斷地敲打。在爭端解決方面,安倍認為應該尊重法治,使用和平與外交的方式而非實力。在經濟方面,安倍以“區域經濟集團化”為名,暗示對中國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施行“一帶一路”戰略規劃的擔憂和質疑。③今年亞投行的成立,日本響應美國的號召質疑亞投行的透明問題,妄言其是中國為實現本國利益的一言堂;對于中國一帶一路的戰略規劃,也始終將其認定為是中國要控制地區經濟的表現。參見周生升:“‘安倍談話’暗暗敲打中國,實則一份精心制作的施政報告”,http://www.thepaper.cn/www/resource/jsp/newsDetail_forward_1364499_1.(上網時間:2015年8月16日)在“價值觀外交”方面,安倍指出“我國堅定不移地堅持自由、民主主義、人權這些基本價值,與共享該價值的國家攜手并進”,大力宣揚所謂的自由、民主、人權等西方政治價值觀念,并以此與美國、澳大利亞、印度等國家形成包圍中國的“價值觀同盟”。此外,安倍談話最后落到了他竭力主張的“積極和平主義”上。安倍強調“我們將高舉積極和平主義的旗幟,為世界的和平與繁榮作出更多貢獻”。這乍看上去寥寥數語,其實卻頗具內涵和象征意義,是“安倍談話”的核心之所在。如果說“村山談話”旨在“以史為鑒”,那么“安倍談話”則以“面向未來”為志向。安倍就是要藉發表“安倍談話”之機,使日本明確“告別戰后”,“堂堂正正”踏上“正常國家化”之路。
安倍此次發表談話反映了日本傳統的“亞洲中心觀”。安倍無論是在談話中對日俄戰爭的表述,還是在談話發表后的記者會上,都強調對中國和韓國的“大門永遠是敞開的”,⑧“日媒:安倍需正視歷史 該道歉就道歉”,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15/0816/906541.shtml.(上網時間:2015年8月16日)均是用“從上往下的視線”對待東亞鄰國,發起了在歷史問題上的“逆襲”。
事實證明,安倍對于歷史問題立場的意義認識已經大幅度衰減,歷史問題成了日本政府撥弄是非、混淆視聽的一個權宜工具。“安倍談話”意在漂白侵略和殖民統治歷史,掩蓋歷史真相,逃避歷史責任,進而從側面為當前最為棘手的安保政策掃除障礙,以更快實現“擺脫戰后體制”的目標定位。⑨張勇、吳懷中:“看清‘安倍談話’的伏筆:‘金蟬脫殼’”,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816/c1002-27468932.html.(上網時間:2015年8月16日)由此也可看出實現日本與東亞鄰國在歷史問題上的和解尚需時日。
三、歷史認識倒退背后的政治右傾化
“村山談話”發表以來的20年,日本在錯誤歷史認識的軌道上漸行漸遠,主要緣于其國內政治的日益右傾化。
右傾化作為一種政治思潮,在日本社會由來已久,甚至可追溯至戰后較早時期。①內田健三、「日本の右傾化狀況を分析する用語集」、『現代用語の基礎知識』、自由國民社版、1983年、第1-7頁。上世紀80年代初期,已經成為超級經濟大國的日本,提出要進行“戰后政治總決算”,并欲在國際社會爭做“政治大國”,日本政治由此正式拉開了右傾化的帷幕。冷戰結束后,隨著日本國內外環境的變化,日本政治的右傾化趨勢明顯增強。尤其是近年來,日本右翼保守勢力及其主張在日本政界開始占據上風并對日本政府的決策產生影響。日本政治越發濃厚的右傾化現象,引起了日本國內外的廣泛關注,甚至招致了盟友美國的批評和警覺。
談及日本政治的右傾化,首先應當關注執政的自民黨的右傾化問題。自民黨作為保守政黨,近60年來長期把持日本政權。自民黨原本是一個派系聯合體,黨內各派林立。自民黨內議員依其政治立場,可劃分為“右派”(“鷹派”)和“自由派”(“鴿派”)。兩者主要區別源于對待被稱為“和平憲法”的《日本國憲法》的立場。“自由派”主張維護憲法所體現的戰后價值,而“右派”則主張“修改憲法”或“制定自主憲法”。長期以來,自民黨內部主要是“自由派”掌握主導權,尤其在憲法問題和歷史認識問題上,“右派”基本上處于守勢。
然而,進入21世紀后,日本社會和政黨制度的變化,促使自民黨本身也發生很大的變化。2001年,小泉純一郎在自民黨黨首選舉中戰勝橋本龍太郎,標志著黨內“右派”取代“自由派”,開始掌握主導權。同時,也預示著自民黨激烈派系斗爭和利益誘導型政治時代的終結。爾后,在新的“大眾迎合主義”時代,自民黨很快蛻變成了“選舉專業政黨”。②中北浩爾、『自民黨政治の変容』、NHK出版、2014年、第208-226頁。小泉高舉新自由主義改革大旗,在“劇場政治”的舞臺上長袖善舞,贏得了較高的支持率,連續執政5年有余。而安倍晉三效仿小泉,打著強調民族主義的“美麗國家日本”的招牌,倡導修改憲法,動員“草根保守”階層,迎來了屬于自己的時代。2006年,安倍初登相位后,不僅公開倡導修改憲法,而且啟動了修憲程序,開了戰后歷任首相之先河。與此同時,還將“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修改了否定軍國主義、確定戰后教育根本理念的《教育基本法》等。可以說,安倍在其短暫的一年任期內,在“擺脫戰后體制”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2009年,自民黨的競爭對手、同為保守黨的民主黨,高舉“改革”大旗,并贏得大選,取代自民黨執掌政權。民主黨對外主張“日美對等”、“東亞共同體”,尤其明確表示反對參拜“靖國神社”。一時大權旁落的自民黨,為了標明與民主黨的不同,轉而更加凸顯自身的保守色彩,以迎合日益保守和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選民。冷戰結束后,日本經濟增長停滯、政權更迭頻繁、社會焦慮不安,無形中為狹隘民族主義的迸發提供了溫床。
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在日本造成很大的震動,甚至有人驚呼“經濟戰敗”。中日國力對比發生逆轉,是許多日本人不愿看到、更是難以接受的。無獨有偶,恰在此時,中日釣魚島爭端驟然升級。從釣魚島“撞船事件”,到“石原購島”鬧劇,再到釣魚島“國有化”,中日關系呈急劇惡化趨勢。于是,日本右翼勢力、自民黨內的右派以及部分反華媒體,趁機抓住“中國因素”,大肆渲染“中國威脅”。他們將歷史問題、與鄰國的領土爭端問題以及自身相對實力衰落等問題捆綁在一起,制造來自中國的所謂“外壓”。就這樣,在日本內外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日本政治的“右傾化”愈演愈烈。一時間,日本社會沉渣泛起,各種政治勢力競相“爭右”。一些極右政黨的出現并受到追捧,客觀上促使自民黨越發向右傾斜,日本政壇出現了右翼勢力集結傾向。
需要特別指出的,由一些文化人和專家學者所構成的“文化右翼”,在日本政治右傾化過程中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文化右翼由右翼的文化人和專家學者構成,他們組織各種右翼學術團體,利用大眾傳媒等多種場合,大張旗鼓地宣傳右翼政治主張,極具欺騙性和煽動力,成為日本社會的最大毒瘤。在歷史問題上,甚至叫囂要打“歷史戰”,說什么“主戰場”在美國,“主敵”是中國。①産経新聞社編、『歴史戦』、産経新聞出版、1994年、第193-219頁。在當今日本社會,政壇、文化和民間三個層次的右翼勢力正在形成一種共生與呼應關系,并且右翼的許多政治主張已經或正在轉化為日本政府的政策。
正是在此情況下,日本國內批評和反對皇國史觀的人越來越少、伸張正義的勢力越來越弱,對向戰爭責任謝罪感到厭倦的人越來越多。概而言之,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國內輿論已由以往分裂狀態逐步趨向統一,越來越多的日本民眾開始認同右翼政客的歷史主張。②這僅從日本民眾對戰后70年"安倍談話"的反應便可窺一斑--多家媒體調查顯示,日本多數民眾表示贊成。例如,根據日本共同社于2015年8月14、15日實施的輿論調查,對于安倍談話表示肯定的受訪者為44.2%,不予肯定的為37.0%。同時,安倍內閣支持率也上升了5.5個百分點。“44.2%的日本人對安倍戰后70周年談話表示肯定”,共同網,2015年8月15日,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8/103462.html(上網時間:2015年8月15日)。那種認為右翼政客在日本不受歡迎的言論,一定程度上是對當今日本社會的誤讀。
安倍現政權吸收多位思想上右傾色彩濃重的人士入閣,說安倍政權是日本最右翼的政權一點也不為過。保守意識濃厚的安倍再度執政以來,日本的右翼勢力空前活躍,氣焰更加囂張。在歷史問題上,安倍大搞歷史修正主義,一系列模糊侵略歷史性質,淡化歷史問題的言行,令國際社會頗為震驚。事實上,安倍在歷史問題上向來缺乏反省之意。早在第一屆安倍內閣時期,他就拋出“侵略定義未定論”。此后,他一再對此進行辯解,稱學術界對侵略定義存在各種討論,政治家不應介入。安倍還公然質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審判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竭力為甲級戰犯辯解。他多次聲稱,甲級戰犯在日本國內不是罪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甲級戰犯的審判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單方面定罪。對鐵證如山的慰安婦問題,安倍政權屢屢表示存疑,甚至圖謀推翻。當然,安倍更是積極主張參拜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認為“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是理所當然的,這是首相的責任。”
可以說,安倍晉三兩次問鼎相位,標志著新生代保守派政治家群體開始執掌新世紀的日本。以安倍為代表的這群日本政要,不愿探討和反思日本對亞洲鄰國犯下的滔天大罪,而是反對“自虐史觀”,強調所謂的民族精神和自豪感。當他們崛起成為日本政界的中流砥柱之時,整個政壇的右傾也就難以避免了。
安倍政權不僅在歷史問題上嚴重倒退,更有甚者,還打著“積極和平主義”的幌子,致力于“擺脫戰后體制”,試圖做出更大的“國際貢獻”。2014年7月1日,安倍政府通過了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內閣決議。這意味著日本戰后以“專守防衛”為主的安保政策將發生重大變化。在此基礎上,安倍政權還試圖在國會通過一系列相關“安保法案”。由此,日本的國家形態將發生巨大變化,亦即日本將由“和平國家”轉為“戰爭國家”。因此,人們有理由對日本是否偏離戰后和平發展軌道抱有疑慮和警惕。
冷戰結束后的20年,日本經濟經歷了“失去的二十年”。同時,日本在歷史認識上同樣經歷了“失去的二十年”。我們看到,從“村山談話”到“安倍談話”,日本在歷史認識上不斷倒退。日本與中韓等東亞鄰國之間的歷史隔閡非但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弭,反倒由于日本方面的歷史修正主義日盛而不斷加深。歷史問題已經成為日本發展與鄰國關系的嚴重障礙和沉重負擔。從這個意義上講,日本的當務之急是要彌補“失去的二十年”,與其說是經濟上的,不如說更是歷史上的。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及日本戰敗投降70周年。對于日本來說,這是實現歷史和解、卸下歷史包袱的關鍵節點和寶貴機遇。日本只有正視和深刻反省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那場戰爭,真誠對待歷史問題,以實際行動取信于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才能同亞洲鄰國實現真正和解,并在此基礎上共同發展面向未來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