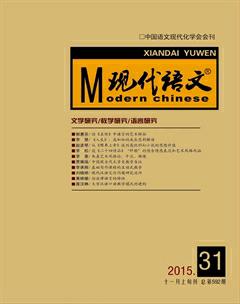《洛麗塔》的敘事藝術與立體主義的審美效果
摘 要:《洛麗塔》是俄裔美籍后現代主義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創作的一部聞名遐邇的絢麗小說。納博科夫采用挑戰世俗的文本主題和獨特的敘事角度,以人物意識流為線索,通過神秘迷離的故事情節、充滿張力的敘事技法、童話意境的詩意語言和唯美主義的藝術追求對人物形象進行工筆描繪,與西班牙畫家畢加索創立的立體主義繪畫所彰顯的“錯位與重疊”“分解與重構”“透視與重塑”的敘事藝術和審美效果異曲同工。
關鍵詞:納博科夫 洛麗塔 立體主義繪畫 敘事藝術 審美效果
俄裔美籍作家拉迪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1899~1977)是20世紀杰出的小說家、批評家、翻譯家、詩人及鱗翅目昆蟲學家。納博科夫是在俄國貴族宮廷長大的最后一代,俄國十月革命后全家流亡德國,并先后在英國、德國、法國居住過二十余年,1940年赴美在多所大學任語言學和文學教授,晚年定居瑞士。納博科夫貴族家庭的教育背景,多國流亡的特殊生活經歷,以及對多種語言的精湛運用,決定了他跨文化的寬廣視野和游刃有余的文學創新。同時,他對國際象棋棋路研究的癡迷,使“游戲”“懸疑”和“探險”成為其作品的個性化標志。對于大自然的向往,使納博科夫把自己比作“沒見過世面的大自然的熱愛者,一個迷失在天堂里的偏執狂”[1],他用一生的時間在大自然中收集并深入研究蝴蝶,以致他的作品也時刻展現著蝴蝶般的絢麗光芒和迷人神采。獨特的成長經歷和對自然科學的濃厚興趣造就了他作為科學家一絲不茍的嚴謹態度,和作為文學家對唯美藝術不懈追求的濃烈熱情。
《洛麗塔》是納博科夫刻意設計的人物與命運不斷糾纏和掙扎的情感悲劇。中年教授亨伯特邂逅并癡狂迷戀12歲的少女洛麗塔,命運的意外使他以繼父和情人的身份深陷與洛麗塔不可自拔的情愛中;這場危險游戲帶來的如影隨形的道德煎熬讓洛麗塔選擇了跟隨劇作家奎爾蒂逃離,奎爾蒂的拋棄使洛麗塔頓悟清醒,向現實妥協,嫁為人婦;故事的結局是奎爾蒂死于亨伯特憤怒的槍聲下,洛麗塔因難產而死,最后亨伯特用生命祭奠了這段短暫刻骨的永生愛戀。
作為20世紀西方重要的藝術流派,立體主義繪畫出現在20世紀早期,追求破裂、解析、重組的藝術表現形式,打破時空的界限,從多角度、采用不同元素來刻畫對象,并將散亂的意象同置在一個畫面中,注重整體的審美效果。《洛麗塔》采用時間和空間的錯位與重疊,敘述視角的分解與重構,人物形象的透視與重塑恰如其分地演繹了立體主義的表現手法和審美效果,用富有節奏的曲式和立體的畫面喚醒人們對現實和生命更深層的思索和感悟。
一、時間和空間的錯位與重疊
《洛麗塔》開篇表明此書是“一個白人鰥夫的自白”,男主人公亨伯特以第一人稱的方式敘述著半癡半醉、夢中囈語般的自白和懺悔,傳記式回憶的倒敘手法將故事和畫面慢慢陳列、徐徐展開。亨伯特對初戀少女安娜貝爾無法自拔的狂熱迷戀,導致了迷失于欲望和時間中的永恒悲劇。敘述情境在回憶和現實中徘徊交錯、在時間和空間里重疊往復,展現出立體主義錯位和重疊的特征。
在亨伯特記憶深處,安娜貝爾是少年懵懂時光的烙印下永遠無法割舍的“心結”,安娜貝爾的因病離世使亨伯特把所有最純真的情感和最原始的欲望“囚禁”在靈魂最深處,在時間的流動中等待著被釋放和救贖。在亨伯特波濤洶涌的意識流動中,時間是一條非線性的斷續軌跡,時間運行的節點是一個個斷層的拼接和重塑。納博科夫曾在自傳中強調了對“時間”的重視:“我承認我不相信時間。我喜歡在用過我的魔毯之后,按照這樣一種方式把它折疊起來,即把一個圖案疊置于另一個圖案之上。”[2]
洛麗塔,在亨伯特口中的“精靈少女”,在時間的折縫中與現實邂逅,亨伯特在見到她的第一眼就無法自拔地深陷其中,情感和欲望在時間和回憶的重疊中瞬間被喚醒并不斷升溫。時間無情地奪走了亨伯特曾經最熾烈愛戀的安娜貝爾,又在不經意的瞬間帶來了讓他無法抗拒的永恒魅惑——洛麗塔。然而,洛麗塔在亨伯特“炙熱、可恥、邪惡的夢境”中的出現不過是在他“飽受痛苦的過去,‘海邊那個小公國的必然后果”[3]。她只是亨伯特期盼已久的超越時間的一個非現實的妄念和幻象。
伴隨著時間的流動和折疊,《洛麗塔》的空間敘事表現為故事場景的交織和轉換。亨伯特敘述和回憶的場景在歐洲、美洲,在海灘、島嶼、叢林、湖泊、平原,法庭、學校、醫院、汽車、旅館等不同背景下不斷進行著交叉和跳躍式的位移,構造了小說空間敘事的迷宮,讓讀者需要不斷從某些蛛絲馬跡中去尋找迷宮的出口和解答。在空間的立方體中,洛麗塔母親黑茲的意外車禍身亡,為以繼父的身份存在于洛麗塔生活中的亨伯特創造了機會,他終于如愿以償地帶著洛麗塔開始四處流浪,擁有兩個人的專屬空間,在多維變換立體空間的每一個側面用相同的激情演繹不同的故事。流浪途中時間的移位感和空間的抽離感營造出一個理想的情境,將人物置于現實空間之外。故事內容在不斷變換的空間中被拉伸、延展出無限張力,“固態空間”展現出“流動的特質”,讀者可以憑借對不同空間的感受任意移動視線的焦點,在跳躍的動態空間中更自由地暢想和更深入地思考。時間的流轉和空間的留白使過去和現在、記憶和現實成為時間鏈條上的中介,以實現多維立體的表現形態。
在另類的時空表現中,投射出亨伯特重返時間、留住時間的妄念,以及洛麗塔挑釁時間、冒犯時間的任性,形成了這部小說縱向的時間脈絡;而亨伯特自述場景、回憶畫面、流亡生活空間的不斷移轉,構成了小說似斷實連、交錯復雜的橫向空間脈絡。縱橫交錯的多維度網狀交織,編織出一種立體主義的敘事藝術和審美效果。
類似的是畢加索創作的立體主義繪畫《亞威農少女》,其創作靈感來源于畢加索少年時期曾在亞威農小街上見到的妓女形象。歷經多年后,畢加索憑借年少的記憶,用成人的視覺眼光和流動的藝術形式記錄下少年記憶中的模糊映像。他同樣采用立體的空間架構,在二維平面中融入了時間的元素,表現出重現時間并超越時間的審美效果,流露出帶有明顯情感痕跡的視覺記憶。畢加索著力用最原始的表現力、流動的視點和審美的意圖將亞威農的少女們分解為各種帶有長度、寬度、高度、深度的“孤立切面”,讓她們在畫面的時間表現下支離破碎,而又將情感延展到畫面周圍的各個空間,凸顯出更為隱蔽的精神特征。他的著眼點,在時間和空間、色彩和形體、心境和感覺中自由穿梭變化。納博科夫筆下亨伯特的心路歷程以及畢加索筆下亞威農少女的創作經歷,都是創作者在用自己的心念不斷挑戰時間,試圖重返時間、再現時間,并在不同的空間視點中,呈現出奔騰跳躍的情感激流,重新喚起理性的思考和渴望重生的靈魂,幻化為紛繁形態的立體形象。
二、敘述視角的分解與重構
在小說中,洛麗塔始終沒有表現出明確的行為或話語,是缺場的主角,是不同敘述視角下的碎片和元素經過多層次重構的形象。在主人公亨伯特囈語中的洛麗塔是自白敘述里隱匿的回憶鏡像,在作者納博科夫創作下的洛麗塔是充滿神秘力量的棋局和謎語,在讀者閱讀體驗里的洛麗塔是歷經層層鏡像的融合和謎語的解答后,被重構的多層次立體形象。
“洛麗塔是我的生命之火,欲望之火,同時也是我的罪惡,我的靈魂。洛-麗-塔;舌尖得由上顎向下移動三次,到第三次再輕輕貼在牙齒上:洛。麗。塔。”[4]亨伯特在小說開篇第一句用破碎音節的內心吶喊和大膽直接的深情告白,表達了他對洛麗塔的如火般熱烈的眷戀和渴望,她的動人、她的柔媚、她的宿命都被賦予深邃的韻味。然而這三個被割裂的音節也注定了洛麗塔支離破碎的情感經歷和錯亂斷裂的心路歷程,意味著亨伯特綿延一生的愛戀、欲望、靈魂以至生命都將被“洛。麗。塔。”這三個溫柔而有力的字句打斷,扭曲拉伸成為折疊的斷層。亨伯特在第一人稱的敘述中,以日記和陳述的形式作為證據,直白地表達出瞬間迸發的內心感受和無法自拔的激動情緒。“一排藍色的海浪便從我心底涌起,在太陽沐浴的一塊草墊上,半裸著,跪著,以膝蓋為軸轉過身,我的‘維埃拉之戀正透過墨鏡向我窺視。”[5]在亨伯特的回憶中,洛麗塔的形象逐步由模糊到清晰——“同樣柔嫩的蜂蜜樣的肩膀,同樣綢子般溫軟的脊背,同樣的一頭栗色頭發”[6]。時間和空間共同構成一面鏡子,鏡子外面是曾經帶給亨伯特真實唯美悸動感受的初戀安娜貝爾,而鏡子里面是在亨伯特的追尋和妄念中投射倒影在時空鏡面的洛麗塔。洛麗塔像是一個被隱匿多年的夙愿和一樁私密的心事,回憶的鏡像被亨伯特書寫的每一個文字、每一種情緒牢牢地包裹籠罩,又以立體鮮活的鏡像被呈現和演繹出來。
作者納博科夫熱衷于“制謎”和“探險”,他坦言自己對《洛麗塔》的偏愛:“我永遠也不后悔自己寫了《洛麗塔》。她就像一個美麗的謎——其創構和結局都像謎:兩者互為一面鏡子,就看你怎么去看了。……那個神秘的寧芙有各種奇特的嫵媚。”“我寫作不是從頭開始寫到下一張,如此寫到結尾的;我只是在填空,整個積木構建我了然于心,這里拿一塊,那里拿一塊,拼出天空的部分,拼出風景的部分,拼出——我也不知道,也許是暢飲的獵人。”[7]整部小說中,納博科夫選擇用大量筆墨刻畫亨伯特復雜多變的心理狀態和晦澀隱喻的靈魂獨白,以人物意識流的此起彼伏來代替對故事情節的深入描寫。小說中,從洛麗塔母親的意外猝死,亨伯特與洛麗塔在各個汽車旅館的危險私情,流浪途中劇作家奎爾蒂的跟蹤尾隨,洛麗塔跟隨奎爾蒂的私奔逃離,亨伯特槍殺奎爾蒂的偵探劇情,到亨伯特由于謀殺罪病死獄中的悲劇結局,其中運用了大量的諷喻、暗指、比喻、象征、戲仿、戲中戲、文字游戲,納博科夫如一個高明的魔法師,與其說他在陳述一部悲劇故事,不如說他在精心編織著一個接一個充滿懸疑的劇情和耐人尋味的結局,使讀者在參與偵查的文本體驗中,探尋神秘莫測的洛麗塔,感受光怪陸離的魔法幻影,領略到藝術的魔力。
在這部小說里,讀者作為傾聽者和旁觀者,是獨立于文本情節外的真實存在;又作為欣賞者和品鑒者在不斷品讀回味著芬芳的詩意語句和色彩斑斕的唯美畫面帶來的藝術質感;同時,作為思考者和游戲參與者而不斷出入穿梭在作品中,和劇中人一起完成這一復雜魔方的復位拼圖。納博科夫嘗試著將熟悉的場景陌生化,喚起讀者的想象力和好奇心,使讀者克服麻木的被動感知。小說中欲言又止的懸疑劇情和處處留下線索的暗示性隱語,需要讀者反復閱讀、仔細琢磨,才能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的字里行間,將斷續的線索串聯、交織成完整清楚的劇情,將洛麗塔零星的影像拼湊成一幅完整的畫面。“《洛麗塔》是一部人物傳記、一部偵探小說、一個浪漫故事、一本游記、一個雙重人的故事、一部喜劇和一部悲劇。”[8]經典總是能經得起時間的打磨,最初的閱讀驚喜隨著時間的沉淀,總能使讀者從再次的閱讀體驗中,感受到作品更加豐富深刻的內涵和深意。
《洛麗塔》是由敘述者亨伯特、作者納博科夫和讀者三重敘述視角共同參與創作的思維流動過程,用個性化的藝術感覺調動著讀者懶惰的被動式閱讀,敘述視角的不斷移動和轉換構成了故事完整的敘事層,將作品中的意象、情節、語言等元素綜合在一起,就如同在立體主義繪畫藝術作品中線條、構圖、色彩等構成的完整畫面。“在呈現獨特審美效果的立體主義繪畫中,創作者們將不同心理狀態及不同視點所觀察到的對象,集中陳列于單一的平面上,造成總體經驗匯聚的效果,他們強調畫面的自給性和整體性,認為每一幅作品都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系統,要求讀者體會繪畫的過程以取得對于作品完整的認識和理解。”[9]
三、人物形象的透視與重塑
洛麗塔的出現是幻影也是現實,洛麗塔的悲劇是偶然也是必然。洛麗塔以亨伯特回憶中的幻影形象出現,又作為現實中的少女經歷了任性時的自我放縱和覺醒后的自我救贖。在亨伯特精神世界的虛構和幻覺中,“我瘋狂地占有的并不是她,而是我自己的創造物,是另一個想象出來的洛麗塔——說不定比洛麗塔更加真實,這個幻想與她重疊,包裹著她,在我和她之間漂浮,沒有意志,沒有知覺——真的,逼真并沒有生命”[10]。同時,洛麗塔又是有著強烈自我意識的立體存在:她是青春期在野營地熱衷于放縱游戲的叛逆少女,有著天生的張揚任性和滿心好奇;是迷茫困惑時受到劇作家奎爾蒂誘惑而跟隨他逃走的天真少女,有著對情感的非理性期盼和熱切渴求;也是徹悟覺醒后嫁作人婦而踏實、平和的重生少女,有著道德反省后的自我認知和自我救贖。
洛麗塔的悲劇起源于一個不完整的單親家庭,開始于一場宿命的相遇,糾纏于一段道德的迷失,結束于靈魂失衡后的涅槃重生。對于洛麗塔來說,長期缺乏父愛并且有強勢母親的嚴厲管束,使她的性格叛逆而任性張揚。或許是宿命,或許是某種長久的期盼,與亨伯特的邂逅,成為她父愛缺失的情感補償,也滿足了她對于成熟男人懵懂好奇,同時是她對于自我存在的某種證明。然而,熾熱夢幻的激情難以掩飾內心道德的譴責和激情過后的負罪感,這樣一段刻骨叛逆的經歷成為了她超脫命運的洗禮。
在《圣經》的“失樂園”中,“原欲”和“原罪”在“智慧樹”下被共置,人類由于沒有控制住欲望而偷食了禁果,對禁果的無法抗拒是人類的“原欲”,人類偷食禁果滿足了“原欲”的同時也導致了“原罪”的產生,從此人類有了自我覺知和理性意識、有了道德觀念和羞愧感受,于是不得不踏上對“原欲”和“原罪”的永恒救贖之路。而與“失樂園”不同的是,《洛麗塔》的自我救贖不只是由于道德羞愧,還有更為深刻的自我剖析和反省,以及對重生的強烈渴望。洛麗塔放縱青春的“原欲”,偷食禁果的“原罪”,都付出了沉痛的代價,需要刻骨的傷痛來償還和贖罪,她終于在道德的迷途中找到了出口,完成了自我救贖。洛麗塔有著古靈精怪的外表,又有著蝴蝶幼蟲般稚嫩的內心,似乎只有經歷過情感缺失的補償和人生宿命的磨難才能破繭成蝶,得到靈魂的成長和身心的自由。
在對“我是誰”的反復追問中,總是需要歷經許多迷茫,才能發現自我存在的意義,最終得到心靈的回應和解答。洛麗塔扣人心弦的生活經歷和糾結迷茫的心路歷程,在復雜多變的現實生活背景下,透視出分裂矛盾的精神特質。納博科夫在作品中刻意制造了一環套一環的懸疑情節和撲朔迷離的變換場景,使人物在糾結和選擇中不斷完成不同側面的全方位自我透視,在掙扎中一步步完成價值觀的重塑,實現自我救贖。“洛麗塔”好像是納博科夫精心孕育的一只蝴蝶,棲息于現實和虛幻間的詩意世界中,在經歷了懵懂任性和悲痛失望后,破繭成蝶,獲得了靈魂的解脫和自由。
《洛麗塔》描繪了人類與真實自我相遇時的投入、沖突和覺醒,其中蘊含著悲劇感。而畢加索的立體派繪畫《鏡前少女》,借鑒非洲面具的立體藝術形式,不故意逃避、不刻意美化,也真實呈現出形式和意蘊上的獨特審美韻致。洛麗塔在不斷找尋真實的自我,《鏡中少女》也在反復打量著鏡中的自己,她們都在反觀最本真和親密的真我。少女總是會選擇在鏡子前面精心妝扮,探知窺視著最隱蔽和真實的自我,試圖從鏡中探測到自己最佳的姿態和最需遮掩的缺陷。正如畢加索所說:“我要同時表現的就是少女裸體、著衣和X光透視三種狀態。”[11]畢加索用最原始的表現力將二維平面開拓出不同空間,將人物呈現出立體感形態,正面、側面、背面、鏡面及鏡子內部這些不同平面,都有著不同的線條、構圖和色彩等元素,當這些破碎的元素被刻意拼貼和有策略地重塑后,給讀者展現出必須經過慎重思考后才能得到的審美效果。
四、結語
納博科夫有著復雜而特殊的生活背景和人生經驗,對文學、藝術獨特的審美見解,他通過迷離幻美的意象,奇幻魔術般的情節,編織出獨樹一幟多重涵義的《洛麗塔》,折射出獨特的實驗色彩和創新精神。納博科夫在創作中擺脫現實世界和世俗道德的禁錮,嘗試以創新的寫作形式,采用靈活多變的敘述技巧,對小說結構進行全新的構思和精妙的布局,運用創造性的語言風格,破解人生隱蔽的謎語,被譽為“美國實驗小說的最有影響的先驅”[12]。納博科夫筆下的《洛麗塔》與立體主義繪畫崇尚移動視角,在平面空間雕琢時間,以抽象演繹具象,用破碎重塑完整的藝術表現形式共同形成了藝術的和諧音調和流暢曲式。無論《洛麗塔》還是立體主義繪畫,其多變的風格,大膽的創新,象征的鏡像,多重的透視,理性的構圖,都不斷喚醒著人們對生命本質的探尋與思索。
注釋:
[1][7]潘小松譯,納博科夫:《固執己見》,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2]陳東飆譯,納博科夫:《說吧,記憶》,吉林:時代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3][4][5][6][10]主萬譯,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洛麗塔》,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版。
[8]李公昭:《20世紀美國文學導論》,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40頁。
[9]胡英:《伊麗莎白畢肖普詩歌與立體主義繪畫》,大連學院學報,2010年,第11期,第31-33頁。
[11]時代文藝出版社編:《畢加索畫傳》,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頁。
[12]伊哈布·哈桑:《當代美國文學》,世界文學,1987年,第5期,第84頁。
(王榮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英語學院 10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