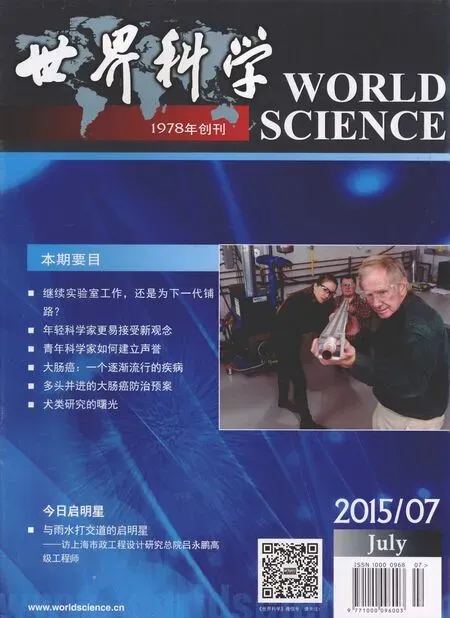抵抗癌癥
蔡立英/編譯
抵抗癌癥
蔡立英/編譯

●如果三個人中有一個人得了癌癥,就說明其他兩個人沒有得癌癥。理解這其中的原因對預防和治療癌癥會帶來啟示。
癌癥是人類的災難,而且隨著人類壽命的延長,將會影響越來越多的人。大約三分之一的人在其一生中會罹患腫瘤性疾病,但是反過來說,還有三分之二的人不受癌癥影響。即使是大多數重度吸煙者,其肺部長年累月吸入致癌物和促癌物,仍然不會得癌癥。自然而然,癌癥患者及其家人的痛苦激發(fā)了研究者去研究癌癥特有的細胞變化和癌癥易感性的遺傳學。抗癌性的遺傳學這個課題本身,基本上還未被探索。
病理學家已經表明,實際上所有60歲及以上的人在驗尸檢查時都會發(fā)現微觀的前列腺癌,但是,這些微腫瘤大多數都不會發(fā)展成癌癥。大家知道,擴散的癌細胞會遍布大部分癌癥患者的全身,但是只有小部分這樣的癌細胞會發(fā)展成繼發(fā)性腫瘤,其余癌細胞都會被身體控制住。
確實,后生動物進化已經導致了很多調適,以保護整個動物王國的物種免受惡意細胞的侵害。免疫監(jiān)視在防御病毒相關腫瘤方面發(fā)揮著重大作用,病毒編碼的轉化蛋白提供了易于識別的外來標靶。但是由異常的宿主細胞構成的非病毒性腫瘤并不會提供這樣的外來標靶,免疫應答被針對自身免疫反應的防御抑制了。反而,我們現在知道了抗擊癌癥的主要防護措施根本不是免疫學措施。
若干種抗癌機制似乎已經演變?yōu)榫S持細胞或基因組的完整性。例如,正常的基質——支持一個組織的細胞的連接物質,似乎會抑制腫瘤生長。其他抗癌機制包括DNA修復、抑制致癌基因活化、腫瘤抑制基因、染色質結構的表觀遺傳穩(wěn)定化以及細胞凋亡。這些機制都得到了深入研究,每一種機制都為癌癥的預防和治療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路徑。
遺傳監(jiān)督
異常的細胞分裂是腫瘤細胞的標志,負責這種細胞異常增殖的突變基因就被稱為癌基因或致癌基因,但這其實是用詞不當。它們的正常功能不是導致癌癥,而是參與正常細胞分裂的調控。同時,命名得更合適的腫瘤抑制基因識別了這種增殖驅動基因的非法活化,從而踩下剎車加以抑制,破壞這種功能的基因突變又會再次導致癌癥。
罹患腫瘤的風險也可能受到那些控制DNA復制的忠實性、DNA修復功效的基因以及涉及DNA合成和染色體結構的檢查點調控的突變的影響。例如,著色性干皮病源于一種特定的DNA修復缺陷。這種病癥最主要的形式是由核苷酸切除修復系統(tǒng)的一種基本成分的隱性突變引起的,核苷酸切除修復系統(tǒng)的主要功能是切除因皮膚上皮暴露于紫外線而引起的分子DNA損傷。著色性干皮病患者必須終生保護自己免受陽光照射,但是他們仍然還是會罹患多種皮膚癌,而且大約三分之一的患者同時還會發(fā)生進行性神經系統(tǒng)異常。這突出了DNA修復作為一種前線監(jiān)督機制的至關重要性。
但是另一組與癌癥形成有關的基因調控著程序性細胞死亡或凋亡。這些基因表達的蛋白質的正常功能是識別那些必須被消除的多余、損壞、老化或異常的細胞。細胞凋亡的重要性可以由脊椎動物的適應性免疫系統(tǒng)來舉例說明,其中的B淋巴細胞,因為它們是從它們的前體細胞分化而來的,重新排列了免疫球蛋白基因的DNA,以產生潛在的大量抗體。如果一個抗體碰巧識別出體內的一個抗原,產生它的B細胞會受刺激而克隆性地擴張。但是,那些產物不綁定相應抗原的B淋巴細胞則必須死,以避免堵塞系統(tǒng)。攪亂組織完整性的潛在的癌細胞也會誘發(fā)啟動細胞凋亡的信號。只有當凋亡機制功能受損時,癌癥才會發(fā)生。
那些通過突變、非法活化,或是相反地,失活或減損而導致癌癥發(fā)生的基因,在所有哺乳動物中幾乎是相同的。許多這樣的基因甚至在血緣關系遙遠的種群中得到保留,比如果蠅、線蟲和酵母。而且,這些癌癥相關基因在不同物種中發(fā)生突變的頻率相似。因此,我們本來可以預計,擁有1017個細胞的藍鯨比只有109個細胞的老鼠或是只有1013個細胞的人類得癌癥的頻率要高。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實際上藍鯨極少得癌癥,即使真的得癌癥,似乎也能夠安然度過一個完整的生命周期。事實是腫瘤發(fā)生的頻率并不隨著組成一個動物的細胞總數的增加而增加,這表明某種系統(tǒng)控制正在預防癌癥發(fā)生。即使典型的實驗室動物在癌癥易感性上也是各不相同的。小鼠、大鼠和倉鼠相對容易得癌癥,而兔和豚鼠抗癌性相對較強。在癌癥頻譜的遠端,兩個鼴鼠物種已被發(fā)現是完全不會得癌癥,盡管它們壽命相對較長。
在抗癌性方面,人類之中會有遺傳學差異嗎?這一點沒有證據,但是很有可能存在。在家族譜系圖保存完好的冰島家族,有若干這樣的例子:六個或更多長壽的兄弟姐妹沒有得癌癥,而且他們的父母沒有死于癌癥。但是,我們不可能把遺傳性抗癌家族的存在與純屬偶然的無癌家族的出現區(qū)別開來。
有趣的是,人類腫瘤發(fā)病率隨著年齡的急劇上升之后,會在80-85歲迎來腫瘤發(fā)病率的下降。百歲老人極少會得新的癌癥。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群體中的癌癥易感個體已經死掉。免于癌癥可能是活到高齡的一個必要的但其本身并不充分的先決條件。
患有一種稱為“拉龍綜合癥”的侏儒癥的人代表了抗癌性人類的另一個有記載的例子。在近親結婚頻繁的厄瓜多爾人口中發(fā)現的拉龍綜合癥患者的骨骼、軟骨或關節(jié)發(fā)育都沒有問題,而且與其他侏儒相比,具有非常高水平的生長激素。但是,他們的細胞缺乏使生長激素發(fā)揮功能活性所需的一種受體。生長激素受體基因的一種不常見的突變似乎是這個案例中的抗癌性的原因。
似乎有多種機制能防御癌癥。除了驅使癌細胞增殖、突變或表觀遺傳學變化可能會影響細胞入侵相鄰組織的能力,從而引起全身轉移或抗拒治療。值得注意的是,利于轉移的突變可發(fā)生在腫瘤發(fā)展的非常早期的階段,遠遠早于有足夠數量的腫瘤細胞從而表現出癌癥屬性之前。

表癌癥的遺傳學原理
相鄰抑制
20世紀60年代,英國癌癥生物學家邁克爾·斯托克(Michael Stoker)觀察到一個意想不到的現象:當他把一定數量的腫瘤細胞移植到盛有適量營養(yǎng)物的培養(yǎng)皿中時,他獲得了大約100個很小的正在生長中的腫瘤細胞集群。但是當他把相同數量的腫瘤細胞跟正常的成纖維細胞混合時,正在生長的腫瘤細胞集群的數量減少了99%。似乎正常的相鄰細胞抑制了腫瘤細胞復制的能力,這種現象后來被稱為接觸抑制或相鄰抑制。
黏著連接是存在于上皮和內皮組織中細胞與細胞之間的接觸點的蛋白質復合物,似乎在這一現象中發(fā)揮重要作用。E-鈣粘蛋白是在這些連接處的重要黏附介質,在大多數上皮性腫瘤中會被下調,通常是通過基因的啟動子區(qū)的甲基化。E-鈣粘蛋白的再表達似乎會抑制孤立的癌細胞中的轉化表型,而阻斷E-鈣粘蛋白的功能則會增強癌細胞的入侵。
細胞膜的其他結構成分可以類似地參與到腫瘤生長的微環(huán)境抑制。β-整合素是介導細胞與細胞外基質(ECM)以及細胞之間相互連接的跨膜受體的亞單元,也在組織構成中發(fā)揮關鍵的信號轉導作用,而且經常被腫瘤細胞異常表達。用抗體標靶腫瘤相關的β-整合素可以抑制腫瘤生長。Notch信號通路中調節(jié)細胞分化和增殖的成分,是另外一個例子。Notch受體或它們來自小鼠表皮基底層的配體的缺失,可導致表皮增生和皮膚腫瘤。
幾年前,我們用綠色熒光蛋白標記人類前列腺癌細胞,并對與不同組織的正常成纖維細胞相鄰的細胞進行電鍍,重新研究了相鄰抑制在抗癌性中的作用。皮膚中的成纖維細胞對腫瘤

相鄰細胞如何對抗癌癥:抵制惡性細胞在體內的過度增殖涉及癌癥相關基因之間的復雜的相互影響,微環(huán)境,以及組織建立正常結構的傾向。在身體的防御機制中有一種現象叫做接觸抑制或相鄰抑制,指的是當細胞感知到其密度達到一個臨界值時會停止生長
生長有強烈的抑制作用。當腫瘤細胞沒有被殺死而持續(xù)大量生長并制造蛋白質時,它們不會分裂。另一方面,從發(fā)生癌變的前列腺中提取的成纖維細胞幾乎不抑制細胞增殖。事實上,這些所謂的癌癥相關成纖維細胞(CAFs)可能甚至會支持相鄰的腫瘤細胞的生長和存活。更嚴密地觀察這些成纖維細胞中的基因表達,我們鑒定出通過炎癥或創(chuàng)傷愈合而被活化的基因,這一發(fā)現與一個既定事實一致:炎癥有利于往往是長期處于非活化狀態(tài)的腫瘤細胞的生長。
重置癌癥
另一種抗癌機制于20世紀70年代被美國生物學家比阿特麗斯·明茨(Beatrice Mintz)發(fā)現。在研究一種高度惡性的畸胎瘤細胞的過程中,明茨發(fā)現皮下接種該細胞的成年小鼠全部死于畸胎瘤。但是,當畸胎瘤細胞被導入非常早期的胚胎時,并不會發(fā)展成惡性腫瘤。導入的細胞只是成為組織的一部分,參與到小鼠的正常發(fā)育,并對胚胎的很多組織做出貢獻。正常化的腫瘤細胞甚至有助于受體小鼠的精子生產。
在早期發(fā)育環(huán)境中的胚胎腫瘤細胞的正常化是惡性細胞分化成正常細胞的極端例子。在后來的研究文獻中,還有很多其他沒這么驚人的例子。高度惡性鼠白血病細胞可被天然或人造物質誘導分化成非惡性細胞。人類白血病的一種——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APL)常規(guī)的治療方法是:一種天然存在的信號受體與憑經驗確定的化合物——染料木黃酮的組合,會誘導癌變細胞從粒性白血球前體分化成不能再分裂的成熟中幼粒細胞。盡管類似的例子仍然相對稀少,它們表明了大多數也許所有腫瘤都可以被誘導進行分化并停止生長,如果科學家能找到誘導物的合適組合。
生物進化給我們人類和其他動物提供了阻止正常細胞進行失控分裂的多重機制。如果正常細胞還是逃脫了控制,細胞會發(fā)動多重機制來阻止惡意細胞,并保護正常的組織結構。這些機制能把威脅生命的惡性細胞生長消滅在萌芽狀態(tài)。只有在正常組織的周圍已經被腫瘤細胞敗壞之后,細胞才不能阻止而是刺激惡性細胞生長,腫瘤才能肆無忌憚地橫行霸道。
[資料來源:The Scientist][責任編輯:彥隱]
無癌的生命

盲鼴鼠裸鼴鼠
有兩種鼴鼠是抗癌性的特例。盲鼴鼠(BMR)和裸鼴鼠(NMR)能分別活到20和30歲而從來不會得癌癥。理解賦予這些動物如此強大的防御癌癥的分子機制,能為抗擊人類癌癥帶來啟示。
裸鼴鼠是一個完全社會性的物種,生活在高度組織化的母系氏族社會,必須在狹窄而且經常蜿蜒曲折的地下隧道中前進。其皮膚的結締組織包含透明質酸的高分子量形式(HA),HA可使動物的皮膚延展性如模型粘土。小鼠和人類體內對應的HA的分子量只有裸鼴鼠HA的不到五分之一。存在于裸鼴鼠體內的高分子量形式的HA阻止了正常細胞轉化成癌細胞;只有消除它,裸鼴鼠的細胞才能轉化成癌細胞。
而且,裸鼴鼠的成纖維細胞抑制了接觸抑制的一種非常形式。小鼠和人類成纖維細胞在撞上其他細胞時,會抑制它們自身的繼續(xù)增殖。裸鼴鼠的成纖維細胞會更早地這么做,當細胞幾乎沒有相互觸碰時。當細胞發(fā)生接觸時,一種涉及導致生長停滯的蛋白質——p16蛋白被上調了。在小鼠和人類成纖維細胞的后期接觸抑制中看不到p16蛋白,而是另一種生長停滯蛋白質——p27蛋白被上調了。
與裸鼴鼠相比,盲鼴鼠是一種孤獨的、非社會性的、具有侵略性的物種,其抗癌機制與裸鼴鼠并不相同。盲鼴鼠沒有高分子量形式的HA或早期接觸抑制,但是當它的成纖維細胞生長到匯合時,會通過釋放一種干擾素進行集體自殺。生物進化似乎再一次制定了控制惡性細胞的多樣化的解決方案,而在這兩種無癌的物種中,那些機制也許是它們驚人長壽的關鍵。
本文作者喬治·克萊恩(George Klein),在瑞典卡羅琳學院的微生物學、腫瘤與細胞生物學系研究愛潑斯坦-巴爾病毒,致癌基因和腫瘤抑制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