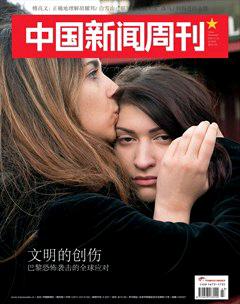斯帝文·鄧:中國或可在5年內全面脫貧
賀斌
對內塔尼亞胡而言,煽動是一種強大的政治手段。然而,今天的叛亂顯示了這種方法所隱含的危險因素。激起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人的恐懼和不滿不僅破壞了政治解決的機會,同時還加劇了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人的失望和憤怒。
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提出的目標要求,“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
“中國已經足夠富有,只要合理利用資源是完全可能在2020年前實現全面減貧目標的。” 斯帝文·鄧對此評價說。
11月6日~8日,2015年北京論壇召開,這次論壇的主題是《不同的道路和共同的責任》,英國政府國際發展部首席經濟學家、牛津大學教授斯帝文·鄧作為嘉賓發表了主旨演講。他高度評價了中國的扶貧工作,認為中國在實現世界千年發展目標和將貧困率減半的目標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斯帝文·鄧是發展經濟學家,從2004年起擔任牛津大學經濟學系教授以及劍橋沃爾森學院的研究員,致力于全球貧困及反貧困工作的研究。他同時也是英國政府國際發展部首席經濟學家,主要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展開扶貧研究并制定政策,以此提高各類經濟發展政策的有效性以及評估標準的可實施性。
11月8日,斯帝文·鄧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對中國的扶貧工作,以及中英經貿合作等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與斯帝文·鄧接觸過的人,都會評價他是一個很友善的人。他總是一臉燦爛的笑容,也會適當減慢語速以便于溝通。可能是長期從事減貧和對非洲研究的緣故,他言談中不時流露出濃濃的人文情懷。這是他第一次參加北京論壇,他表示,北京論壇對于學者,特別是對于國外學者來說是個很好的交流機會,能夠聆聽中國學術界對一些問題更加公開自由的討論。

斯帝文·鄧。圖/受訪者提供
要實施更有針對性的扶貧
中國新聞周刊:作為一名長期從事扶貧研究的經濟學家,如何評價中國的扶貧工作?
斯帝文·鄧:中國近二三十年來在減貧方面的紀錄令人贊嘆。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的時候,中國還存在嚴重的極端貧困的問題。比如,90年代的時候,把所有的世界的貧困人口的名字放在一起,隨便抽取一個,可能的就是中國人,因為中國當時貧困人口最多,而當時在整個東亞地區可能有10億人陷入極端貧困當中。
然而到了2015年,這一數字變成8300萬人,雖然人數依然很多,但我們還是要看到成就是非常明顯的,而這其中,中國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中國現有貧困人口7000多萬,執行的標準是年人均純收入2300元,高于世界銀行的標準,消除貧困的時點也比聯合國提出的目標早了10年。
這些年,中國經濟取得了快速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也提升了人民的收入,減貧成就舉世矚目。
但是,要降低貧困率不能只是發展經濟,對于一些特殊的貧困人口,如邊遠地區的人、老人孩子等弱勢群體,以及就業困難群體,需要實行多樣化的扶貧政策,如養老金、社會保障等。在這些方面,中國已做了很多努力,但要實現到2020年全面消除貧困的目標,還需要實行更全面、更有針對性的政策。
在這一方面,很多國家已經有一些成功的經驗,但不知道是否適合中國。不過,我認為,中國已經足夠富有,只要合理利用資源,是完全可能在2020年前實現全面減貧目標的。
中國新聞周刊:離2020年中國全面消除貧困的目標還剩不到5年時間,你認為完成這一目標最大的挑戰是什么,中國政府應該如何應對?
斯帝文·鄧:我認為,現在中國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較少,因此需要更有針對性的行動來應對。
在過去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的進程中,中國的貧困人口在縮小城鄉差距、提高收入和增加就業機會等方面已經取得了進步,但是僅此還不夠。現在很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哪些群體是貧困群體,有些貧困人口可能是老人、無法工作的弱勢群體,還有邊遠地區的農民或城市里找不到工作的困難人群等,針對這些群體需要有些特殊的、專門的扶貧項目。
中國新聞周刊:這些更有針對性的減貧措施具體包括哪些?
斯帝文·鄧:比如針對一些貧困的老人,可以提高養老金水平和一些現金轉移支付;針對一些城郊地區的就業困難群體,可以提供一些更加集中的教育項目和技能培訓;針對一些特殊的移民群體,可以有一些更好的教育和健康的資源等等。
在這些方面,中國已經有一些相關的政策,但仍有改進的空間,對一些項目的效果還需要作出評估,從而作出具體的、有針對性的改進。
除了經濟發展以外,中國還需要各種類型的項目而不只是一個項目覆蓋各種人和地區,我認為中國有足夠財力做這些。
中國新聞周刊:在中國的“十三五”規劃建議中,提出探索“資本扶持收益制度”,在你看來,這種制度能否有效化解貧困,實現收入分配的公平?
斯帝文·鄧:這個政策現在很復雜,不能簡單判斷效果如何,必須要一些高水平的、實際的成果,來看是否有效。中國一直在實驗和試點方面做得很好,但當問題變得更加復雜之后,在學習試點方面就會變得更加困難,因此需要更多證據來支撐。
理論上,這種政策對農民群體是有利的,但不知對特殊人群,比如老人孩子等群體是否有利;對收入公平會有一些貢獻,但不確定是否是唯一的解決辦法。
無論如何,對一項制度,我相信證據的效力,光看理論是不夠的。
競爭或合作,對中英都是機會
中國新聞周刊:不久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英國進行了國事訪問,可以看出,英方對這次訪問給予了高度重視,你認為,加強和中國的經貿合作將會為英國帶來哪些利益?
斯帝文·鄧:英國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體,歡迎來自全世界的外部投資,中國有很多很好的高效率的企業,英國很愿意通過這次國事訪問,加強引進中國相關的投資合作意愿。
英國歡迎互相的獲利,中英相互出口彼此喜歡的東西,中國也有很多機會引進英國的投資和合作,雙方可以進行更多的合作。
中國新聞周刊:此次中英雙方簽署了數十項合作協議,總金額高達400億英鎊,特別是在高鐵和核電等大的項目上都有合作,你認為,中國和英國的合作,主要是技術輸出還是資本輸出?
斯帝文·鄧:我認為,在合作時雙方并沒有特別區分是技術還是資本、專家等方面,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有著很好的經驗,引入英國將會更有效率,并且英國可以提供很好的服務。
中國的企業競爭力很強,英國和中國在高鐵等方面的合作重點不是因為技術之類的因素,而是因為中國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可以運用一些很低的成本高效運作一些產業。這也是開放經濟的一個優勢,你可以去引進其他國家的優點,也可以向其他國家輸出本國的優點。
中國新聞周刊:有人說,中英關系迎來了新的黃金時代,你如何看待未來10年中英兩國的經貿關系?
斯帝文·鄧:現在對于中英雙方來說,都有很多機會。對英國來說,可以進行海外投資,自己生產的產品還可以出口,從而克服國內生產方面的壓力;對中國來說,利于更開放的經濟和同世界更多的交流。因此,中英兩國無論是競爭還是合作都是很好的,都有很多機會,希望以后在英國能看到更多的中國企業,也能在中國看到更多的英國企業。
因為我本人是在英國政府國際發展部工作,從我個人來說,希望中國和英國將來能在一些貧窮地區,比如非洲共同開展工作,希望兩國今后在這一方面可以有更多的學習和交流:英國向中國學習發展方面的經驗,也希望向中國提供一些英國發展的經驗,以及在對非洲投資和援助的經驗。
非洲對中英兩國來說都有很好的經濟機會,但兩國需要合作來解決貧窮、沖突等大的問題,也可以幫助當地經濟發展,使非洲發展成一個平等的經濟體。實際上,習近平主席在這次國事訪問的過程中,兩國也探討了一些國際合作發展方面的問題,以后可以在這些方面進行更多的努力。
中國新聞周刊:目前對非洲的投資主要是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除此之外,你認為中英還可以在哪些方面開展合作?
斯帝文·鄧:首先,中國在非洲地區基礎設施領域的援助工作做得非常好。其次,對于很多非洲國家來說,還存在一些沖突,以及減貧能力有限等問題,在這些方面,中國可以提供一些建議和幫助,使他們在運行水平方面能夠得到更好地提升。非洲如果能夠引進并參考中國在發展中經歷的經驗,可能會在社會管理、教育、醫療方面都會有很好發展。
實際上,中國在這些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我們看到,中國在塞拉利昂的醫療工作人員,幫助控制住了埃博拉疫情,我們也看到在尼泊爾地震之后中國在救援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經濟發展固然重要,但我們也要在其他領域扮演一些角色,通過經濟合作,為消除地區貧困作出貢獻,確保世界上每個人都從中獲取利益。
很多的國際援助體系都在思考人道主義援助這個重要問題,想要改善這個方面的工作。當然,這一切都應該放在發展和挑戰的大框架下來考慮。
(羅玲 鐘雪 陳燕鳳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