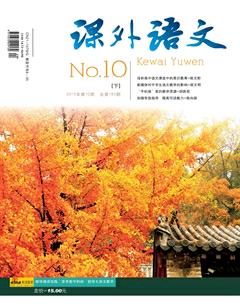建構與消解:論葉兆言小說《白天不懂夜的黑》的語言特點
孫愛琪
【摘要】葉兆言小說《白天不懂夜的黑》發表于《人民文學》2014年第7期,以第一人稱“我”的視角敘述了老師皆友人林放——一個典型在市井沉浮的文人——跌宕起伏的一生。建構了“二十世紀末文學和文人社會位置的變遷”的嚴肅話題,又以語言逐一消解。本文即從“句式中的語言”和“敘述中的語言”兩個不同角度來論述該小說敘事的語言特點。
【關鍵詞】葉兆言;小說;語言;建構;消解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讀者往往是粗心大意的,在小說閱讀過程中跟隨著作者所設置的故事情節一波三折迂回前進,對語言視之默然,這當然也是無心之失。一部小說,語言若寫得好,則與情節渾然天成,讀者便難分彼此;若寫得不好,讀者自然批評小說或是佶屈聱牙,或是零散拖沓,理由始終也尋不到語言身上。這就是語言,它是一部小說唯一的、原始的呈現形式,卻在讀者眼中隱秘而不可見;它是一部小說完成敘述的唯一工具,卻又在情節敘述完成后悄悄隱退。可以說,語言是小說隱藏的靈魂,語言的每一字句都操縱著情節的某些部分。評點一部小說,若看不到語言中的珠璣,都是徒勞無益。
學術界對葉兆言小說的語言有著一個公認的評價——冷靜從容而略帶幽默色彩。這個評價從葉兆言小說中總括而出,是從具體作品中抽象出的普遍公理。但這樣的公理又包含著特定的價值,在不同的小說中以不同的語言形式呈現,當離開作品而談論時,其實已經失去了意義。例如,余華的小說語言同樣可以說是“冷靜從容”“帶有黑色幽默”的,但與葉兆言的語言又可謂千差萬別。余華的冷靜是表面的,在其小說中的人物好似一對處于冷戰中的夫妻在談話,表面客觀、冷靜,毫無嫌隙,內里卻是情感的暗潮涌動,情感通過語言,又在語言之外到達人物的內里,進而也達到讀者的內里。葉兆言的“冷靜”則是表里如一的,通過將敘述時間拉長,把人物郁積的情感都一一分散、再淡化,不論是夫妻、朋友、仇敵還是陌生人,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都是一個交往了上百年后“通透”的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種冷靜,與其說是“零度的語言敘事”,倒不如說是三十七度五的“恒溫”敘事。
《白天不懂夜的黑》并非一篇精妙絕倫的上乘小說,也算不上葉兆言作品中的佼佼者。但可以說是一篇在語言文字上頗下功夫的老手之作:有著深刻的人生觀、真實的生活體驗、迅速的觀察、敏銳的感悟,經過長期艱苦的訓練,又以精熟的文字技能調配,從而達到所有在追求天才的路上而成為人才的那種境界。
一、句式中的語言:俗語、俚語多重方式的借用
所謂“句式中的語言”,即是以語言學為出發點,討論語言的形式,并研究在使用這一形式時所產生的效果。葉兆言在這篇小說中借用了大量的俗語俚語,甚至改用一些俗語、俚語以達到消解文本立意嚴肅性的效果。這些俗語的使用有的符合本意,有的卻與本意相悖。俗語、俚語乃是民間智慧的抽象結晶,它代表著市井民眾的平均心智,在文意上講,“原意借用”是對市井生活的肯定和迎合,“逆意借用”則是對現實已經天翻地覆而觀念卻依舊原地踏步的現狀的嘲諷。在語言上講,小小的俗語短語的插入,大大地改變了句式的節奏。一切藝術形式的歸根結底都是“節奏”,語言也不例外。
小說中所使用的一些俗語、俚語:“兔死狐悲,唇亡齒寒”“生命誠可貴,愛情價跟高”“貧賤夫妻百事哀,人窮萬事難”“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人走茶涼,時過境遷”等等,使葉兆言的小說語言不僅色彩濃重,而且工整、節奏勻稱、上曰悅耳、從容不迫。葉兆言的這篇小說里多的是使用這種疊加、遞進、加強的短語表達,看似不經意的安排同樣也會被讀者不經意間忽略。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重復加強式的語句中,小說中人物的氣勢隨之增強,但作者似乎仍置之事外,依然冷靜從容。
葉兆言小說中的那種超然、平靜、客觀化的,將情感降到零度的語言風格已經為讀者所熟悉。而葉兆言的小說語言之所以冷靜從容而略帶幽默色彩,是因為他敘事多采取連續使用意義相近或相關的四字俚語短語的方法。
二、敘述中的語言:嚴肅立意又被消解的敘述
所謂“敘述中的語言”,即是以小說敘事學為出發點,討論語言內容在小說敘事過程中所發揮的共用。他在漢語的詞匯、句式、修辭等方面對語言加以錘煉,形成了一種冷靜從容而略帶幽默色彩的語言風格。
小說中有這樣一個情節,朋友們為了安撫剛離婚的林放,在一家名為“黑森林”的餐館請客。他們吃完飯后結賬,林放掏出一張特約記者證與服務員商量著打個折扣,服務員不算事做不了主,于是請出了老板:
不一會兒,老板一本正經地出來了,非常誠懇地問哪位是記者同志,點頭哈腰地又問味道如何。我們異口同聲,一邊將林放推出去,一邊稱贊說菜還不錯,說廚師手藝很好,只可惜價錢稍稍貴了一點。老板看了看林放,說能覺得菜不錯就行,我這兒呢講究的就是一個質量,換了別人,我真可以給你們打折,可是晚報的記者,這個就對不起了,我是一分錢折扣也不會打。
老板又說,我這兒就是不給報社的記者打折,不打折就是不打折,你們總不能為這個再投訴我們吧?別人都說要防火防盜防記者,做生意的都害怕你們,我不怕,老子就是不怕。
這種近于“黑色幽默”的表達方式,時常是在作家不動聲色的平靜語體敘述中完成的,作家采用的是一種“冷面滑稽”的藝術手法,把可怕與可笑的語言材料組合在一起,模糊了悲喜劇之間的界限。作家消除了悲喜劇的界線,使得小說在多重的復義中產生更大的潛在功能。作家不動聲色,一本正經地把這一切當作正常的東西呈獻給讀者,而讀者在領悟了其潛臺詞完全對立的含義后,禁不住便露出一個苦澀的微笑。這種反諷兼夸張,把讀者從一種驚喜的情景中引入對于人生和社會病態的深刻思考之中。他在敘述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將人的抽象的情感嵌入了具有知覺化和具象化的動態過程之中,從而使抽象的情感具有了某種感性的生動。然而,透過“語言”所設置的重重障礙,透過作家沉穩平靜的敘述態度,我們可以感覺到一種調侃,一種無可奈何的唱嘆,一種對于人之所以有各式各樣的情感狀態這一事實本身的嘲諷。
(編輯: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