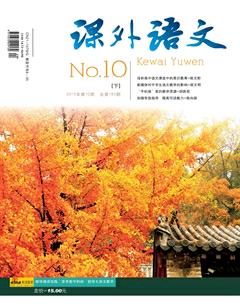以某著名培訓機構為例分析父母收入學歷對子女語文學習的影響
【摘要】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會把更多目光投向在父母教養方式本身對孩子學習成績以及做人做事態度的影響,而父母本身的收入和學歷或者說文化水平帶給孩子潛移默化的影響卻并沒有引起教育研究者足夠的重視。那么作為一名在北京某著名培訓機構任升學年級兼職語文教師的文學研究生,筆者對此問題進行了較為細致的研究,并總結出了一個結論:父母的收入在一定范圍內對子女語文成績、學習態度、課外閱讀時間及其數量以及整體學習時間的影響是正相關的。同時,父母的文化水平對子女的語文成績、學習態度、課外閱讀時間及其數量以及整體學習時間的影響在任何范圍內均為正相關。而在子女語文學習中的場獨立性和場依存性上,父母更高的文化水平會加強子女認知的場獨立性。同時父母收入對子女認知場獨立性和場依存性的影響上并不存在隨著收入增加而增加場獨立性或者減少場獨立性的狀況,因此這也在之后展開。
【關鍵詞】場獨立,場依存,年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課外閱讀時間,中考平均分數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自改革開放以來,富二代們不學無術、橫行霸道的新聞屢屢被爆出,而寒門子弟取得優異成績的報道則屢見報端,這難免會讓人們形成這樣的觀念:自古雄才多磨難,從來紈绔少偉男。換言之,家庭出身相對較差乃至父母文化層次較低的青少年會更容易取得更加優異的成績,而家庭條件較為優越同時父母文化水準較高的青少年則往往比拼不過前者。那么事實真的如此嗎?筆者以管窺豹,以自己在北京某著名培訓機構所教授的三個升學年級班級共150個樣本為例(其中一個尖子班目標為北京前十名重點高中,一個承諾班目標為北京市級示范校,一個普通班目標為普通高中,入學前經過分班考試測試學習水平),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調查,并得出了與上述觀念幾乎完全相反的結論。同時對于認知中的場獨立性和場依存性筆者也發現了較為有趣的結論。
在此次調查中,筆者共采集了150個樣本,對于收入與文化水平這兩個變量,則設置了如下選項:家庭年收入(稅前),A.10萬以下,B.10-20萬,C.20-50萬,D.50-100萬,E.100萬以上。鑒于北京2014年的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為6400元,又鑒于選擇報名課外培訓班的學生往往家庭條件不至于貧困。因此在設置選項過程中筆者設置選項的收入都比較高。文化水平筆者將其定義為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選項如下:A.9年及以下,B.9-12年,C.13-16年,D.17-19年,E.19年以上。這也分別對應初中學歷,高中學歷,本科或專科學歷,碩士學歷,博士學歷。
一、父母收入及文化水平對子女語文學習成績及中考成績的影響
由于做此調查的時間是在中考成績發分之后,因此筆者所選取學習成績的參照系就是2015年學生的語文成績和中考成績。北京市中考語文滿分為120分,總分為580分。在這150個樣本中,學生的平均語文成績為109分,平均中考成績為530分。在語文成績方面,尖子班平均成績為116分,承諾班平均成績為110分,普通班平均成績為101分(均為四舍五入后取整)。中考成績方面,尖子班平均成績為559.3分,承諾班平均成績為530.7分,普通班平均成績為502.3分。
我們可以明顯看出的是,尖子班的成績無論是語文單科還是總體成績都要明顯好過承諾班,而承諾班的成績也要明顯好于普通班。同時尖子班成績的方差和標準差都比較小,承諾班和普通班的方差和標準差均較大。筆者對尖子班、承諾班和普通班學生家長不同的收入狀況和文化水平進行了分析,具體情況如下:
關于收入狀況:在尖子班的50名學生中有5名學生的家庭年收入在100萬以上,7名學生的家庭年收入在50-100萬,25名學生的家庭年收入在20-50萬,7名學生的家庭年收入在10-20萬,只有6名學生的家庭年收入在10萬以下。而尖子班學生家庭年收入的眾數集中在20-50萬,其中也有將近四分之一的學生家庭年收入在50萬以上。承諾班的50名學生中只有一名學生家庭年收入在100萬以上,4名學生的家庭年收入在50-100萬,15名學生的家庭年收入在20-50萬。換言之,只有40%的學生家庭年收入在20萬以上,只有10%的學生家庭年收入在50萬以上。其余學生中27名家庭年收入在10-20萬,3名學生的家庭年收入在10萬以下。同時普通班沒有一名學生的家庭年收入在100萬以上,只有4名學生家庭年收入在50-100萬,9名學生的家庭年收入在20-50萬,21名學生的家庭年收入在10-20萬,16名學生家庭年收入在10萬以下。也就是只有略高于20%的學生家庭年收入在20萬以上。大部分學生的家庭年收入在10-20萬,有將近三分之一學生的家庭年收入在10萬以下。這讓我們不由得想到往往家庭年收入更高的學生會更容易取得更為優異的成績。而對于受教育年限來講,尖子班學生中有2名學生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9年以上,有23名學生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7-19年(即碩士學歷),22名學生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3-16年,只有3名學生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12年(即大學以下)。總體來講,尖子班學生中有一半學生根據推斷父母至少有一方為碩士學歷,百分之九十四的學生父母至少一方受到過高等教育,只有三名學生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少于12年。而承諾班學生中有1名學生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9年以上,9名學生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7-19年,36名學生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3-16年,4名學生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2年以下。普通班中只有6名學生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7-19年,14名學生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3-16年,30名學生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2年以下。這與承諾班和尖子班的情況完全不同。從這個方面來講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與學生的學習成績應該是正相關的。
之后筆者將分別敘述來自不同收入與不同學歷父母家庭的學生們各自表現出的語文學習水平和中考成績。首先在6名家庭年收入100萬以上的學生中有一位中考語文滿分,總中考成績位列北京海淀前二十名。這6名學生的總體語文平均成績為116.8分,中考中位成績為562分,進入了海淀區的前三百名(海淀區2015年共一萬五千余名中考生)。這似乎與從來紈绔少偉男的說法完全不符。而15名家庭年收入在50-100萬的學生中他們的語文平均成績為117.1分,中考平均成績為558.2分,超過北京最好高中人大附中的錄取分數線,但與年收入100萬以上的學生相比依然存在差距。在49名家庭年收入在20-50萬的學生中,他們的語文平均成績為110分,中考平均成績為528分。在55名家庭年收入在10-20萬的學生中,他們的語文平均成績為102分,中考平均成績為518分。在25名家庭年收入在10萬以下的學生中,他們的語文平均成績為97分,中考平均成績為506分。那么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學生的語文成績和學習成績是隨著收入的增加而遞增的,但年收入百萬以上的學生語文成績略低于家庭年收入在50-100萬的學生。那么來自不同學歷父母家庭的學生們又呈現出怎樣不同的樣子呢?首先3名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9年以上的學生中考語文平均成績為118分,最高分為滿分,其次為118分和116分。而他們的中考平均成績為560分。其次38名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7-19年的學生中中考語文平均成績為114分,中考平均成績為548分,剛好達到連續出了三年中考狀元清華附中的錄取分數線。而72名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3-16年的學生中他們中考語文平均成績為106分,中考平均成績為526分。在37名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2年以下的學生中中考語文平均成績為97分,中考平均成績為513分。我們可以看到父母受教育年限的長度對學生的語文成績和中考成績是有著顯著影響的。顯然受教育年限越長孩子的語文成績包括總體學習成績會越好。
綜上所述,父母收入及文化水平與子女語文學習成績和整體學習成績呈現正相關關系。
二、父母收入及文化水平對子女課外閱讀時間及其數量以及整體學習時間的影響
針對這一方面筆者共涉及了三個問題,分別關于學生每周的閱讀時間、每年閱讀書的數量以及整體的課外學習時間。而對這個問題的設計,筆者并未設置選項,而是讓學生自己填寫閱讀時間、閱讀書的數量和整體的學習時間。在這150名學生中,他們整體的平均課外學習時間為每天2.34小時,初一初二的課外閱讀時間為每天1.01小時,初三的課外閱讀時間為每天0.51小時。
在6名家庭年收入為100萬以上的學生中他們的平均課外學習時間為每天1.98個小時,初一初二課外閱讀時間為每天1.02個小時,初三課外閱讀時間為每天0.83小時。可以看到,家庭年收入高的學生,他們的課外學習時間并不長,初一初二課外閱讀時間與平均水平接近,而初三的課外閱讀時間則高于平均水平。在15名家庭年收入在50-100萬的學生中他們的平均課外學習時間為每天3.34個小時,初一初二課外閱讀時間為每天1.67個小時,初三課外閱讀時間為1.1個小時。可以看到,這個高收入學生群體中學生無論是課外學習時間,還是課外閱讀時間都要明顯高于平均水準。在49名家庭年收入在20-50萬的學生中他們的平均課外學習時間為每天2.95個小時,初一初二課外閱讀時間為每天1.6個小時,初三課外閱讀時間為1.2個小時。在55名家庭年收入在10-20萬的學生中他們的平均課外學習時間為每天1.87個小時,初一初二課外閱讀時間為每天0.5個小時,初三課外閱讀時間為0.2個小時。在25名家庭年收入在10萬以下的學生中他們的平均課外學習時間為每天1.1個小時,初一初二課外閱讀時間為每天0.2個小時,初三課外閱讀時間為0.15個小時。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除去家庭年收入100萬以上的群體,實際上學生的學習時間、課外閱讀時間是隨著父母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
在3名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9年以上的學生中,他們的每天學習時間分別為5小時、4小時、3小時,平均為4小時。而他們的初一初二平均課外閱讀時間為2.2個小時,初三平均課外閱讀時間為1.6個小時。這幾個數據均遠遠高于平均水準。在38名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7-19年的學生中,他們平均學習時間為每天3.11個小時,初一初二的課外閱讀時間為每天1.8小時,初三平均閱讀時間為0.9小時。在72名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3-16年的學生中,他們平均學習時間為每天2.2個小時,初一初二的課外閱讀時間為每天0.6個小時,初三的課外閱讀時間為每天0.13小時。在37名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2年以下的學生中,他們平均學習時間為每天0.56小時,初一初二的課外閱讀時間為每天0.2小時,初三的課外閱讀時間為每天0.1小時。由此可以看出,父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換言之文化程度與學生的學習時間(學習投入度),課外閱讀時間是呈正相關的。
三、父母收入及文化水平對子女學習中呈現出的場獨立性和場依存性的影響
針對認知的場獨立性和場依存性這個問題,筆者采取了運用認知方式鑲嵌圖形測驗這一方式來檢驗被試者認知的場獨立性和場依存性。在150名學生中,認知方式為場依存性的學生占到58%,認知方式為場獨立性的學生占到42%。那么來自不同收入和不同文化水平家庭的學生,又在場獨立性和場依存性上呈現出怎樣不同的情況呢?
就收入而言,6名家庭年收入在100萬以上的學生全部為場獨立性認知方式;15名家庭年收入在50-100萬的學生中只有4名。換言之,不到三分之一為場獨立性認知方式,其余均為場依存性認知方式。在49名家庭年收入在20-50萬的學生中有20名學生為場獨立性認知方式,其余均為場依存性認知方式。在55名家庭年收入在10-20萬的學生中有28名學生為場獨立性認知方式,其余均為場依存性認識方式。在25名家庭年收入在10萬以下的學生中有5名學生為場獨立性認知方式,其余均為場依存性認知方式。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家庭年收入非常高(100萬以上)的學生往往會采取場獨立性認知方式。而家庭年收入比較高(50-100萬)的學生卻只有少部分采取場獨立性認知方式。而在中上收入(20-50萬)和中等收入(10-20萬)的學生中采取場獨立性認知方式的卻比較多。而較低收入(10萬以下)的學生只有五分之一采取了場獨立性認知方式。
就文化水平而言,3名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9年以上的學生全部為場獨立性認知方式。38名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7-19年的學生中有30名學生的認知方式為場獨立性。72名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3-16年的學生中有20名學生的認知方式為場獨立性。37名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2年以下的學生中有10名學生的認知方式為場獨立性。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其子女的認知方式為場獨立性的可能性就越大。
四、結語
總之,父母收入及文化水平與子女學習成績、課外閱讀時間、學習態度均呈正相關關系。而父母文化水平的提高會進一步加深子女認知方式的場獨立性。但是父母的收入與子女認知方式的場獨立性相關并不大。當然,筆者只是選取了首都某著名培訓機構的150個樣本,以管窺豹而已,如有不妥之處,歡迎指正。
作者簡介:榮蕾,1992年生,河北唐山人。現就讀于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研究生部,主要研究方向為現當代文學。已有近兩年在著名培訓機構教授中學語文經歷。
(編輯:馬夢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