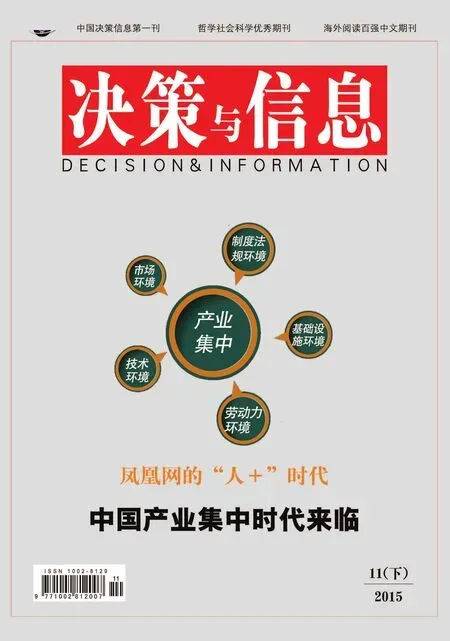孵化網絡協同演化分析
李浩費良杰
1.甘肅政法學院 2.蘭州職業技術學院 甘肅蘭州 730000
孵化網絡協同演化分析
李浩1費良杰2
1.甘肅政法學院 2.蘭州職業技術學院 甘肅蘭州 730000
將種群化重新解構的孵化網絡置于協同演化框架中,分析內層種群和外層種群關系及相互作用。結果表明:孵化網絡內外層種群具有互利共生關系,其所表現出的協同演化正是孵化網絡演生的關鍵內生動力機制。
孵化網絡;種群;協同演化
學術界對孵化網絡內涵及其異質性雙層結構的研究,以及作為網絡化孵育機制載體踐行價值的分析,已經回答了“是什么?”和“有什么用?”的問題。然而,對新生事物探究和解釋所強調的另一關鍵問題“怎么來的?”,現有研究卻并未予以回答。
一、協同演化理論
協同與競爭演化成為組織生態學從單一種群演化過程和演化機理研究向多個種群相互作用演化分析拓展的軌距。Jocl等最先定義了兩個種群間協同演化關系和相互競爭關系,指出彼此不同但又存在某種聯系的兩個種群中任何一個種群密度的增加致使另一種群的創建率增加或失敗率降低,則表明兩個種群是互利共生種群,其演化為協同演化;與此相反,彼此不同但又存在某種聯系的兩個種群中任何一個種群密度的增加致使另一種群的創建率降低或失敗率增加,則表明兩個種群是競爭性種群,其演化為競爭演化。
孵化網絡指嵌入區域社會經濟環境中,以孵化器為核心結點,圍繞孵化過程與供應鏈企業、中介機構、科研院所、金融機構以及政府所構成的超越結點并集聚大量基于技術與市場關系資源的創新網絡組織。異質性源于孵化網絡主體的多樣性,而雙層結構的劃分則是依據關系類型和強度,將強關系和正式關系為主的孵化器與在孵企業界定為內層孵化網絡,而其他外部創新主體(外部合作企業)所構成的外層孵化網絡則表現出松散的網絡結構,關系強度較弱。孵化網絡的出現與生成即是異質性雙層結構演化的過程。而且,雙層結構還成為部分學者用于判定孵化網絡周期的重要依據。基于此,本文將內層孵化網絡組織界定為內層種群,將外層孵化網絡組織界定為外層種群。
二、孵化網絡協同演化規律
進入和退出種群的企業數量不僅可以反映外部環境對種群的影響,時間透鏡下其所呈現出的變化規律能夠映射出種群演化的軌跡。李文華和韓福榮研究發現,種群演化早期密度低時,密度增加能夠提升種群合法性,創建率隨之增加而失敗率(退出)降低;當種群演化持續發展密度變大時,競爭凸顯使得創建率降低而失敗率(退出)增加,并將這一規律拓展到計算機硬件種群和軟件種群間協同演化過程的實證研究中。
孵化網絡外層種群作為孵育過程的外生(積極)要素,向內層種群中的孵化器與在孵企業提供資源和服務,而內層種群則以資金作為向外層種群的回報,并在相互輸入輸出的閉環體系下得到自身發展需要的資源。需要說明的是,外層群體中的政府機構所提供的某種無償服務是一種政策性的補貼項目,同樣會得到財政和社會性回報。
隨著孵育機制網絡化發展的持續,內層種群中在孵企業的增加需要更多外層種群的支持,而且需求多樣化所催生的網絡租金會吸引更多外部創新主體加入外層種群,同時向現有外層種群提供更多有償業務的機會。當外部創新主體以關系型模式嵌入外層種群,增加外層種群密度的同時,孵化器能夠獲取更多網絡資源提升孵育能力,向在孵企業投入更多創業與創新資源,并接收更多新的入孵企業,進而提升內層種群的密度和創建率。與此相反,內層種群或外層種群的衰退,同樣會傳染到另一種群。綜上分析,內層或外層種群,任何一個種群的密度增加都會提升另一種群的創建率和密度。同樣地,任何一個種群內的競爭性衰退也會消極影響另一種群的創建率和密度。
時滯沖擊同樣是內層種群與外層種群間協同演化過程中不可回避的系統性干擾因素,信息的傳遞、決策的時間以及反應的過程,這些因素都會造成種群協同演化過程存在時間誤差,但這一系統誤差并不會顯著影響種群協同演化的同步性。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說命題:孵化網絡,內層種群與外層種群是兩個互利共生種群,存在協同演化關系。
三、結論與研究展望
孵化網絡內層與外層種群相關性表現為一種互利共生關系,種群間演化呈現出具有同步性的協同演化。具體而言,內層種群與外層種群在創建率和密度兩方面均表現出協同演化關系。因此,本文將孵化網絡演生過程界定為,由孵化器與在孵企業契約關系與孵育互動開始,在逐漸形成內層種群的同時,吸引外部企業通過關系嵌入形成外層種群,進而逐漸演化為異質性雙層嵌套網絡組織,內層與外層種群間相互作用成為孵化網絡演化的內生動力機制,在此機制的作用下孵化網絡得以持續發展。
協同演化規律的提出以及內生動力機制的喻化,加之孵化網絡誘發模式的研究結論,再從理論層面回答孵化網絡“怎么來的?”同時,為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孵化網絡建設與管理方面提供了有效的實踐指導。首先,孵化網絡的發展不僅依靠擴招在孵企業來吸引外部企業。外部優秀企業如果能夠成為孵化器合作伙伴,會帶來更多創新契機,進而以項目孵化的模式,引進具有創造潛力和技術匹配的企業入孵,將被動篩選變為以項目找企業的引孵機制。其次,孵化網絡的發展,不僅需要競爭性甚至排他性財稅政策及各項扶持資金這樣的外生動力要素。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確保內生動力機制是實現網絡活性和內外種群演化協同性的關鍵。這就要求確保掌握需求信息并及時向外層種群擴散,從而保證“壓力”傳導的時效性。與此同時,加強外部合作企業的政策支持,促建外層總群的發展,實現政策拉動外層種群擴張,進而創造內層種群擴張的“空隙”。歸根結底,需要改變現有觀念對外部合作企業被動跟隨的固有印象,充分挖掘其機會創造的潛力。
本文尚存以下不足:研究結論對傳染行為的支持說明,企業存在非理性決策行為,進而影響協同演化進程,但種群演化后期的非理性因素有待后續研究的證實。而種群演化與組織生命周期理論的融合將有助于探究這一問題;最后,本文未對樣本的綜合性與專業性做先驗分析,專業孵化網絡所表現出的協同演化規律能否適用于綜合孵化網絡仍需驗證結論的普適性。
[1]Ariza-Montes J A, Muniz N M. Virtual ecosystems in social business incubation[J].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in Organizations, 2013, 11(3):27-45.
[2]蘇敬勤.高新技術孵化網絡生成模式及要素研究[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1,12(32):45-52.
[3]張寶建,胡海青,張道宏.企業創新網絡的生成與進化——基于社會網絡理論的視[J].中國工業經濟,2011(4):117-126.
[4]李文華,韓福榮.企業種群間協同演化的規律與實證研究[J].中國管理科學,2004,12(5):138-143.
[5]眭紀剛.技術與制度的協同演化:理論與案例研究[J].科學學研究, 2013,31(7):991-997.
[6]劉滿鳳,危文朝.基于擴展Logistic模型的產業集群生態共生穩定性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5,35(8):121-125+137.
[7]張萌,姜振寰,胡軍.工業共生網絡運作模式及穩定性分析[J].中國工業經濟,2008,6:77-85.
[8]羅峰.企業孵化器商業模式價值創造分析[J].管理世界,2014,8:180-181.
[9]張虹敏.滯后性統計方法論證及應用[J].統計與決策,2014,15:66-69.
The analysis of incubation network co-evolution
LI Hao1, Fei Ling-jie2
(1.Gansu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2.Lanzhou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 Gansu 730000, China)
This research places incubation network which has been deconstructed as population in co-evolution framework, then analyzes the relation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inner and outer popul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inner and outer populations of incubation network have mutually beneficial symbiosis relationship, which shows the co-evolution is just the key of endogenous dynamic mechanism for evolution of incubation network.
incubation network; population; co-evolution
1.李浩(1982-),男,河北秦皇島人,甘肅政法學院,講師,研究方向:創新網絡.
2.費良杰(1982-),女,陜西華陰人,蘭州職業技術學院,講師,研究方向:創新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