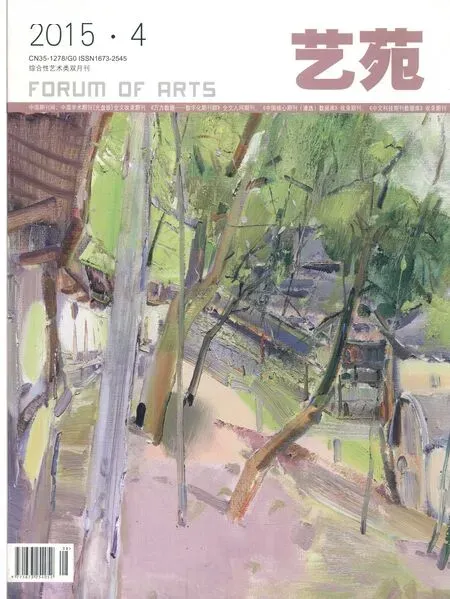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的女性主義行為藝術表達
文‖王 熠
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的女性主義行為藝術表達
文‖王 熠
本文主要從女性主義行為藝術入手,對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在藝術表達中自主呈現身體的藝術作品進行研究,分析這位女行為藝術家的藝術生涯以及獨特大膽的思維創意和藝術造詣。作為迄今為止最杰出的女行為藝術家,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用她的藝術探索精神深入地展示了她在行為藝術生死邊緣的超前創新性和高度自由感。
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行為藝術;女性主義;身體呈現
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是20世紀以來最偉大的女性行為藝術家之一,素有“行為藝術之母”之稱,她形容自己是“行為藝術的老奶奶”。瑪麗娜在早期創作生活中長期居無定所,四海為家,先后旅居到德國、荷蘭、巴西、美國等地,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國際公民”。瑪麗娜的行為藝術生涯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進行實踐,在她將近四十年的行為藝術職業生涯中,她用自己最原始的身體作為原材料進行創作,做出了許多超前和引人深思的行為藝術作品,讓視覺藝術和行為藝術的界限得到消解。她的行為藝術在往后的藝術界中已經成為一個令人難忘的傳奇。
一、用身體說話的女行為藝術家
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于1946年11月30日在前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出生。她是一位前南斯拉夫藝術家, 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前衛行為藝術家。在童年生活中,瑪麗娜受到壓抑式教育,甚至經常挨打,由于經常被忙于革命的父母所忽視,她從小個性敏感而脆弱。但同時,她的母親丹妮卡在她的成長中為她安排了很多文化課程,并讓她學習了法語和英語。瑪麗娜經常出沒于古典音樂廳、歌劇院、俄國芭蕾舞團,她甚至在12歲那年去了威尼斯雙年展,看到了眾多激進的新材料藝術作品。從那之后,她開始對繪畫產生極大的興趣,并因此獲得母親給予的一間工作室。[1]

圖1 《節奏0》
此后,1965至1970年她在前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美術學院學習繪畫藝術,后來去了德國漢堡和巴黎美術學院深造。也許是童年經歷和性格決定了瑪麗娜的創作風格,她走上了叛逆傳統的藝術道路。瑪麗娜雖然畢業于貝爾格萊德美術學院,并受到了良好的蘇派美術教育,但她卻熱衷于用傳統的技法畫一些極端的題材,比如車禍現場的暴力性和實時性。之后,瑪麗娜和幾個同學組建了一個藝術小團體,并開始逐漸接觸行為藝術。
隨著瑪麗娜在藝術造詣上的提高,她不再滿足于藝術的思維只停留在二維空間架上的繪畫表達方式, 她開始接觸裝置藝術,并利用裝置藝術來進一步表現她的藝術作品。她用自己的身體審視并探索著行為藝術的邊界。她在這個領域熱情耕作了30多年,依舊不放棄努力探索前衛的藝術表現方式。“我極力地讓自己不受人和人,以及任何事的影響。發展自己獨特的藝術表現手法, 對我來說很重要。”[2]
漂亮迷人的瑪麗娜似乎就是為藝術而生,她極其勤奮、坦率、聰明,從一文不值的行為藝術時期到現在,她幾乎經歷了行為藝術的顛覆性演變:從行為藝術該如何運作、收藏這樣具體的問題,到創建瑪麗娜行為藝術學院培養行為藝術人才,在探索行為藝術怎么樣才能擺脫作為藝術家的“副業”的地位成為主流藝術這一過程中,瑪麗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二、顛覆傳統的行為藝術實驗——“占領舞臺”
在瑪麗娜的行為藝術生涯里,她不斷地學習、挖掘、探索、實踐和突破個人行為作品、雙人組合、行為錄像、行為藝術教學以及嘗試并開拓了行為和戲劇、行為和電影等相關行為藝術的表現、推廣和發展的工作,從1969年開始,并延續到今天。藝術家瑪麗娜身體力行地向世人證明著行為藝術的價值。
在瑪麗娜嘗試行為藝術的前期, 她探索把身體在三維空間里的藝術表達形式融入到藝術創作中,且憑借它來實現對藝術的新解釋。從1970年代開始,
她利用自己的身體進行創作,不斷制造各種危險的場景和自殘的方法來思考如何突破自己身體的極限和心理的承受度。她大膽地用自己的身體來進行行為藝術的表現元素和表現手法,挑戰著她自己身體和心理上的最大忍耐和承受極限。1972至1976年,瑪麗娜創作了很多令人難忘的行為藝術作品,其中,《節奏》( Rhythm) 系列成為了這一時期的典型代表作。[3]在濃煙烈火之間,她在木質五星圍欄中的場景中被燒傷乃至昏迷,瀕臨窒息,最后被現場的工作人員搶救(《節奏5》,1974);除此之外,她還吞下了過量的精神類藥物,很快便讓自己陷入了昏迷休克的狀態,身體和意識失去了知覺 (《節奏2》,1974)。

圖2 《休止的能量》

圖3 《巴爾干巴洛克》
在瑪麗娜的藝術生涯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行為藝術表演是《節奏0》(圖1),那是她首次嘗試與現場觀眾進行互動。場景中有可供觀眾選擇的危險致命道具,包括菜刀、槍、鞭子等道具,觀眾可以對她做任何傷害的舉動,她都不會做出任何回應和反擊。在這期間瑪麗娜的視線穿過她前方的人一直望向遠方。這樣空洞的眼神使得觀眾對她的行為變得更加肆無忌憚,他們開始變本加厲,變得更加極端。盡管瑪麗娜與參與者有眼神的接觸,也許會產生一點震懾力提醒觀眾將會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但似乎并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到后來,有參與者拿起了槍試圖傷害瑪麗娜,她最終流下了無助的眼淚。在這種極端的作品中,瑪麗娜似乎是一個被遺忘在角落的孩子,她期望得到關愛,或者尋找到一種生命的平衡,可這種平衡又在哪里?瑪麗娜的《節奏0》探討了在無需擔當責任的情況下參與者的侵犯性和攻擊性,這次行為也被當做探索人性道德底線的心理學經典案例。[4]
在瑪麗娜后期的行為藝術發展階段, 她結識了藝術家烏雷,她的作品開始呈現雙人組合的表現形式,他們開始在藝術創作上進行探索合作。在之后的一段時期,兩人一起嘗試了許多以探索人性底線及人類關系為主題的系列行為藝術作品。
瑪麗娜和烏雷創作的《無量之物》(Imponderabilia)是探索觀眾心理的作品。他們一絲不掛地像門柱一樣面對面站在美術館入口,并且一動不動、目光空洞地望著對方。那個本來就窄的入口被他們倆站上后,顯得更狹小了,如果想進入美術館,觀眾必須從他們的身體之間側身擠過去。結果不難想象,幾乎所有的男性觀眾和大部分的女性觀眾都會選擇面對著瑪麗娜的方向。可以看出女性的形象更多代表著無害的、溫柔的。顯然,觀眾也無法將他們的裸體視作客觀物體,身體和精神是無法割裂開來存在的。在選擇面對誰的問題上,觀眾的表現也揭示出男性的形象比女性更難接觸,因為男性顯得更為強勢、具有攻擊性,所以他們在選擇的時候,大部分人會面對柔弱的一方。[5]
但他們大多數作品的題材都沿用了遠古時期的愛情故事, 表達了男女間永恒卻又復雜的話題。事實上,男女間的關系十分微妙,情感上相互吸引依賴,而在現實生活中彼此爭端矛盾。瑪麗娜和烏雷之間的分分合合便把男女之間的這種關系表現得淋漓盡致, 特別是后來他們在感情上的掙扎、分歧、徘徊、默
契和喜悅等各種不同的心理變化。瑪麗娜和烏雷合作的眾多作品中, 他們用自己的身體作為載體, 通過行為藝術把男女之間關系的跌蕩起伏以及情感的掙扎徘徊表現得淋漓盡致,也體現了作為不同性別的兩種個體的特質和心理。
愛情亦有分離的一天,當愛情走上結束時,他們決定完成最后一件合作作品《情人-長城》(The Lovers-The Great Wall Walk)。這個作品是他們1988年在中國北京完成的。他們在萬里長城上各自行走了2500公里,在中間相遇,然后告別。兩個人一共徒步走了長達三個月的時間。在行走的過程中,當他們再次相逢的時候, 瑪麗娜的心理發生了強烈的變化,她感覺到前所未有的壓抑、痛苦、困惑和迷茫。從1987年開始,從之前的相知相戀到后來的組合合作,他們在創作的過程中也逐漸發現彼此在對待藝術和生活的態度和價值觀上,長期以來,慢慢形成了很大的分歧。隨著這件作品的完成,瑪麗娜和烏雷的12年合作關系以及感情走到了盡頭。
分手后的瑪麗娜并沒有放棄自己對藝術的追求和執著,之后的幾年,她完成了許多互動的裝置作品。《龍頭》(Dragon Heads)是她離開烏雷之后重新創作的第一件個人行為藝術作品。行為裝置作品的創作是瑪麗娜基于之前行為藝術作品的深層延伸和發散,也是她在探索行為藝術階段上的第三個突破。
1997之后,瑪麗娜開始嘗試行為圖片攝影,并涉足到行為藝術的教學部分。1997年,她被聘為德國布倫瑞克造型藝術學院的教授,在那里教行為藝術課程。在她任教期間,她以自己大量的行為藝術的實踐經驗傳授給學生。不同于一般的教學方法,她鼓勵學生走出校門,而不只是局限于校園。為此,她還親自帶領學生去世界各地切實參與到各種行為藝術展覽,讓他們體驗課堂所學不到的知識,真正做到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后來,瑪麗娜關于行為藝術的想法延伸到了舞臺劇場,她希望行為藝術以一種很簡單、很獨特的方式融入到舞臺劇的表現中。瑪麗娜一直不斷地突破自我和藝術的邊界,30多年來的堅持和努力以及敢為天下人先的嘗試讓她成為了當代國際最有影響力的女行為藝術家。她對藝術的追求和執著充斥著無限的熱情與專注,盡管在前期取得了很大的反響,但她并不滿足于現狀,而是不斷探索和研究著行為藝術的創新發展。瑪麗娜精彩的行為藝術生涯成為了當代行為藝術發展長河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6]
三、女性身體實驗的呈現
20世紀以后,隨著女性藝術家身份的認可,以及女性主義運動帶來的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女性身體的呈現方式也發生了顛覆性的改變,由原來的被表達、被凝視的對象變成了主動的、自我表達的主體和場所,這其中女性身體的象征意義和社會身份也隨之改變。
女性的內心比男性更加細密,知覺更為敏感,她們也更富有同情心和感受自然美與藝術美的天性。當女性藝術家成為創造者,她們以自己身體為媒介呈現的藝術也更具表現力和感染力,她們有男性行為藝術家所不具有的魅力。行為藝術家通過自己的行為體驗讓觀者產生視覺及心理的感受,這種感受不可言喻,任何的描述都不如現場體驗、觀看行為本身更加飽滿有力量。[2]
瑪麗娜作為女性身體實驗的典型代表人物,非常規地運用自己的身體進行藝術創作,創造出了視覺或非視覺審美的藝術作品,它是附著精神和靈魂的材料,它的運用也能更好地體現作品中的精神價值。在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作為革命者后代的她,有著一股倔強而又堅毅的勇氣,她用行為藝術這一載體表達著個人反對壓制的訴求。武器不再成為武器,她把它們轉化成了藝術, 不是通過戰爭,而是通過藝術去進行力量的抵抗。
1980年瑪麗娜和烏雷合作,創作了《休止的能量》(圖2)。這個作品表達了他們彼此的信任和給彼此帶來的攻擊性。兩個人一手拉著一張緊繃的弓,一手拽著一支有毒的劍,彼此面對面站著,帶毒的箭頭直指瑪麗娜的心臟,他們身體都向后傾斜,將弓拉滿,毒箭隨時都有可能脫弦而出,射中瑪麗娜。從剛開始到后來,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的體力逐漸透支,觀眾透過擴音器可以聽到兩人后來加快的心跳聲音。這種危險的、看似平衡的狀態持續了足足4分鐘。他們急促的心跳通過胸前的麥克風傳遞出來,使得空間里充滿了令人窒息的緊張氣氛。這件行為藝術品運用簡單的道具和形式來表達或揭示了男女關系中矛盾的對抗性、傷害性。作品中由烏雷拉弓,反映了社會中男性掌握權力的主流性,女性在這件作品中起到的作用是最終危險的受傷者,男人在危險游戲中掌握主動權,看起來似乎更值得信賴并被視為理所當然。
這次表演的形式是簡單直接的,也是激烈沖突的,瑪麗娜在這次表演中最接近死亡。這也是他們彼此之間極度依賴與信任的表現,也暗示出在雙方的關系中女性處在了對男性完全依賴的角色,同時男性則變成潛在的殺手,傷害的制造者。而女性要為自己的過分依賴承擔著受傷害的位置。[7]
在瑪麗娜的不斷嘗試下,女性身體作為媒介進行表達的藝術有更強的開放性,藝術家不再像以往將自己關在工作室中埋頭創作,而可以走向更開放的場所——街頭、廣場等,直接與觀眾產生交流,消解了創作者與觀眾之間的距離,身臨其境也便于感同身受,因此她的行為藝術表演有很強的互動性,能增加觀眾對其藝術創作的認同感。瑪麗娜追求身體極限的狀態和心理的自我解放是她追求藝術自由的創作源泉和內在線索。
同時,由于身體的暫時性、偶然性和不穩定性的特征,這一藝術更強調
的是藝術發生的行為過程,它把其他藝術門類中注重結果的單一視域拓展到了充分認識、關注創作過程的范圍,因此有助于受眾全面地了解人類藝術多維度的,符合藝術發展軌跡的藝術運動。以女性身體為媒介的藝術看似平凡,但它具有深刻的藝術特性。藝術家用平凡的身體“有意味”地展示行為過程從而展示藝術。這種藝術打破了“藝術與生活”、“藝術與非藝術”的邊界。[8]
當代消費社會一切都在商品化之中,藝術也不可避免,然而行為藝術卻是個例外,由于受到場地、時間、創作媒介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此類作品難以留存。過程本身即是作品,在這里藝術家不再單純地看重結果,而是更加注重過程。傳統的藝術形態被消解,由此而拓寬了整個藝術領域的維度,合乎藝術前進發展的規律。行為藝術消解了傳統的藝術形態,不僅表現在無視傳統藝術的法則,還挑戰著人們的審美極限。但是在后現代看來,由于今天人類社會日益加重的危機和矛盾,審美活動失去了意義,于是后現代開始不加修飾地表現生活的本來面目。
作為一門“反叛”的藝術,行為藝術自產生之時就和暴力有著不解之緣,早期的女性藝術家更是喜歡挑戰身體的極限。由于行為藝術的開放性,藝術家為達到效果,往往會采用極端的手段來表現生命、死亡、性、暴力等問題,以喚起社會中麻木人們的覺醒。
瑪麗娜的作品多是以身體為主,她喜歡進行身體的極端體驗,挑戰身體和心理的極限。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認為,藝術真正的使命不僅僅在于滿足大眾的好奇和求知的心理,還在于通過藝術這一載體去讓受眾了解到更深處的人性真相和心理承載極限,使人們通過藝術傾聽到超越存在的聲音。也就是說藝術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千變萬化的,但要有對生命的探討和對現實哲理的啟迪,藝術中不能存在精神上的缺失。
在以身體為媒介的創作中,藝術家獲得了雙重的身份——既是(藝術創作的)主體也是(藝術作品中的)客體,由此而拓展了藝術的新主題。特別是在歐美等國,通過行為事件和藝術表演的活動,藝術家開始在觀眾與他們之間的鴻溝搭起了一座橋梁----創造和接受藝術之間----并且觀眾成為藝術中不可或缺的參與者。
瑪麗娜的《巴爾干巴洛克》(圖3)獲得了1997年威尼斯雙年展的金獅獎。[9]在這個作品中,瑪麗娜穿著白色長袍,700根牛骨頭堆成了一座小山,藝術家坐在上面瘋狂地、沉重地刷洗著還帶著軟組織的牛骨頭,她的白色衣服上沾滿了血跡和脂肪留下的痕跡。她連續4天、每天7個小時坐在這堆牛骨頭上面,一邊不停地用刷子和水來清洗它們;一邊長時間哀嚎,有時甚至歇斯底里,反復吟唱著前南斯拉夫共和國各個國家的民歌。藝術家與她的母親出現在裝置中的三個巨大的熒幕上,將現實融進了這充滿戲劇性的表演。[3]在這個行為藝術作品中,她將自己與這個社會和歷史聯系在一起,這是一次種族的清洗,通過隱喻的儀式表達了對巴爾干內戰的哀悼以及希望能蛻祛傷害達到治愈的效果。這件作品是對亞得里亞海彼岸當時所發生的事件的集體哀悼行為,這是一次穿越的儀式,是一場救贖,每個人都可以來見證這場儀式。這里的女性是在苦難中不停洗刷(靈魂)是一個救贖者的形象。[10]由女性身上的血跡以及悲慘的哀嚎象征出戰爭的慘痛,藝術家不停地洗也代表著不屈的抗戰和巴爾干的希望。
四、小結
很多人覺得女性藝術家的行為藝術做得越來越膚淺,僅存于表面,甚至帶有炒作的傾向。女性藝術家以身體為媒介的藝術表達應該是自由的、非限制性的。
我們傳統的以權力為一切的行動尺度限制了女性藝術家的發展,她們不需要遵從男性建立起的藝術標準進行創作。如果藝術界獨斷地以男性化的姿態評判女性藝術作品,那只能帶給女藝術家更多的局限和傷害。
瑪麗娜認為,藝術家所呈現出來的作品不應該僅僅是批判、揭露和反抗的本質責任,而是“必須盡可能廣泛地傳達思想并教育公眾”。她的眾多行為藝術作品讓人充分感受到殘酷、痛苦、激烈,但同時也能深深觸動人們的內心深處。她的作品中充滿著藝術的力量,那是來自她對愛永不滿足的需求,她經歷愛、懂得愛,把我們內心深處的訴求轉化和升華為極有沖擊力的侵犯式教育和行為藝術形式,起到了一種微妙的平衡作用,不管是在社交領域,還是在審美領域,都發展為一種不可抵抗的趨勢。瑪麗娜的一生都獻給了藝術,她是一位偉大的、值得尊敬的藝術家。瑪麗娜并非旗幟鮮明的女性主義藝術家,但她的作品卻涵括了大部分女性主義表達的自由觀念。
瑪麗娜用自己的身體大膽冒險,不斷去探索突破行為藝術的實驗。她試圖用自身感官觸覺所承受的一次次難以想象的痛苦,來喚醒和解放觀眾潛意識中的束縛。她的行為藝術作品充滿著強烈的、難以阻擋的視覺、觀念沖擊力,并蘊含著觸動內心的智慧和發人深省的意味。
[1]詹姆斯·韋斯科特.瑪瑞娜·阿布拉莫維奇傳[M].閆木子,譯.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 .
[2]蔡青.行為藝術現場[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
[3]朱迪斯·巴特勒.身體之重:論“性別”的話語界限[M].上海:三聯書店,2011.
[4](美)琳達·諾克琳.失落與尋回:為什么沒有偉大的女藝術家[M].李建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
[5]汪民安,陳永國.后身體:文化、權利和生命政治學[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6]Marry Douglas.Natural Symbols[M].Harmond-sworth: Pelican,1973.
[7]洪穎.行為: 藝術人類學研究的可能的方法維度[J].民族藝術,2007(1).
[8]李燕燕.行為藝術的思考北方文學[J].北方文學,2010(3)
[9]張瀟爽.血腥、病態和污穢一淺析行為藝術的誤區[J].大眾文藝,2010(12).
[10]洪穎.論作為藝術人類學研究對象的“藝術”[J].民族藝術,2010(1).
J05
A
王熠,深圳大學藝術設計學院2013級藝術學專業碩士生。